一
世间的风景有多样:壮阔的,纤秾的;雄浑的,清丽的;典雅的,时尚的……。每一道风景,缘自它生长的土壤,每一道风景,各具独特的美感。在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史上,林文月真可算是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过去的几天,林文月现身北京大学,为北大学子作公开讲座,听众达四百人之多;又在北大与六朝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当代散文等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了为期一天的闭门工作会(Workshop),本人有幸参与其会。
年届八秩的她,在中国六朝文学研究、日本古典文学汉译和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作出了骄人的业绩,令人瞩目。大概是谢灵运的山水诗奠定了她贴近自然的审美观,《源氏物语》、《枕草子》给了她源源不尽、哀婉幽玄的情致,加之岁月人生的演进,渐次凝炼出她亦文亦史、平淡中见雍华的学者型散文。林文月自述“我的三种文笔”,实在并不是自诩自夸,而是经年累月穿梭在论著、翻译、散文三种文体之间,历经沉潜涵咏过后的金针度人之谈。
一般来说,平常人——学者也好,译家也好,文人也好——一辈子能够得到她上述三者当中的一份成绩,也应该是很好、很圆满了。偏偏她能够三者兼顾,更还出了本《饮膳札记》——女教授的十九道私房佳肴,弄得不知学术为何物的饮食男女、普通读者,也通过她的厨房料理,得知了她的美丽人生和过人才华。不仅仅如此,林文月还更得上天眷顾,天生生得“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富有民国才女之风韵,而高鼻阔嘴间又透出西洋的大气。一时间,美丽林文月在秋意正浓的京城,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文学旋风。
二
林文月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日租界,从小上的是日本人小学,接受了十多年母语式的日本语教育。日本战败,她回到祖籍台湾,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之后,林文月一路在台湾学习成长,读的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后一路做到母校中文系教授,可以说是将自己真正的母语修成了正果。日语的先天优越,中文系的后天学养,是她正式展开日本古典文学翻译的雄厚资本。这两者缺失一项,或许都要减分不少。目下出版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更多出自外语出身的译者之手。这让我们常常怀念过去年代富有国学素养、汉文功底深厚的周作人、钱稻孙、丰子恺等人的翻译。从这一点上看,林文月的中文系身份,使她具备了可以上承这些前辈大家的资质,无论在翻译上,还是创作上。
1969年,36岁的林文月赴日,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一年。在专业领域研修拓展的同时,她遍访京都古刹名寺、书店、料理店,体悟千年古都的文化遗存、风俗人情;陆续写成京都游记,一篇篇寄回台湾,连载发表。在那个中日之间尚没有很多往来交通,更遑论开放旅游的时代,这本随后结集出版的《京都一年》,是林文月留日一年,不亚于专业(正业)研究成果的重要副业收获。
在我看来,当时要在京都成就这份副业,是有点“功夫在诗外”的意味的。除了日语娴熟外,至少还需要另两个要素——经济上和心情上两方面的余裕。不妨拿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在结束京都进修前,林文月父母欧游返台路过日本,在京都一流的“东华菜馆”,特设中华料理宴席,款待京大人文研照顾女儿的日本人指导教师等人。那些并不能让宴请主人满意的异邦中国菜,却令日本教授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一席五万日元,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经济实力,恐怕是入乡问俗、入乡随俗的基本保证吧,也是《京都一年》中逛书肆、品茶会、观歌舞伎、享受京料理的前提。这是经济方面的余裕。另一个例子,是她历年散文中多次提到自己的一位京都好友“秋道太太”“A女士”——一个有文艺追求的日本料理店老板娘,一个能够把自己绝密隐私告知作者,并在此后三十多年一直与作者维系着友情、分享着人生欢愁的京都女人。她的故事,在林文月笔下,如剥笋般层层展开,虚实相间,铺陈有致,有惊异,有理解,这是对异国的采风,更是对生命情爱的追寻。如果没有精神上走近日本,走近日本人内心的明敏,又如何写得出这样体贴入里的散文?这是心情上的余裕。
这么想来,作为学者而能够研究与创作兼营兼善,是要有一颗敏感灵动的心和优雅余裕的心境,无论在何时何地,本土抑或异邦。
三
1972年,林文月赴日参加学术研讨会,宣读《桐壶与长恨歌》的中日比较文学论文,之后,论文在台湾大学《中外文学》上刊发,同时附录了《源氏物语》第一回《桐壶》的汉文翻译。以此为契机,林文月用了五六年时间,翻译出百万言的《源氏物语》全本,从1973年至1978年在《中外文学》上连载完毕。这是中文世界《源氏物语》译本的首次完整问世。
在此之前,丰子恺于1965年末完成了《源氏物语》的全部翻译,却因“文革”爆发,书稿的出版计划一再被迫中止,蹉跎十多年。直到1980年,《源氏物语》上册前20回才得以问世,中册和下册于1982、1983年陆续出齐。
可以说,林文月是在中文世界汉译《源氏物语》第一人的心情和责任感之下,完成并出版了这部巨著的。
继此之后,她又陆续完成《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的汉译工作。这四部著作构成了日本平安时代文学的巅峰阵容,也是林文月作为台湾翻译家,以一己之力对中文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其中,《枕草子》有周作人译本,《伊势物语》有丰子恺译本,但这两个本子在大陆的命运,也都是早译而晚出。周作人、丰子恺均是上个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是林文月的大前辈。林文月译本在中文世界能够“后起而领先”,不能不令人寻味这过去的百年中,大陆与台湾文化环境、学术力量的此消彼长,交替演进。
人们多津津乐道《源氏物语》丰译和林译的风格特色,也喜欢比较评说《枕草子》周译和林译的优劣高下。这确实是饶有趣味的话题,可以藉以增进读者阅读鉴赏的能力和品味。但我不想对此细说详辨。要之,周作人、丰子恺、林文月等人先天的性别不同,所处时代不同,加之学术环境、人生境遇、语言禀赋等外在因素的差异,使他们呈现了各具风格特色的译作,令汉译日本文学名著的园地晨钟暮鼓,阴阳浓淡交错有致,正如京剧舞台上之有梅尚程荀,柔美、典雅、深沉、委婉、刚健,异彩纷呈,有福的正是我们读者和观众了。
更令我驻足留意的,是译者林文月面对千年前作者和作品的心境和态度。学者的谨严和练达,文人的敏感和细腻,透过译文,跃然呈现出来,令人赞叹。细品《源氏物语》修订本序言,你会感到,对于这么一部裹挟着许多谜题、几乎是凌空出世的日本古典文学长篇,对于这么一部花费了自己五六年心血,首译问世的鸿篇巨制,译者在交代叙述时,不紧不慢,把《源氏物语》的世界性位置,作者的姓名身世及创作过程,物语、和歌的文学史阐释及与中国类似文体的比较,以及平安时代的贵族生活图景等等,一一娓娓道来;又推进及于原书主题的探究,介绍日本现代语译本乃至西文译本之种种,最后是译者关于翻译中具体事宜的自述,一项项曲尽其详,而又都是用了平易简约的文字来写出。没有旁征博引,不作高深玄奥,由博返约、通达洗练,呈现出“博文约礼”的美德和厚积薄发的功力。
博与约之外,还有理与情。林文月说,“近来我则又逐渐了悟,即使写学术论文,仍然不能完全抹煞情感;至于冷静与同情之间的敛放不逾矩,又委实是此类文章的高层次标的了。……冷笔与热笔的运用自如,也应当是写作论文的更合情合理的正途吧。”(《我的三种文笔》)在遵守学者的冷静客观和理性谨严的同时,也要不失研究者自己的情感立场,这一点,林文月的主张或许不能被时下的青年学人所全部认同和体悟,而正是在这点上,我也是深表赞同的。且看她给《枕草子》作者清少纳言写的一封信:“你的心情,我想是可以体会的。……你可以把我当做一个知音,因为我曾经仔仔细细读你所写的每一个字,并且能够体会那些文字,以及文字以外的一些事情。”(《你的心情》)她就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发表一个译者对于所译作品作者的理解、评论,甚至交谈,道出译者对于文学、生命、情爱这些永恒的主题的体认和主张。正如她在另一处所说,“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参入了紫式部的世界。有时夜深人静,独对孤灯,仿佛紫式部来相伴,虽千年相隔,文章神交,我并不寂寞。”(《我的三种文笔》)文学的魅力直抵人心,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林文月首先感悟到了,又用她的译笔,为我们移译传达出这个融汇古今、打通中外的通明世界。这时,她是多么充满了感情,充满了自信!
紫式部、清少纳言得遇林文月,何其有幸!
握有“三种文笔”的林文月,是海峡彼岸一道亮丽的风景;这道风景的名字叫做:美丽林文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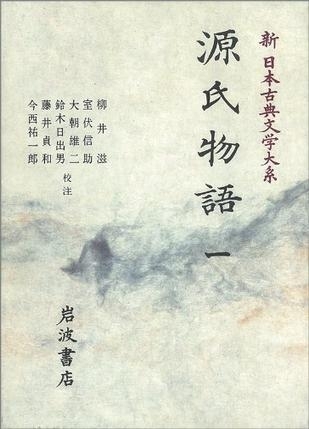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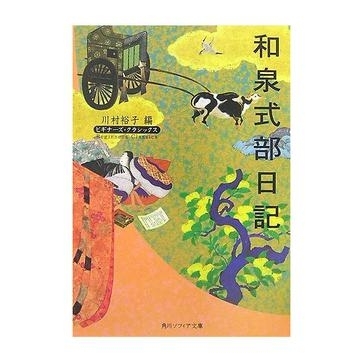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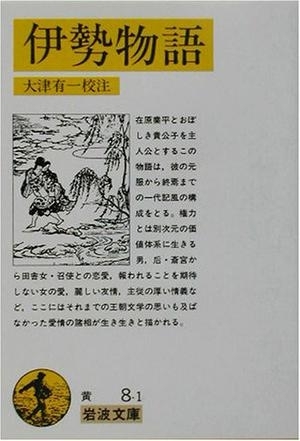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