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与中国诗学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两棵大树,它们的根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30年来探讨诗禅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热点,至今出版的相关著作早就超过一百种。马奔腾所著《禅境与诗境》最初由中华书局于2010年9月出版,2012年5月修订重印。
从内容结构上看,《禅境与诗境》构思巧妙,逻辑顺序合理、整饬,涉及到了禅境与诗境关系研究最主要的方面,先探讨了诗、禅趋近的文化背景,为下文进一步的展开作铺垫;接着分析了文人与禅的关系,从古代文人的信仰世界、文人生活与佛禅、文人诗歌与佛禅三个角度进行论述;然后探讨了禅对诗歌意境创造新变的影响,从禅家自性对意境的开拓、禅门直觉与意境的神韵两个方面入手,并顺带说明了道家艺术境界与禅家艺术境界的异同;进而阐述了禅与诗歌意境理论发展的关系,对历史上各个时期与禅相关的主要诗文论著述进行了细致而又简明扼要的研究;最后谈到意境理论和禅美学的现代意义问题,重点突出了王国维、宗白华在历史转折点上对意境研究的重大贡献。全书是在宏观历史文化背景上对关键的微观问题进行阐发,点与面紧密结合,而又收放自如,颇具匠心。
《禅境与诗境》有许多令人感到新颖的理论成果。如运用现代心理学以分析禅境与诗境,揭示了它们相通的思想根源,认为它们是异质同构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诗、禅多重关联的基石。在“禅与诗歌意境创造的新变”一章中,主要抓住禅家自性、禅门直觉与意境创造的关系分别论析,把传统上禅对诗境的影响这一比较模糊、非常难以说清的问题清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作者认为禅家自性拓展了诗人的心性、改变了诗歌意境的内在构成方式并使诗歌有了孤清一途.“如果说不受佛禅时空观影响的诗歌在表现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上追求身与物游、心与物游的话,那么受禅家时空观影响的诗歌则追求心超物我。前者追求的是自然之境,后者追求的是超然之境。其意境的构成方式和审美情趣,因而有质的差异。”禅门直觉则使诗境更少滞碍、更含蓄蕴藉。在谈到道、禅反映于文艺中审美追求的异同时,他说:“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上,道、禅都表现为对外在世界散点透视(甚至是毫无间隔、浑融一体的‘无点透视’)的审美原则,而不是焦点透视,其作品充盈着自然精神和宇宙精神。”“如果说道家诗篇常让我们感到清新的话,那么禅家诗歌的境界常让我们感觉到洁净。道家的清新来自于对自然的亲融,禅家的洁净源自于对俗世的超越。”本书还特别揭示出,在中国古代封建等级秩序中,禅的平等精神能使士大夫压抑的精神和人生得到舒展和超越,并塑造了他们的审美追求。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许多文论概念是在没有学科分野时产生的,与西方比中国诗学概念的形成有综合性的特点,所以作者是“将中国古代诗学问题与传统文化哲学联系起来在一定范围内作整体性的研究”,最后又结合西方相关美学理论探讨了禅美学的当代价值。
《禅境与诗境》另一个吸引人的亮点是语言的优美流畅。佛禅理念原本深奥难懂,古代诗论也颇多玄妙之处,作者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却是举重若轻的,以轻灵的笔触行云流水般把它们展现于读者的眼前。如在谈到陶渊明《饮酒》和王维《终南别业》两首诗时说:“前者的视角缓缓扫过菊花、东篱、南山,抑或还有想像中头顶的悠悠白云;后者的视角则伴随作者的行程经过了蜿蜒的泉水、空旷的山岭、升腾的云霭。”他在《后记》中言:“我怀疑,那种外科手术式的解剖研究和异常繁琐的理论论证能否真正达到文艺的真心。”“许多地方的表达也感性了一点,想的是借理性之刀在切开问题外壳的同时而尽量少伤及里面原本圆融生动的内容。”有读者在网上评价说:“并未陷于故弄玄虚、自炫与炫禅,并未迷于禅中说禅。”
《禅境与诗境》一书所谈的“诗境”是以诗歌境界为主,但并非仅局限于诗歌之境,而是指一种宽泛的诗意境界,所以除诗歌之外,作者还在不少地方谈到禅对绘画、园林等的影响。不过这方面的论述还相对薄弱,是需要作者在将来继续拓展和丰富的学术园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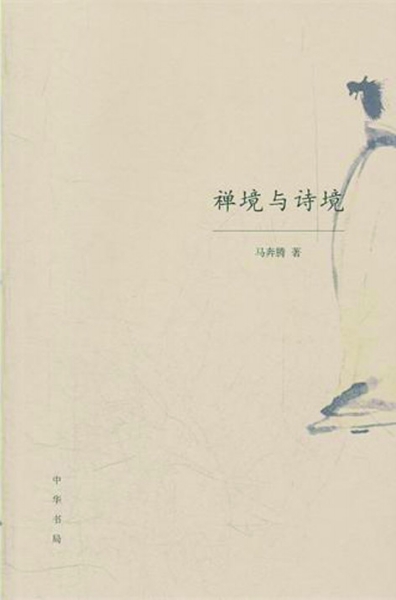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