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研究需要和个人兴趣,笔者多年来收集了不少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去年夏天,当获知中华书局要出版一部内容涵盖新中国建立前已有的7种汉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时,心情非常激动,几乎每隔一周左右的时间都要在网上看看有无该书出版的消息,真是翘首企足、望眼欲穿了——我想,由百年老店、又是新中国建立后学人公认的文献整理出版重镇的中华书局来把这珍贵的7种译本汇编成册,其质量绝对应该是有保证的。最近,这本书终于出版了(版权页上标明出版时间是2011年12月),我一次购置了两部,一部供平常阅读和研究时勾画、做笔记用,一部供珍藏。但最近经过初步翻检后,却不能不遗憾地说,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这个纪念版(以下均称该书为“纪念版”)的编印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出版说明》没有交代清楚影印各译本时所据底本的情况;有关译本的排列顺序有误。
纪念版的《出版说明》是这样列举7种汉译本的:1)陈望道译本,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2)华岗译本,1932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印行;3)成仿吾、徐冰译本,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4)陈瘦石译本,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比较经济制度》(下)一书中作为附录收入的;5)博古校译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出版;6)乔冠华校译本,1948年香港中国出版社出版;7)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1949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
纪念版在汇编7种《宣言》的汉译本和一种英汉对照本(实际上就是华岗译本的初版本,笔者注)时,采取了影印或仿真排印的形式;同时按照各底本的不同版式(直排和横排),将全书分为两部分(直排部分右翻,横排部分左翻)。这可能是出于排版的方便,读者是可以理解的。《出版说明》中说:“其中所据成仿吾、徐冰译本,因当时印刷质量欠佳,本次汇刊时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改为仿真排印。其他各本则采用影印的形式。”
那么,除成仿吾、徐冰译本外,在影印其他译本时采用的底本分别是什么呢?读者恐怕只能理解为,当然是上引《出版说明》中列举的各相关译本后注明的版本了,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像第一种译本即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陈望道译本,就有8月的初版本和9月的再版本之分,那影印时所据的究竟是何种版本呢?可见,《出版说明》并没有给读者交代清楚影印各译本时的底本情况。这对于“纪念版”来说,是比较粗疏的。
还有,列举7种译本时,其顺序理应根据影印的各译本出版时间的先后来确定,从实际情况看,这也是编辑部的打算,但读者可以发现,在《出版说明》中,1943年初版的博古校译本却置于1945年初版的陈瘦石译本之后,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目录》中的排列顺序以及实际编印的顺序是正确的,笔者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高放先生为纪念版所写的序言中,误将陈瘦石译本的初版时间作为1943年9月了(见该书右翻部分第三页),事实是,陈瘦石译本是作为附录收入《比较经济制度》一书的,但该书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上册初版于1943年9月,下册初版于1945年4月,作为附录的《宣言》是在下册中才出现的。《出版说明》既已正确断定陈瘦石译本初版于1945年,就应该将其置于1943年初版的博古校译本之后。
第二,影印的陈望道译本和博古校译本与《出版说明》不符;影印的陈望道译本封面,存在严重问题。
按理,既然是《〈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那么,制作时均应以各译本的初版本作底本,但该书事实上并未做到这一点。退一步说,如果在寻找或选择初版本时确有困难,那也应该都像对成、徐译本的处理一样,给读者交代清楚有关情况——尽管根据笔者了解,目前要影印7种译本的初版本,并不存在底本来源方面的困难;至于《出版说明》中关于成仿吾、徐冰译本之所以采取了“仿真排印”的形式是因为“当时印刷质量欠佳”,这一解释恐怕难以成立,而是另有原因的。笔者现在要说的是,纪念版中影印的陈望道译本和博古校译本,不但不是初版本,而且与《出版说明》不符。
根据《出版说明》,纪念版影印的陈望道译本应该是“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版本,但事实是,在纪念版中出现的,既不是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8月的初版本,也不是9月的再版本(从“纪念版”的角度看,当然应该按8月版影印)。陈望道译本的初版本和再版本的正文,均为56页的繁体字直排本(两个版本的区别在于封面和版权页不同),而纪念版中影印的正文,却是66页的已经含有大量简化字的直排本——根据北京红展马克思展厅范强鸣同志初步判断,纪念版很可能是根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某出版机构内部印行的一个本子影印的;而更令读者不能容忍的是,纪念版影印的陈望道译本的封面,存在严重的问题:马克思的手指竟然有6个(所选底本的封面模糊,可以修补,但这一修补效果显然不理想)!
其实,现在要影印《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的初版并不是难事,笔者手头就有近年来国内影印的两个版本。一是2006年10月,由范强鸣同志设计并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红色中华第一书》,二是2011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上海图书馆下属的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仿真影印本,两书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重新影印了陈译《宣言》的初版本和再版本。这两种影印本从封面到正文,质量均属上乘。中华书局这次完全有条件借鉴和参考兄弟出版社的经验,在影印陈译本方面更上一层楼,但谁能料想到会是如此效果呢?
根据《出版说明》,影印的博古校译本应该是“1943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版本,但现在读者看到的,封面顶端是“干部必读”四字,这显然不是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的初版本,因为编辑“干部必读”是中共中央在1949年春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才决定的事,“干部必读”则是1949年6月才开始出版的。
行文至此,笔者想大胆地说一句,《出版说明》之所以不给读者交代清楚影印各译本时的底本情况,恐怕不是编者的疏忽,也不是不可为之,而是不想为之的;与此问题相联系,纪念版的编者不想为之的,还有影印各底本的版权页——这么一项重要内容,在影印大多译本时,是缺失了的——而我们知道,历史文献的版权页能提供该文献的出版时间、地点、出版人或出版机构、印数等各种信息(即使有的版权页因采取了伪装形式,可能会提供某些虚假信息),是从事研究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依据——这本来是影印历史文献的常识啊!
第三,影印的1932年版华岗译本出现失误,而其“勘误”页上的说明,意思表达不清,给《宣言》的版本研究制造了新的盲点;把成仿吾、徐冰译本作为华岗英汉对照本的附录,则是不符合逻辑的。
纪念版的横排部分,主体是1930年初版的华岗译本(即英汉对照本)的影印本。这个影印本有两个附录,其编排都存在问题。
附录一有两个内容,其中之一是影印了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1932年版的华岗译本,这样,华岗所译《宣言》的正文,在纪念版中就出现了两次。我们知道,华岗译本1932年版与1930年初版的英汉对照本的区别,在内容上就是前者多了三个德文版的序言,那么,作为附录,纪念版本来只影印这三个序言就可以了。当然,1932年版的华岗译本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仍是非常珍贵的革命文献,全本影印,亦不无意义。问题是,在影印1932年版时,纪念版最初却遗漏了第47页,也就是《宣言》正文的最后一页。事后,编辑部制作了一份“勘误”,但这份“勘误”中的说明文字,意思表达不清,甚至给《宣言》的版本研究人为地制造了新的盲点。“勘误”中的说明如下:
“因制作时所采用的1932年版华岗译本存有瑕疵,现将原底本遗失的第47页,据华景杭女士藏本影印,制成此面,以补遗憾。”
这里的问题首先是,所谓“1932年版华岗译本存有瑕疵”,会让读者误以为是华岗翻译上的“瑕疵”,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其本意,恐怕应该是说影印时选用的“1932年版”的“底本”“存有瑕疵”吧;根据附录一中的另一内容,即华岗女儿华景杭所著《华岗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一文可知,华岗译本1932年版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书前标明“1930年初版,1932年三版”,根据笔者了解,国图所藏该书完整无损,并不缺页),又据《出版说明》,在制作纪念版的过程中,编辑部与华景杭是有联系的,那为什么影印时不采用国图的原版或华女士的藏本,却要采用一部“存有瑕疵”的底本呢?其次,我们还知道,由于华岗从1955年起即被错误关押,此后他的所有著作包括译著均被封存或毁坏,因此,现在存世的解放前《宣言》华岗译本的各种版本,是极为罕见的,那么,编辑部在制作纪念版时采用的那个“存有瑕疵”的“1932年版”,究竟有何特点,是国家藏本还是私人藏本,现藏何处,等等,不是也都值得考证和研究吗?纪念版的性质和意图是文献整理,读者有权从中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不能不说,“勘误”页上的说明,给《宣言》的版本研究人为地制造了某种新的盲点。
附录二也有两个内容,一是“仿真排印”的成仿吾、徐冰的1938年译本;二是成仿吾晚年所写的《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我们知道,成、徐译本是在我国出现最早的根据德文本翻译的《宣言》汉译本,它本是一个独立译本,与华岗译本不存在任何依附关系——那么,编者把成、徐译本以及成的回忆文章作为华岗译本的附录,道理何在?其实,按照逻辑关系,博古和乔冠华的校译本,倒是都可以作为成、徐译本的附录的,因为它们分别是根据俄文本和英文本对成、徐译本的校订。
最后顺便说一句,纪念版版权页上的译者署名是:陈望道、华岗、成仿吾、博古、乔冠华、陈瘦石,这里显然漏列了徐冰以及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的译者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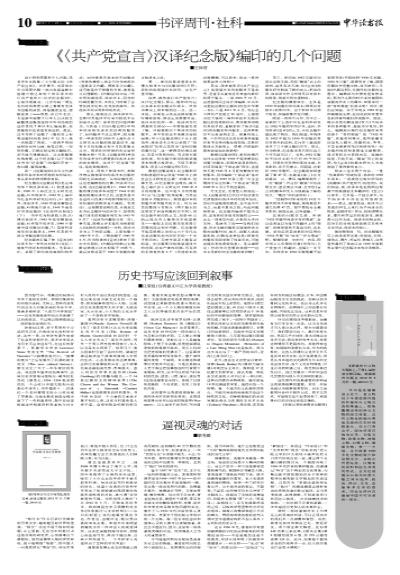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