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写给自己的书。一是珍藏个人情感,一是自我答疑解惑。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个人经历、朴素情感,显然不是博士论文选题的理由,对我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的家乡是永济县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打记事起,黄河就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白天,一出家门就能望见大河。晚上,枕着河水的声音入梦。幼时,正值黄河泛滥,大河东崩西蚀,人们眼巴巴看着大片土地沦入河水,河水一天天紧逼村庄,以至村人夜不能寐。后来,政府在村西开始修建拦河大坝,村庄才归于平静。当河水消退后,沿河一带的村民开始耕种滩地,边界争端此起彼伏,我亲历村庄之间的大规模械斗,那种场面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想做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我觉得,写博士论文的过程,就是把以前的一些感性的东西转化成学术性的东西。关于本书选题的过程,我在后记里面有所交待。其实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就想做,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做,后来读博士学位,又回过头来,有一个反复。把博士论文当作散文来写,用生动细腻的文字来描述“流动的土地”是最基本的东西。
这些距离学术研究还有很大差距。历史研究注重的是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对新材料而言,行龙师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搜集一手资料。为了搜集相关资料,我到过山西、陕西各地档案馆查阅资料,也深入沿黄村庄收集鱼鳞册、碑刻等资料,开展田野访谈,应该说在新资料的发现上有所突破。
有了新资料还不行,好比有了一堆菜,能否把它烹饪为佳肴,则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如何把地方性、区域性资料和学术问题对接起来,把自身的研究置放在学术通道上,也就是形成开展研究的问题意识,这一点曾长期困扰着我。
世纪之交,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区域转向,在区域史研究中,出现了“太湖模式”、“关中模式”、“岭南模式”等等一些具有中层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名词时常挂在嘴边,其实我对这些东西也是一知半解。秦晖先生在《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再版序言中,忆及当年他在关中各地档案馆查阅资料的情形,我感同身受。我最初在陕西省的一些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根本没有把“关中模式”和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半点意识。直到有一天,我在翻阅秦晖先生的论文时,忽然发现他所运用的资料正是我已经搜集到的资料的一部分,掩卷长思,“关中模式”对黄河滩地鱼鳞册的解读和我的经验是不相符的,这种困惑是需要自己来解答的,所以,我尝试着写了相关论文,对“关中模式”提出了商榷,得到了秦晖先生的肯定和鼓励。
当然,学术商榷只是本书很小的一部分,也不是著作的立意。本书在方法上,受到环境史这一学术潮流的影响,试图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研究区域社会。黄河滩地这类“流动的土地”,受水沙条件、河岸条件影响,位置、面积、壤质等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条件下,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对区域社会的构建和变迁产生着重要影响,也让人看到了常态土地不易显示的因素。“流动的土地”有点四不像,奇奇怪怪,但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流动性、不稳定性,如何把这种流动性的因素固定下来,划分边界,明晰地权,建立秩序等成为地方社会和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从黄河小北干流来讲,人与环境的关系经历了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状况的被动适应,到建立三门峡水库的改造环境,这是一种结构性变迁。我对“流动的土地”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想探讨人与环境关系的演变。
鉴于研究对象的特点,我借鉴了环境史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既然“流动的土地”是四不像,因此,这本书连我自己都很难说清它属于社会史、经济史还是历史地理学,以及它是否属于环境史的著作,只有接受读者的检验了。书中不是没有欠缺和遗憾,我对此很清楚,比如,书中对于三门峡水库修建后的研究,就有些不充分,只好留待以后努力了。总之,我会“把环境史进行到底”。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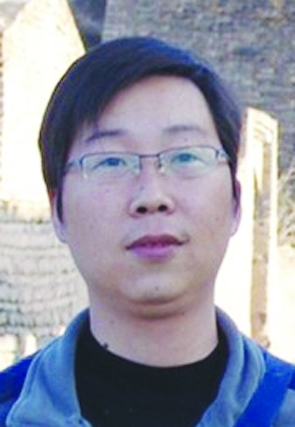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