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先生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学者。张先生不但朴实无华、和蔼可亲,而且最具有“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真正学者精神。
先生以学问渊博著称,时常有人当面或书面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或多少与学术有些关联的问题。公家(如先生任职的社科院历史所)也不时将他们收到的咨询与学术有关的问题的来信交给先生,请先生答复。先生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无不竭诚作答。如果提问题请教的是熟悉的年轻后辈,先生谆谆诱导的恳切态度更是令人感动。有时候,先生头天回答了本单位一位年轻人的提问,第二天上班还要从家里带来有关书籍,让提问的人参考,而提问的人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我曾经多次向先生请教,获益极多。这里只举一个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例子。我本是学先秦史的,从1956年底到1960年,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随导师胡厚宣先生在历史所先秦史组学习。头两年,我跟另两位年轻人合用的办公室正挨着张先生的办公室,接触机会较多。有一次我向先生请问学先秦史应该注意之点。先生告诉我,对于了解先秦的社会、历史,最重要的古书是《左传》和《周礼》,想学好先秦史,一定要好好读这两部书。这一教导对我非常重要,让我一生受用。惭愧的是,我虽然经常用这两部书,但并没有真正读透这两部书。
请先生看稿子的人也非常多,固然多数是学生、朋友,但也有不少本来并不怎么熟悉的人。有些稿子也是公家交给先生,请先生审阅的。先生对让他看的稿子也都持认真的态度,提出他感到应该提的意见。
先生还时常主动为人提供研究问题或写文章所需要的资料。我就曾两次受益。
我写成《战国货币考(十二篇)》一文后,曾把清稿送请先生指正。文中《圁阳布、圁阳刀考》举出了我所知道的汉代金石刻中把地名“圁”写作“圜”的全部例子。先生看了稿子后告诉我,北京大学旧藏的郭仲理、郭季妃二石椁刻文中也有“圜阳”地名,并把石椁刻文抄给了我。我在向北大学报交稿前,把先生告诉我的例子补了进去。
我在写成《释❶》一文前,曾利用一次会议的休息时间,跟先生说明这篇文章的大概内容,讲到了《说文》“❷”字的篆形。我指出在《四部丛刊》影印的《说文解字系传》的影宋钞本里,“❷”字及两个从之为声的字的“❷”旁,其篆形中部都不作“❸”而作“禹”,这是合乎较古的文字的写法的。那时,先生和我正在参加北京市政协的大会,会期较长,平时住在开会地点,中间有回家休息的机会。先生从家里带来他所藏的清人冯桂芬翻刻的宋本《说文解字均(韵)谱》给我看,指出我说过的那三个字的篆形,宋本《均谱》与影宋钞本《系传》全同。我把先生告诉我的情况写进了《释❶》。
先生接待来访者,回复来信,看送来的稿子,花费了大量时间,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写作。熟悉先生的后辈们都为此感到可惜,有时也直接向先生说出这种想法,要先生多考虑一些自己的工作。先生却仍然我行我素。显然,先生是把他为别人所做的那些事,看作一个学者应尽的义务的。
先生渊博的学问,我们固然望尘莫及;先生的真正的学者精神,我们更是高山仰止,自愧弗如。
在这里还想附带记下先生的一个具体的训诂见解。先生有一次跟我说,他认为大盂鼎“❹正厥民”的“❹”,不应该像一般人那样读为“畯”,而应该读为“允”,用法跟《论语·尧曰》“允执厥中”的“允”相同。我认为先生的这一见解是值得重视的。我想,按照这样的思路,在先生看来,金文中的其他“❹”字,至少有一部分,如“❹臣天子”、“❹永保四方”、“❹保四或”、“❹保其孙子”等语中的“❹”,也是应该读为“允”的。甚至《诗经》中的某些“骏”字,也可能应读为“允”。如《周颂·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句中的“骏惠”,是很难讲通的,似乎就可以读为“允惠”,“惠”就是殷墟卜辞中常见的虚词“叀”,用法与“唯”相近。《尚书》的《酒诰》和《君奭》都有“允惟”之语。“允惠”与“允惟”相近。“允惠我文王”还可以跟《周颂·时迈》的“允王维后”相比较。此外,《诗经》里的“骏”似乎还有不少可以读为“允”。希望我的引申是符合先生的原意的。先生读“❹ 正厥民”为“允正厥民”的意见,似乎没有公开发表过,所以我感到有必要记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本版文章除李零文外,标题均为编者所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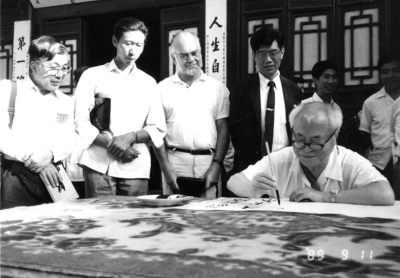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