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再到《浩荡两千年》,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系列,只是这次时间的跨度如此之大,让我终于明白吴晓波真的要跟中国企业发展的漫漫历程死磕到底了。说实话,面对这个令人头晕的大跨度写作,我由衷地敬佩吴晓波的执着和耐性。
关于经济和历史的写法已有很多,学术的研究也蔚为壮观。而作者一直以来坚持探寻显像世界之下的某条潜在脉络。这条脉络区别于学术研究追求的理论体系或者思想系统,也区别于更为庸俗肤浅的猎奇式的历史故事的讲述。作者希望用一种更加生动的方式对人们所感受到的种种世界表象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中国自古轻商重农。当我们细查历史文献时,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至少从政府的角度、政策的层面,扬农抑商的宣传从未停止过。但是,正如当前众多政策出台后,人们的解读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一样,单从政策的文字表述上,至少很难看出政策所表述的内容能够代表实际情形。当前国家要求企业保证职工的各项权利,但是执行落实者寥寥,我们身处其中很容易明白这种错位的存在。中国历史上轻商的思想确实存在,代表经济线索的商业发展史也从未缺失,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时隐时现而已。本书作者就是在探寻这条商业线索。
中国的商人从来无法单纯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人,他们必须在经商的同时努力靠近或者远离权力。可实际上,这两种选择都令中国式经商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商业行为。在这样的语境下,令中国的老百姓称道的所谓成功商人只能是那些在权力与商界之间保持良好平衡的人,或者人们会用“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之类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状态。可是冷静的观察者们很容易发现这种惬意背后的基础是多么脆弱。中国人常把国外有数百年历史基业长青的企业挂在嘴边,并感叹中国企业的鼠目寸光。然而,在皇权意识延续两千多年的环境里,在财富会被随时剥夺的境遇下,人们不会相信纯粹追求财富就可以长久,所以中国的古话“富不过三代”就真的很“灵验”,这其实不是古人发现的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古人总结出了中国式财富轮转的事实。书中写道:“在经济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汉唐明清莫不如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中火中取栗,成就功名,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
明白了这个道理,自然也就清楚了为什么中国的商人无法长久地积累财富,因为每一次政权的更替、每一次权力的转移都会让个人的财富从有到无、从无到有。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商人的至高境界是成为“红顶商人”。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数百年的企业,许多省市都有众多的百年老字号,而它们的一大特点就是基本属于日常生活的范围。比如,北京的六必居、吴裕泰、同升和、便宜坊,天津的崩豆张、狗不理,山西的东湖老陈醋,上海的杏花楼等等,这些老字号大都集中在餐饮、药品、日用品等领域。人们很少看到曾经红极一时的钱庄票号发展出的金融业老字号,更不必说当时由国家控制的盐铁之类。这些老字号存在的一个原因用书中的话说就是“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这些限于生活领域的商业很难积聚大量的资本,甚至资本有所积累之后也难以进一步实现资本的运作,它们能生存下来已属不易。而那些“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的领域基本上看不到纯粹民间资本的身影,这些领域要么直接属于政府要么属于皇权的附庸,由此产生的商业机构也自然要随着帝王、朝代的更替而改变,既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么又怎会有数百年不变的政权,更不会有脱离政权而“基业长青”的商业机构存在了。
从书中不难看到,历史早期的所有大商人都是与帝王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他们把自己的商业头脑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而个人的命运也与国君的生死捆在了一起。从中也能看到,中国的商人是怎样被政治与经济营造出的巨大漩涡卷入其中无法自拔的,中国式的商业难题单单依靠商人群体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两千年的时间跨度的确太大,此书因而没法显出《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那样的生动。它把落脚点放在更大的题目——权力与商业的相互融合、纠缠上,即中国式商业困境的历史,对某些商业集团或者企业在历史洪流中兴衰的描述只是围绕着这一落脚点展开。这些例证点到为止,它很像一幅混合着政治史与经济史的《清明上河图》,从中标出了一条两者相互纠葛的红线,让人们明白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种种思考。吴晓波以一种不是学术写作的方式试图找到一个具有学术深度的答案。
吴晓波的文字有种无形的力量,似乎总能带动阅读者进入一种状态,引发一种情绪。面对作者笔下的世界,那是一种感慨与激荡同时迸发的情绪,加之对人物的细节描写,极易令人产生出某种情感上的呼应。书中不仅梳理了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梳理了相关的学术研究结果。这样的梳理当然可贵,只是它不像学术文章那样最后罗列出明确的一二三来。
对中国式商业困境书中并没给出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只是让读者更加明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和特点。循着感性的出发点经由理性的解剖最终从历史中剥离出带有主观设定的逻辑结果,似乎是研究历史的宿命。作者在写作结束时的怅惘实在是渺小生命面对浩瀚历史时的真情写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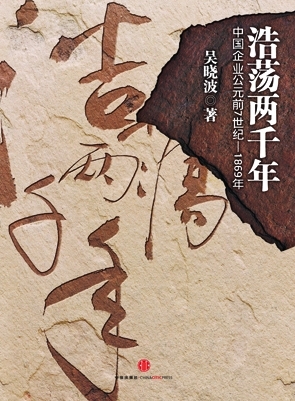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