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老的朋友张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
张奚若家没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长期的小摩擦。他同杨景任的结合是新式的结合,他有过旧式的结合。所谓“旧式的结合”是把彼此不认识的双方经媒人说合成婚。张奚若的头一次结婚是怎样了的,我不知道。杨景任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他们是在苏格兰结婚的。结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见他们。这个结合是自由式的。张奚若头脑里想的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发现杨景任不是“知识分子”,假如所谓“知识分子”是用知识去办大事,像他自己那样。杨景任不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说的Womanly woman(女子女子),这实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性。要看她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听她同萧叔玉太太的谈话,两人都争分夺秒地谈,由赵、钱、孙、李到黄焖鸡到红烧肉。杨景任这一方面的性格虽然突出,然而她总是支持张奚若的。从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担,显然是勇于负责的事。
张奚若这个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权论沿革》,登在《政治学报》月刊或季刊上。这个刊物只出了一期。据我的记忆,经手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杨景任女士。那时候她在上海读书。以后没有多久,她也到苏格兰念书去了。
他是作为革命的青年到美国去的,同去的人有王夏将军。他确实得到扎实的书本知识,但是,忽略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乡的老办法去办。例如要裁缝给他做一身新衣服(美国的低收入的人不缝衣服,买衣服)。裁缝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里之后,裁缝仍不肯改。我说,“找我们的律师去”,旁边有一个人听了就说,“哪里不合身,让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确实应该改,也容易改”。问题在于“我们的律师”。这表示中国学生是有法律顾问的,不只是临时找律师而已。
从那个时候起,奚若认为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这样一个“认为”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到了昆明之后,才打住了。
有一天傍晚,约6点钟光景,年轻小伙子唐二哥来了。这里说的是昆明。他说他早就到了西南联大广场,张伯伯已经在那里讲演。他站在那里听,他说张伯伯要求蒋介石辞职。这是我离开上海之后,头一条好消息。我可惭愧不堪,我不知道奚若要做如此重要的政治一步。真是对不起朋友。后来我要唐二哥到奚若家里去了次,我很高兴唐二哥得到了大后方的政治气氛。
30年代中期,送张奚若回西安,我写了一篇游戏文章:
敬启者朝邑亦农公奚若先生不日云游关内,同人等忝列向墙,泽润于“三点之教”者张奚若讲话总喜欢说:“我要讲三点……”金先生跟他开玩笑,称他为“三点之教”者。数十礼拜于兹矣。虽鼠饮河不过满腹,而醍醐灌顶泽及终身,幸师道之有承,勿高飞而远引,望长安于日下,怅离别于来兹。不有酬觞之私,无以答饮水思源之意,若无欢送之集,何以表崇德报恩之心。兹择于星期六下午4时假座湖南饭店开欢送大会,凡我同门,届时惠临为盼。
门生杨景任
再门生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成、林徽因,陈岱孙,邓叔存,金岳霖启
陈岱孙很能办事
哲学所从前有一位青年同事曾大声说:“我发现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我没有多少知识,可是,早已被安排在知识分子之内,而我又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就证实了他的话。但是,还是要承认有非常之能办事的知识分子,陈岱孙先生就是这样一个。
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住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给他写的条子如下: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是有条件办伙食。
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
陈岱孙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成员之一。认识了这样长久的老朋友,他能办事,并且能办大事,我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怪事!
到了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住在昆明北门街唐家家庭戏园的后楼上。这五个人是朱自清、李继侗、陈岱孙、陈福田、金岳霖。那时虽有教学,很少科研,经常吵吵闹闹。对陈岱孙先生,我可以说更熟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他能办事。可是梅校长知道,他知道陈岱孙先生能办事,所以在大家回到清华园以前,他派陈先生回北京做恢复清华园的麻烦工作。
清华校园受到日帝军队的破坏,糟蹋得不像样。教员的宿舍也成为养马房子。陈岱孙先生居然在短期内把清华校园收拾到原先一样,重办大学。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
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
(本文摘自《金岳霖回忆录》,金岳霖著,刘培育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定价:26.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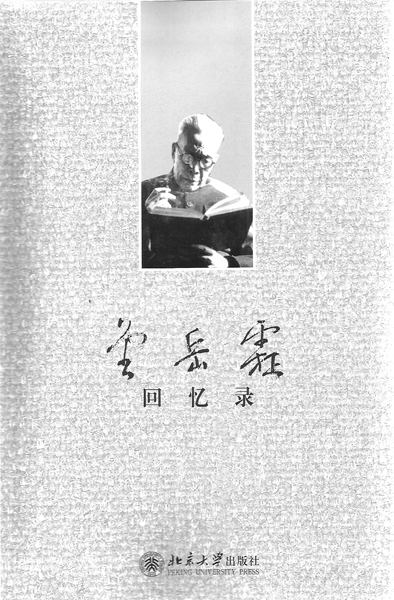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