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墓和赛文墓并立在草地上。济慈墓碑上刻有浮雕,是一只古希腊里拉琴,应该有八根弦,但四根已断,只留下四根,意味着诗人的天才未发挥净尽即被死亡掐断。碑上遵济慈的遗愿不刻他的姓名,只刻着他自定的碑文:“用水书写其姓名的人在此长眠。” 济慈的生死之交赛文墓紧挨着济慈墓,墓碑上刻着画板和画笔,表明他的画家身份。碑上的文字是:“约瑟夫·赛文,约翰·济慈的挚友和临终伴侣,他亲眼见到济慈列入不朽的英国诗人中。”
一
在小女儿的陪同下,我于几年前访问了济慈故居(伦敦)和济慈临终住所纪念馆和墓地(罗马)。
济慈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倾心于他。他22岁时得了肺病,我也是22岁时得了肺病。他25岁即死去。我也曾自忖过只能活到25岁。(解放前生活贫困,肺病特效药还没有产生。我的同窗好友年纪轻轻即死于肺病,我自以为也不能幸免。)济慈迷于诗,我也迷于诗。于是我把他当做超越时空的冥中知己(不把他当做古人,而是当做朋友)。当然,他是大诗人,我只是渺小的诗爱者,不能相比。“文革”中,我在“干校”劳动,是济慈的诗成为我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之一。那时这类洋书在我的家中已经绝迹。1966年,“红卫兵”冲击私人住宅时造成许多惨剧,我不得不把大批英文原版书籍撕去封面封底称斤卖掉(每斤2分)以免祸及家中老人。但济慈的诗我能背诵,这是任何“造反派”都拿不走的。我译济慈的诗,始于20世纪40年代。到了90年代初,任吉生女士(当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约我翻译济慈,我花了三年时间,译出济慈的几乎全部重要作品。
1999年,新闻出版署主办第九届国家图书奖工作时,评委会副主任委员季羡林先生特别提出将《济慈诗选》列入初评入选书目(事先《济慈诗选》没有上报,是季先生见到书后提出的)。但复评时落选了。
后来,正巧在我访问济慈故居的差不多同时,在绍兴,与鲁迅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相结合举行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大会。此时我不在国内,根据作家协会的通知,我的儿子蒋宇平代我到绍兴领了奖。据告,《济慈诗选》是全票通过,按照票多少排名次,它排在鲁迅文学奖七个奖项之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第一名。鲁迅是我最敬佩的现代中国伟大的作家、思想家。这次奖以鲁迅命名,是对我极大的荣誉。——但,我也没有太激动,对我来说,荣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奉献,是把尽可能好的译作奉献给亲爱的读者。能写好诗,译好诗,奉献给读者,这比什么都重要。
二
伦敦的济慈故居位于这个大城市的西北部汉普斯泰德区,现在也是较繁华的镇,在济慈的时代还是偏僻的郊区乡村,附近是丛林和草地。济慈在这里住过一个不太长的时期。1818年12月,济慈的弟弟汤姆死于肺结核,他的好友布朗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同住,这就是现在的济慈故居。济慈一度离开此宅,后又住入,直到1820年9月他赴意大利为止,不到两年时间。在这里,他写出了他最主要的作品,六首颂、《圣亚尼节前夕》、《海披里安》等。
我和女儿访问了伦敦西敏寺,特别流连于那里的“诗人角”——其中莎士比亚塑像的上方就有一块纪念济慈的圆石板。下午便与女儿赶到汉普斯泰德济慈故居访问。(这已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来时恰逢星期一不开放。)这个地方原名“温特沃斯宅”,现名“济慈故居”,又名“济慈林舍”。房屋所在的街道也命名为“济慈林舍路”,路对面是圣约翰教堂。地方很幽静。故居是一幢独立的两层楼建筑,楼上楼下共有六间房间,当年住三家人家。还有地下室,包括厨房、贮藏室等。房屋坐落在一个不大的花园中。屋墙是白色的,在绿色的树木和草坪中显得格外清幽。楼上有济慈的卧室,楼下有济慈的起居室,室内的一些家具有些是原物,有些则是按当时的原貌仿制的。玻璃框里陈列着他的手稿、出版诗集等珍贵文物,济慈的代表作《夜莺颂》就在这里诞生,据布朗在给友人的信中说,1819年春天,这里前院绿地上有棵李树,李树上有一只夜莺的巢。济慈听见了夜莺的歌声,感到一种宁静和持久的愉悦。一天早晨,济慈从早餐桌旁端起一把椅子,放到院子里绿地上李树下,坐了两三个小时。布朗说,当济慈回到屋子里时,他见到济慈手里有几张小纸片,他什么也没说,就把纸片塞在书堆后面。这就是《夜莺颂》的原稿,是布朗把纸片捡起保存了下来,流传到了今朝。今天,故居前院还有一颗李树,但不是当年的,是后人新植的了。我在这棵树下徘徊了良久。
布朗曾把温特沃斯宅的部分房间出租给狄尔克一家和布劳恩太太一家。布劳恩太太是个寡妇,有一个女儿芳妮。济慈认识了芳妮,一见钟情,坠入爱河。济慈的一些著名的爱情诗就是写给她的。他们于1819年订婚。济慈曾一度离开温特沃斯宅,住到他的另一位好友李·亨特家中。亨特粗心大意,误拆了芳妮给济慈的信,济慈不高兴而离去,回到温特沃斯宅。此时济慈的肺病已日趋严重,芳妮和她的母亲悉心照料济慈。这是济慈在英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是他一生中最温馨的一段时间。但病情未见好转。医生认为伦敦的冬天不利于济慈,劝他到温暖的南方过冬。济慈只好听从医嘱,前往意大利,那是在1820年9月。陪同前去的是济慈的好友、画家塞文。济慈与芳妮这一别,就是永诀。当次年2月济慈逝世的消息传到伦敦时,芳妮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悲痛欲绝,面上光彩尽失,头发变色。她为济慈穿丧服四年(一说六年),之后,又守了八年独身生活。一位朋友在书信中说到芳妮当时的情况:“济慈与之相爱并准备结婚的,是一位美貌的少女,现在她正憔悴得骨瘦如柴,我相信不久她会随济慈而去。”芳妮在给济慈妹妹的信中说:“他(济慈)的朋友们都已从这次巨大的打击中缓过来了,他们以为我也会缓过来,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芳妮到33岁的时候才与林登结婚。她活到65岁,而济慈赠给她的订婚戒指她一直戴在手上,直到死。现在济慈故居楼上有芳妮卧室,其中就陈列着那枚订婚戒指。
三
在这之前,我和女儿到罗马,访问了三圣山下的另一故居。这是一座三层楼的意大利民宅,坐落在罗马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上。广场上广阔的台阶之上是名胜地三圣山。济慈于1820年9月由赛文陪同从伦敦乘船赴意大利,11月抵达罗马,住在这里。他的病曾一度好转,但12月大咯血,病情急剧恶化。次年2月23日,病逝于此。这个故居现在称做“济慈、雪莱纪念馆”。19世纪末,这座房屋面临着被拆毁的危险。意大利的济慈、雪莱纪念协会购买了这座房屋,并建成了济慈、雪莱纪念馆。事实上雪莱并未曾住在这里,但雪莱在罗马住过。
在最后的日子里,济慈一再要求赛文把一种名叫“劳丹酊”的药给他,这是一种强烈的麻醉剂,能致人于死。他想自杀。他对赛文说:“既然我必死无疑,那么我只是想把你解脱出来,使你不至于长期服侍我,眼睁睁地见我死。死亡可能迟迟到来,我知道这会使你缺乏经济来源而陷入困境,你的前程也会因此破灭。我已经使你停止了绘画,那么既然我必有一死,为什么不现在就死?我决定吞服劳丹酊,使迟迟来到的死亡早日来到,同时把你解放出来。”这使赛文大惊。赛文好言安慰他,又把药藏起,最后交给了医生。济慈因不能如愿而发怒、哀求、甚至大怒,最后才慢慢平静下来。医生一天来看他几次,济慈因消瘦而眼睛显得很大,淡褐色愈来愈明显,他的眼睛射出一种非人间的光彩。他用这双眼睛望着医生,用一种带有深沉悲怆的声音问:“我这Posthumous生命还能维持多久?” Posthumous是“死后的”。他认为自己实际上已经死了。最后,赛文在给布朗的信中说:“他已经去世了——他在最恬淡的心境中死去——他似乎入睡了(23日星期五)四时半死神来临……‘赛文——塞——抱我起来,我正在死——我要死得安详——不要害怕——感谢上帝,它[死]来了’——我用双臂把他抱起,痰在他的喉咙里好像沸水一样——这状况延续到夜里11时,他渐渐沉入死亡——如此宁静,我还以为他在熟睡。”济慈索求劳丹酊时对赛文说的话令我万分感动,从中可以窥见济慈的人格。我读赛文给布朗的信时竟湿润了眼睛。
济慈死后,葬在罗马新教徒公墓。同日下午,我和女儿找到济慈墓地,向他凭吊。济慈墓和赛文墓并立在草地上。济慈墓碑上刻有浮雕,是一只古希腊里拉琴,应该有八根弦,但四根已断,只留下四根,意味着诗人的天才未发挥净尽即被死亡掐断。碑上遵济慈的遗愿不刻他的姓名,只刻着他自定的碑文:“用水书写其姓名的人在此长眠。”济慈的生死之交赛文墓紧挨着济慈墓,墓碑上刻着画板和画笔,表明他的画家身份。碑上的文字是:“约瑟夫·赛文,约翰·济慈的挚友和临终伴侣,他亲眼见到济慈列入不朽的英国诗人中。”
四
在英国浪漫主义六大诗人中,人们常常把济慈和拜伦、雪莱并提。并且排位在后。的确,过去拜伦、雪莱对世界的影响比济慈大。鲁迅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特别推崇拜伦,把他列为“摩罗诗人”之首。(“摩罗”即反抗者、叛逆者,指反抗旧世界、旧秩序者。) 拜伦晚年支援希腊独立,摆脱土耳其统治,倾其家产,亲赴希腊,组织“拜伦旅”,竟以身殉。当时中国处于半封闭半殖民地地位,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强、民主、自由,所以鲁迅推崇拜伦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鲁迅也推崇雪莱, 雪莱曾被马克思誉为“真正的革命家”。而济慈过去曾被目为唯美主义者,而唯美主义者在一个时期内是贬义词,因为他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就是漠视国家、社会、人民。其实这是对济慈的误解。济慈在他的诗作中歌颂民族独立,反对专制压迫,渗透民主精神。但他的民主精神并不都体现在具体的政治事件的描述中。他的民主倾向同他的诗歌美学统一在一起。他所歌颂的美,是一种政治倾向的审美折射。
在罗马济慈故居的陈列物的描述中,有一段代表当今诗歌评论动向的文字,译如下:
拜伦上个世纪(19世纪)在意大利享有巨大声誉。他与意大利‘调和者’集团和烧炭党人的接触保证了他在意大利爱国者中间享受荣誉,获得成功。……雪莱在意大利的声誉稍逊于拜伦,来得也迟些。……济慈当年在意大利没有得到爱国者的称赞也没有得到诗人们的尊敬。但是今天,在意大利,济慈已被认为是上述三位诗人中之最伟大者。欧金尼奥·蒙塔莱把济慈列入‘至高无上的诗人’之中。
(按:蒙塔莱是现代意大利诗人,被称为意大利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罗马济慈故居访问时,遇到纪念馆工作人员,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女士,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和蔼,有问必答。我原以为她是意大利人。我访问伦敦济慈故居时,又见到这位女士,原来她是英国人,在两个济慈故居轮流工作,这回是回到英国了。我们一见面,好似熟人似的。我把我译的《济慈诗选》交给她,作为我给济慈故居纪念馆的赠品。她高兴地接受了,询问我译了济慈的哪些作品,我一一回答了。她说,她将把这个中文译本收藏在济慈故居的书库中。
开始写这文时,天气温和,户外树叶还是绿的。文写完时,气温大降,西北风敲窗怒吼,树叶枯萎,大半被风卷落。我想起济慈的《秋颂》:“雾霭的季节,果实圆熟的时令”,也想起他的一首十四行诗:“刺骨的寒风阵阵,在林中回旋,低鸣,树叶一片片枯萎,凋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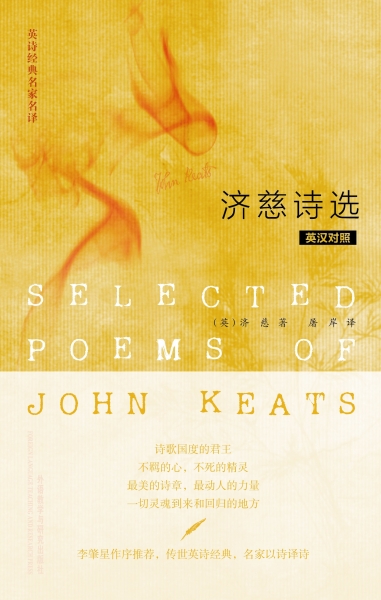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