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被称作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位先驱。两人早年在哲学道路上的共同探索让人印象深刻,后来他们之间相互提出异议,并强调各自哲学观点的不同,但从未公开论战。本文梳理了“雅海”书信以及两人半个世纪的交往过程,汉代古诗中有“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的句子,这两句诗同样也可以对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半个世纪的友谊作很好的概括。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就经常被人称作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位先驱。他们在哲学道路上的共同探索,似莫逆之交的形象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们之间相互提出异议,并强调各自哲学观点的不同,但从未公开论战。因此对这两位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大师之间私人关系的研究,一直为西方学界所关注。
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差不多属于同一个时代。雅斯贝尔斯(1883年出生)比海德格尔(1889年出生)长6岁,出生于奥登堡一个信仰新教、思想自由的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而马丁·海德格尔则出生于施瓦本—阿雷曼地区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农民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当地小镇上的一个教堂的司事,家境十分贫寒。他后来除了在马堡工作过五年之外,在古代阿雷曼人这块极小的土地上度过了他几乎全部的生涯。他那震撼整个哲学界的思想,也是在德国西南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酝酿、完成的。
对他们俩来说,哲学意味着对自由的保证。学过神学的海德格尔试图借助哲学的帮助,从狭隘的天主教的信仰世界中找到一条出路;学过医学的雅斯贝尔斯则希望通过哲学的帮助,去超越自然科学中的教条主义的界限。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哲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亦即以此来理解那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用一种隐蔽且困难的方式去寻求哲学家的上帝。后来,他们赋予这个上帝一个相同的名称:“存在”。
一
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当海德格尔在生命的自我透视的哲学道路上摸索、探求并确立其范围时,雅斯贝尔斯也在寻觅着哲学的一个新的开端。这时,两个学者之间的艰难的友谊开始了。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相识于1920年春季,在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家中举办的一个令人愉快的晚会上。胡塞尔是海德格尔早年的老师。经过一年半小心的接触,雅氏与海氏于1922年的夏天终于在一种“很少有的、自主战斗集体的意识”中结成了友谊。
雅斯贝尔斯在当时的哲学界人士的眼里还是一个门外汉。他原本从事医学中的精神病理学研究。早在1913年他就以一本《普通心理病理学》的著作而一举成名,获得了在海德堡大学教授心理学的资格,“这部著作已经显示出他精神中那种视野广阔、联想丰富的专门才能”,并很快就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性著作。但是,雅斯贝尔斯却开始脱离医学这个领域。他特别清楚地认识到病人那种模棱两可的情况,而这种精神上的疾病是用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精神病学无法充分解释的。雅斯贝尔斯出于自身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孤寂感受以及对疾病威胁的敏感意识,而一再追问生命的意义。但“科学的知识在面对一切根本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能阐明真理以及我们生命意义和目的的哲学。跟马克斯·韦伯以及基尔凯郭尔的相遇则是他转向哲学研究的关键。
雅斯贝尔斯于1919年出版的《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标志着他从心理学的研究转向了哲学的研究,这本书完全超越了专门学科的范畴。雅斯贝尔斯用韦伯关于观念类型构造的方式来研究从人类的生活经验中——特别是从人类的基本问题,例如自由、罪责以及死亡中——产生的“观点和世界观”,正是它们给当时的哲学构想描绘出了一种独特的轮廓。他在这里探究的是如何克服对自由的恐惧以达到自由,并且让我们在内在活动中自由地选择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历史地来看,这本书是作为后来被称作存在哲学的最早著作而问世的,它几乎涵盖了存在哲学中所有最根本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的处境以及他根本无法逃脱的“临界状况”(死亡、痛苦、意外事件、罪责、抗争)。雅斯贝尔斯认为,人正是在这种临界状态之中接触到超越的,而通过这个接触,人实现了自己的存在。关于这本书,他在《哲学自传》中写道:“所有这一切就像在一种迅速的捕捉中被领悟一般……整本著作的观点要比我以后成功地讲述的内容全面得多。”
这部著作使哲学界出现了新的声音。公众的反响是如此之大,以致雅斯贝尔斯虽然没有哲学博士的头衔,却于1921年在海德堡获得了一个哲学教授的席位。雅斯贝尔斯之所以将他的这本书命名为“心理学”,实际上是利用心理学的方法来阐明他的哲学,进而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区别开来。不过这也使得他的哲学教授的职位变得有些含含糊糊,他因此受到来自两个领域的攻击:科学家按照自己严格的惯例,将他看作是科学的背叛者,是那种从事不确切事物,即哲学研究的人;而在哲学家的眼里,他是那种走在心理学旁门左道上的哲学教授。
雅斯贝尔斯对此并没有加以反驳。他感到自己正处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因此,当海德格尔于1921年8月5日写信谈到自己哲学工作的性质时,他特别能够理解海德格尔:“我是否也要到空旷的地方找到我的路,我不知道;或者我只能走这么远,就此打住了,或者我本来是否要走,都不知道。”
此时的海德格尔还只是一个大学的无薪讲师,并在弗莱堡给胡塞尔当助手。他还没能发表任何能使他声誉鹊起的著作,但却已为人所知,因为他频繁地举办演讲和各种研讨班。海德格尔通过意识完成了对意识的无止境的自我观察,并将哲学的重点放到了日常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上。人们感觉到,海德格尔的这种做法是一种解放。他的哲学思考强烈要求与生存的关系。和雅斯贝尔斯一样,对自身的忧虑是他研究的主题。
海德格尔在雅斯贝尔斯身上感到了相似的动力。因此他写了一篇有关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的书评——“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并于1921年6月寄给了雅斯贝尔斯。由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并未真正论战过,他们以后在思想上也没有真正交过锋,这篇书评就成了分析哲学思考的唯一书面文件。
海德格尔首先对这本书极尽赞美之词。接着,他就以极其谨慎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雅斯贝尔斯的研究显然不够深入。他虽然“描述”了生存的发生,但并没有将自己的思考“深入”到这个生存的发生之中。他还躲在一种科学的保持距离的态度背后。海德格尔在书评的最后写道:“如果存在一种真正的自我思考,那么人们只能理智地将其公开。而这种自我思考在此存在,并且只可能存在于严格意义上的被唤醒之中。而真正的被唤醒只能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毫无顾虑地将他者推入反省之中。为了推入反省之中,让人关注,他自己就只有先行一步了。”而只有当他领会了哲学的“事物”,他才可能先行一步。这个哲学的“事物”是指“哲学思考着的自身及其显而易见的贫乏”。
雅斯贝尔斯没有将这种所谓的“贫乏”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从上下文的联系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里指的是人类的一种贫乏。所以,雅斯贝尔斯并没有因这篇书评而生气,不过这篇书评却让他无所适从。因为他不知道海德格尔所要求的,人不应该只是探讨“关于”生存的发生,而应当“跳出”这种生存发生来进行哲学思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或者是海德格尔误解了雅斯贝尔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雅斯贝尔斯已经走上了“自我忧虑”的哲学道路;或者说是海德格尔对这条道路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他的解释又不是很清楚。可以肯定的是,雅斯贝尔斯没有看到,海德格尔有沿着他的这条道路走下去的意思。尽管如此,雅斯贝尔斯还是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雅斯贝尔斯在晚年时依然对海德格尔的书评心存感激,他认为跟李克尔特想打压他的心态不同,“海德格尔却极彻底地读了这部著作,通过他一篇并未发表的批判性书评,以其比其他一切都更加毫不留情的方式,对我的著作提出了疑义。这对我来说无异于肯定了一个新的开端。”1921年8月1日,雅斯贝尔斯写信给海德格尔:“您的评论文章是我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深刻地挖掘了思想本质的评论。它确实触动了我的内心世界。但我还是怀念我们在讨论‘我存在’和‘历史性的’所采用的那种积极的方式。我在文章中始终感到了一种向前的动力,但后来往往很失望,并发现自己已经如此远离了自己的初衷。”
在回信中,海德格尔称自己的书评是一项“荒谬且又可怜的初级事业”。 他的本意是,“我并不幻想会在这方面比您自己走得更远,尤其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走些弯路了”。两人之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和谐。雅斯贝尔斯原本想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更多的赞扬,而海德格尔则希望雅斯贝尔斯能对他深刻的批评给予更多的肯定,海德格尔把这理解为他们之间友谊的一个重要行为。雅斯贝尔斯为自己没有公开对海德格尔书评的看法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因此我推测海德格尔会很失望的。不过他深入到我的这本书的内容和重要的观点之中去——批评少于对话——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激励我的积极因素。”但在当时,他们之间的通信为此中断了近一年之久。并且海德格尔书评中所表现出来的苛刻态度,使雅氏始终不能释然。
后来,雅斯贝尔斯于1922年夏天邀请海德格尔到海德堡呆几天,海德格尔接受了邀请。9月的这几天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味着这几天的经历,因为将来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将建立在这些实际的经验之上。对哲学的强烈感受、和睦的沉静气氛以及启程和开始时共同的骤然感觉——正如雅斯贝尔斯后来回忆时所写的那样——“征服”了他,并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使他感到自己和海德格尔之间很“亲近”。
在这段时间里,海德格尔经常到雅斯贝尔斯位于海德堡的家中做客,他们俩真正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几。在具体描绘当时昼夜相伴的日子时,雅斯贝尔斯说:“海德格尔来我们家做客时,我跟他通常是在工作。每天我们都要聚几次来交谈。前几次的谈话就已经令我倍受鼓舞了。没有谁能够想象我对能跟他相处感到多么地惬意,他至少是在哲学家阵营中唯一能跟我真正交流的人。”
二
这种友谊在其初始阶段是如此令人振奋,因此雅斯贝尔斯建议,创办一本只由他俩写稿的杂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哲学的“火炬”。最后,人们不得不在“哲学的荒芜时期”对学院哲学提出抗议,反对一个庞大的、普遍有效的价值体系。他们俩共同认为,表面化的、远离生活的学院哲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它们所讨论的事物对于人的存在等基本问题并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他们相约建立一种新哲学,以期改变学院哲学的传统。但是,作为哲学教授的雅斯贝尔斯随后便想到,这一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此时海德格尔还没有任何教席。所以,办杂志的项目要等到海德格尔被任命为教授之后。而此时,海德格尔还在焦急地等待教授的职位。
事实上,海德格尔在1922年和1923年夏天,在自我澄清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从海德格尔1922年底作为求职论文寄往马堡(直到1989年才被重新发现)的学术论文德文本卷宗《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诠释》,以及1923年,即他即将走马上任马堡大学教授之前在弗莱堡的最后一学期所开设的关于本体论的讲座中,都可以看得出《存在与时间》思想的端倪。
那些写给雅斯贝尔斯的、充满着战斗意识的信件表明,海德格尔想充当收拾哲学界这个烂摊子的海格力斯的角色。他沉醉于“彻底的哲学改造和彻底变革”的幻想之中。1923年的夏天,海德格尔才发现自己是海德格尔。
这个夏天在弗莱堡举办的关于存在论的最后一次讲座中,海德格尔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事业。他愉快地告诉雅斯贝尔斯:“我将书籍以及文学上的装腔作势都丢给了世间,而引来了年轻人——‘引来’的意思是严厉地抓住他们——因此他们在整个一星期都是‘有压力的’;有些人忍受不了——这是选择的最简单方法——有一些则需要二到三学期才能理解,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允许他们:懒惰、肤浅、欺骗和空话——特别是‘现象学的’空话的原因。您知道,我是从来不让学生做什么报告的,——只有讨论,并且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讨论——突然产生的念头以及辩证法的游戏我也是不允许参与到讨论中来的——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准备,也就是说对各自事物的全身心投入,这跟写一本书和再写一本书相比,只有其一半的舒适度。我最大的乐趣在于,在这里通过示范实现转变,以及我当下的自由。”
但是在1923年这个令人愉快的夏季却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1923年7月14日,就要离开弗莱堡赴马堡大学接受哲学副教授一职的海德格尔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表现出了对他的老师胡塞尔的极端不满情绪。雅斯贝尔斯在当时并没有对此加以评论,不过海德格尔的人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大打折扣了。无独有偶,雅斯贝尔斯后来发现,海德格尔背后对人轻蔑、尖刻,当面则变成了奉承或不敢承认。这种行为模式在雅斯贝尔斯以下所经历的事件中得到了证实。
雅斯贝尔斯给海德格尔寄过一本他的著作《大学的观念》。但不久,就有人告诉他,海德格尔在他的学生面前说,“这是当今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最无足轻重的东西。”1923年9月,当海德格尔再次拜访雅斯贝尔斯时,雅斯贝尔斯向他指出:他并不是不允许他作这样的评论,但是作为朋友,他应当事先直接地告诉他本人。海德格尔马上否认道,他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雅斯贝尔斯回答:“那么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解决了,我相信您。”但事实并非如此。一种怨恨和怀疑的情绪,在雅斯贝尔斯的心中挥之不去:交不忠兮怨长。后来,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他似乎是这样一位朋友,当你不在场时,就会出卖你。不过在瞬间,你又会发现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是觉得他是你难以忘怀的亲密朋友。在我看来,似乎是有一个魔鬼混入了他的体内,所以,出于对他本质精神的喜爱,我要求自己,不去理会他的这种失礼。”庄子说:“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这是古今中外朋友相处最基本的道理,显然,海德格尔违背了这一友谊之道。
三
1923年秋季,海德格尔来到了马堡,1928年春季他又离开了这座城市,前往弗莱堡去接替胡塞尔的教授席位。在离开马堡之前,他写信给雅斯贝尔斯:“有关马堡的事情我无法给您历数。我没有一刻感到舒服的。”但是,后来海德格尔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又称这些年是他生命中最令人振奋的、收获和经历最为丰富的时期,同时也是最幸运的时期。
海德格尔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对这段马堡生活时期的负面评价也有着其战略上的意义。当时,雅斯贝尔斯曾考虑离开海德堡,因此他想从海德格尔那里知道,能否为自己在马堡任职提供一些建议。但海德格尔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这些年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作为一个副教授又能帮上雅斯贝尔斯什么忙呢?这其中的原因不单单是大学的环境,同时也是因为他经常往来于马堡和托特瑙贝尔格之间,很难顾及到雅斯贝尔斯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让雅斯贝尔斯知道他跟自己年轻貌美的犹太裔女学生汉娜·阿伦特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
1924年,阿伦特在马堡大学遇到了海德格尔,这时她才18岁。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35岁的海德格尔正在酝酿《存在与时间》的写作,阿伦特出现在了海德格尔的课堂之上,在他们四目交会的刹那,阿伦特的貌美和睿智,海德格尔的深邃和厚重,使他们一见倾心,很快便成为了两相愉悦的情人。当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没有任何结果时,海德格尔将阿伦特推荐给了他的好朋友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则在听了一年胡塞尔的现象学课之后,去了海德堡。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论奥古斯丁爱的观念》的博士论文。而对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的恋情,雅斯贝尔斯却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略有所知,并且不是从他的朋友海德格尔那里,而是从他的学生阿伦特那里。当时,海德格尔为了避免麻烦,将他的这位学生送到了海德堡。又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但不管怎么说,雅斯贝尔斯还是对阿伦特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慈爱之情,而阿伦特一生对雅斯贝尔斯夫妇都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这些都可以从他们之间持续44年的几百封通信中看得出。
海德格尔主要从自己的哲学出发对《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予以了评论,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书评了,但其中对雅斯贝尔斯的严厉批评一直都让雅氏难以做到心境坦然。后来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的时候,雅斯贝尔斯承认对此书毫无兴趣,认为这是一本毫无新意并且充斥着生造新词的失败之作。
而在1946年《普通心理病理学》修订版的后记中,雅斯贝尔斯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想提供知识的企图,是一种错误的哲学途径,他写道:“尽管他的具体说明有价值,但是,在原则上,我认为这种企图是错误的哲学途径,因为它将人带到了人之生存的整个概念的知识上去,而不是带进哲学的思索中。这种思想的结构,对于个人历史性的具体存在没有裨益(作为加强并确定其生活的实践),只能成为另一个更有害的妨碍,因为正是由于这种最接近于‘存在’的意见,才使得真正的存在易被错过,从而变为不重要的东西。”
反之,海德格尔却认为雅斯贝尔斯的哲学的深度不够,他的哲学思考和不断超越的活动,实际上是在逃避真正至关重要的存在的问题。
两位哲学家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者的思想风格的不同使然。雅斯贝尔斯所拥有的绝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和情感,他认为哲学是当下的、是跟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息息相关的。而海德格尔的思想高度,决定了他的哲学是无条件的孤独和不可交流。他对最复杂的哲学术语的追根溯源,以及《存在与时间》在结构设计上的精密,都明显来自他那扎实厚重的学院哲学背景。《存在与时间》在出版后不久就被认为是20世纪欧洲哲学中真正划时代的著作。今天看来,这一说法并不过分,因为它对欧洲哲学、文化乃至技术的影响,是任何著作所无可比拟的。平心而论,上述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尽管有他的道理,但实际上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研究者很容易证明,雅氏1932年出版的集他思想大成的三卷本巨著《哲学》一书的许多观点和方法明显受到过《存在与时间》的影响。而雅斯贝尔斯的信奉者们却相信,正是由于雅氏这套洋洋洒洒的《哲学》一书,才使得海德格尔放弃了出版《存在与时间》下半部的计划。实际上这正显示出了两位哲学大师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思想上的相通。伽达默尔在论述两位大师在思想方面的异同时写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从根本上说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追问方式,这种追问方向要返回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向度上去。……雅斯贝尔斯固然也吸收了海德格尔以‘存在式的’名义耕作的土壤,但他作为海德堡学术界的教师首先还是选择了基尔凯郭尔存在辩证法的思想加以阐述。”这样的一个结论,可以说对两位哲学大师都是比较公允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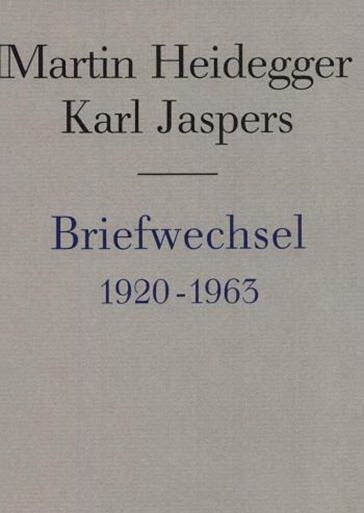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