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发微》是余嘉锡多年教授“目录学”的集成之作,也是研究目录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此书仅十余万字,从史学的角度出发,阐明了目录学的意义功用、目录学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目录类例的沿革等,以客观、发展的眼光看待目录学的产生、流变,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向有所预期,对目录学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问题,做了明确、中肯的结论。其中关于目录学可独立成学、目录学即学术史、目录书类是发展的等论述,特别值得关注。
目录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学界的看法仍不一致,还有人认为目录学应当从属于校雠学。目录之名,起于刘向、刘歆校书之时。汉以前书籍多是以竹简、木牍为书写材料的,其既笨重,所写字数又少,故图书多单篇别行。基于图书这样的流传形式,校书必须先编书,第一广集众本; 第二审阅篇章,删去重复,确定所存篇章; 第三通过校雠考订讹误。所谓“校雠”,即刘向所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然后“改易刊定”所发现的讹误,可缮写者即可上素、誊写,再冠以确定的书名,这样校书中编书步骤即告成。编目就是由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最后由他的儿子刘歆根据这些书录编撰成我国第一部综合书目《七略》,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改编《七略》而成,对后世目录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由于纸的发明和普遍使用,改变了图书单篇别行的状况,撰著群书目录,不再需要编书,更不必校雠。宋代郑樵撰《校雠略》,论图书的搜求、整理、编目,实际上是研究目录学理论的论著,遗憾的是,他以“校雠”定目录之名,对后世造成深刻影响。清代章学诚亦以《校雠通义》命名其论目录学的专著,并称“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余嘉锡从正名的角度,指出郑、章诸人犯了以点盖面的概念错误,称“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雠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渔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雠,命名已误”。认为目录学自可独立成学。时至今日,仍有人坚持目录不能自立为学的观点,甚至将目录、版本、校勘三学共统于校雠学之下。由此可知余嘉锡正视学术的发展与专学的分野,指出郑、章谬误症结之所在,有多么重要,现在仍具有生命力。
余嘉锡明确指出目录学“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他区分了我国历代书目不外三种类型,并说明了各类书目的特点,指出不论哪种书目,它的宗旨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对我们了解我国古代书目的特点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了深入说明这个问题,作者从目录的篇目、叙录、小序、板本序跋四方面阐述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篇目及版本序跋考一书之源流,前者考其内容,后者考其流传。著有篇目,即可知此书的篇数、顺序,乃至简明要旨,就能勾出此书的大致构架,这从《史记·太史公自叙》、《汉书·叙传》皆开列篇目,得到印证。在图书单篇别行的情况下,篇目著录尤显必要。图书流传经过载体,以及书写、雕版的变化,其间纷纭复杂,余嘉锡条分缕析,厘清其始末。值得注意的是,他关注目录迻录他人序跋,考证出此举始自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而在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其书除主采晁公武、陈振孙书外,时从文集及本书抄出序跋,间有书亡而序存者,亦为录入。余嘉锡对此颇为称道,曰“虽不完备,然其体制极善,于学者深为有益”。与其同时代的目录学家莫伯骥撰《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即大量迻录他人序跋,故五十万卷楼藏书虽毁于抗日战争时期,但还能通过《初编》,对其有所了解,可谓是不幸中之大幸矣。同时也证明了余嘉锡赞同目录迻录他人序跋,是多么有远见。
余嘉锡认为刘向作叙录,与司马迁、扬雄自叙大体相同,其体制似列传,对于作者之功业学术性情,并平生轶事,凡有可考,无所不尽。汉魏六朝人们作书叙,也是以叙述作者生平事迹及其学问为主。这就能说明目录学即学术史。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余嘉锡从作者之行事、作者之时代、作者之学术三个方面分而论之。其间他提出的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王俭作《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他指出此作法以变叙之名,从传之实,其原因则是叙录本与列传相近,点出传录体目录产生的必然性。其次,言及叙录在最常见的史志目录中的变化。班固取《七略》作《艺文志》,虽删去叙录,然尚间存作者行事于注中,这是为遵修史之体例; 《隋志》只载官爵;宋、明史志只记姓名。从而不难看出,史志目录对叙录的逐渐淡化。《新唐书·艺文志》的作法,则略有新意,撰述人未立传者,就详注始末于《艺文志》。这些变化,对于考镜一人之流的叙录,意味着什么?后人又当作何思考呢?再次,提醒撰目录者,“自揣学识未足衡量百家,不如多考证而少议论,于事实疑误者,博引群书”。又强调作目录不同于私人著述,旨在成一家之言,必须博采众长,善观其通,贵在兼收并蓄。
官修目录是目录的主流,余嘉锡考溯其沿革变化的同时,亦颇关注私家目录的出现与发展。根据《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踪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他认为此书目是任昉私人藏书书目,是见于史书最早的私家藏书目,应是后进私家藏书目之权舆。他对私家藏书目以及《坟籍志》的阐述,使得读者对古代目录学的发展的轨迹有了更完整、全面的认识。此前曾称叙录略如列传,而余先生又通过列传发现了目录的线索。《魏书·孙惠蔚传》载,孙惠蔚上疏请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校完秘书典籍,所提卢昶《甲乙新录》仅此一见。对孙疏,《北史》删削太多,《玉海》卷五二也只有数句,《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不置一词。余嘉锡在书中详录孙疏,既反映北朝目录学也在发展,也为少有记载的北朝文化增添些许内容。不难看出,由于余嘉锡谙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将目录学置于其中,考镜其源流,与学术发展融会贯通,我们从《目录学发微》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目录学。
说到类例,余嘉锡以为刘歆《七略》将群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晋荀勖变六略为甲乙丙丁四部,就是所谓类例,也就是分类。当时并无类例之名,此名始见于《隋书·许善心传》,而极言类例重要者,则是郑樵。余嘉锡当然主张类例心推本于学术之源,但他从历代著目录者皆在兰台、秘阁职掌图书,在著目录时必兼计储藏之法,不像郑樵、焦竑等仰屋著书,按目分来而已,所以批评郑、焦只强调以图书内容性质分类,忽略简篇卷帙多寡对分类的影响。如《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附在春秋类,就是因为当时史书尚少,不足以为一部。纵观中国目录的分类,从刘歆《七略》、汉魏时之四部、荀勖之四部、经史子集四部、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隋志》之四部,乃至《书目答问》在四部之外,另设一丛书部,分类在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余先生强调“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他主张顺应图书的发展而变化类例,而“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且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祖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心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他赞成张之洞关于藏书家书目和读书家书目的提法,前者待图书馆学者讨论之,后者以备学术之史。二者各治其书,然而《七略》、四部之成法,都不应成为目录分类的藩篱。余嘉锡发展的学术眼光,反映出他深得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真谛。
本书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与正文相得益彰的自注。自注所涉内容范围广泛,注明引文出处,解释引文内容,考辨引文是非,提出引文讹误,或是正文表述的延长,甚至还批评引文作者有掠人之美之嫌等等。如文中引郑樵《校雠略》之《泛释无义论》:“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下有注曰:“案此乃向、歆、王俭、阮孝绪之成法,安得谓《崇文总目》始出新意。樵最推重《隋志》,又尝引用《七录》,不知何以于二书所叙源流略不一考。”又如文中引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书册装潢考》,有注曰:“岛田氏此条,多本之汪继培之《周代书册制度考》,但稍详耳。而文中无一言及于汪氏,未免意存掠美。”又如引《史通·书志》篇“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论其妄载,事等上篇”,下有注曰:“上篇谓《天文志》。知几以为史不当有天文、艺文、五行等志,故云妄载。”以上数例抑或可以说明小注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正文,而且带给我们更丰富的知识和有益的启示,同时不影响正文的体例。余嘉锡对传统的自注有所继承和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从《目录学发微》中,既能学到系统、全面的目录学知识,而且可以体察到老一辈学者严谨、务实、开放的治学态度,这些都将令我们受益终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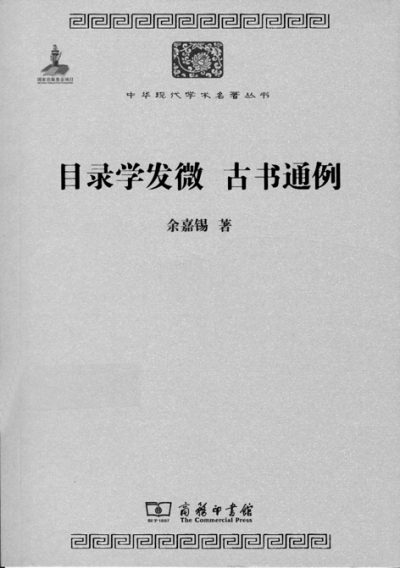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