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主要集中于书本身,尤其该书如何评价那段历史,如何评说那些众说纷纭的事件和人物,颇牵动各方的神经,也勾起一般读者的兴味。另外,这样一套大书,其编纂历时长久,牵涉众多,亦构成一部小型历史,很值得我们关注。
启动于一个特殊的年代
讲述《中华民国史》的编纂历史,需要追溯到1971年。正是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民国史研究列入国家出版规划。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研究员介绍说,1971年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是在特殊形势下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当时,全国的出版工作已停顿多年,几乎没有新书出版。时值“文革”进行的间歇期,召开此次会议,也有推动、恢复新书出版的目的。会议原定开两周,结果却开了4个半月,从3月到7月,从春天到夏天,最后形成的会议纪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毛主席批示,下发全国执行。正是在此次会议上,决定重印《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恢复“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出版《新华字典》修订本,等等。会后,国务院出版口即找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传达中央关于编纂民国史的指示。“但是,究竟是谁提出编纂民国史的建议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是如何指示的,只有等到今后相关档案开放,方可完全知晓。”汪朝光说。
“民国史编纂计划的提出,恐怕与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很大关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推测说。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松动。当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势必牵扯到台湾问题。1949以后,台湾仍以中国的合法政权自居。大陆提出为中华民国修史,意味着向世界严正表明:中华民国已成历史,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
汪朝光介绍说,编纂民国史的任务交给近代史所以后,1972年8月,近代史所向学部“军宣队”、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党组负责人刘西尧呈交报告,表示:“经过我们研究,认为在当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由近代史所负责这项任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报告呈交后,刘西尧批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吴庆彤批示:这件事是要做的,提呈郭老批示。郭沫若院长随即批复:同意。9月间,刘西尧将郭老批示转学部,民国史研究工作正式启动。
1971年,近代史研究所有工作人员近160人,其中研究人员100人左右。他们中的多数人在1970年5月下放到学部设在河南明港的“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7月才回到北京。1972年10月,民国史研究组成立,先后吸收40余人参加,他们都是刚刚从河南回到北京,正待开始研究工作,民国史项目的上马,刚好给了这些研究人员恢复研究工作的机会。
耿云志听说要搞民国史还是在河南明港干校。当时大家猜测,这个项目只能由近代史所接手。1972年6月,耿云志回到北京,消息也进一步明朗了。“民国史研究组最初成立时,总共只有十几个人。老一辈以李新、姜克夫为代表,都是解放区磨练出来的革命老干部。年轻人中,大多数人毕业之后从没搞过业务,不是都能立即开展研究工作,提笔写书或写文章。所以我说那时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到现在,这十几个人,有的故去,有的退休,有的外调,仍然在岗的,就剩我一人了。”耿云志回忆说。
中华书局很早就介入了《中华民国史》的出版。中华书局编审陈铮先生回忆说,文革期间,中华书局处于解散状态。1972年12月,中华书局多数员工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当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合并,两块牌子,一个班子,原中华书局文史哲编辑人员多被编为第二编辑室。1973年元旦后上班不久,原中华书局主持近代史编辑组工作的副组长李侃先生兴奋地告诉陈铮,他和近代史所谈妥一个项目,这就是出版民国史的项目。当年二三月份,李侃和陈铮首次参加了李新主持的民国史组会议。会上双方指定了工作联系人,作者与出版者的合作从此开始。
舍弃“以论代史”,坚持“论从史出”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作为民国史项目的主要领导者,李新先生承受了怎样的压力。耿云志介绍说,项目启动伊始,有些史学界高层人士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李新的工作。1975年,林修德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任领导小组组长,很担心这个项目出问题,便劝说李新不要搞了。李新回答说,我们编写中华民国史,并不是为统治集团树碑立传,而是要写中华民国的兴亡史,也就是要搞清楚它是怎么灭亡的。就这样,这个项目在文革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下来。
研究怎么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文革中流行的工作方式是“以论代史”(文革中搞大批判就是这种办法), 即先有结论,再根据结论去搜集材料。而李新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自一开始,他就坚持“论从史出”,强调先熟悉材料,积累史料,从材料出发,不说空话。“这样路子就走对了,我们的研究没有变成无谓的浪费。”耿云志说。
在重视史料的方针指导下,民国史研究组最初分为人物传记组、大事记组和专题资料组。汪朝光介绍说,当时的计划是编写一千人左右的民国著名人物简传,逐日编写民国大事记,编写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社会的专题资料,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民国史的撰写工作。“当时还没有电脑,一切工作都是循传统的方式,从查找、抄录资料,积累卡片开始,为此积累的卡片多达数十箱,体现出学者的刻苦和认真。”
1973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一辑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一辑同时印行,这是最早出版的资料汇编。最初出版的资料汇编采用白皮封面,大16开,被称为“大白本”。它们有材料,有分析,可谓有骨有肉,可读性很强。“大白本”只是内部发行,但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不少人托关系千方百计找来读。
197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一卷是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的,这也是1949年以后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带有“民国”字样的著作,充分说明了国家政治环境的变化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变化。
汪朝光介绍说,1978年以后出版的资料汇编,虽然仍有内部发行,但更多是公开发行。到1980年代末期,共计出版了“人物传”23辑,“大事记”31辑,还有特刊、增刊、专刊、专题资料等29种36册、译稿19种43册,其中不少至今仍为学界在研究民国史时所广泛利用,如《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奉系军阀密电》、《奉系军阀密信》、《史迪威事件》、《马歇尔使华》、《冈村宁次回忆录》等。这些资料都是从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报刊中爬梳所得,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辨整理,最终编辑成册出版,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1990年代以后,随着情况的变化,各种专题资料不再编辑出版,“民国人物传”和“大事记”全部改为公开出版。
台湾曾认为大陆是用修史来“灭亡”民国政权
有了丰富的材料积累,1977年便开始部署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内容是辛亥革命史。过去,国民党人曾经写过数个版本的“中华民国史”,主要着重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李新却认为这样太简单,应该把清末重要的事件都纳入到辛亥革命的范畴,其中包括立宪运动。
梳理立宪运动史的的任务交给了耿云志。在那之前,国内没有人认真研究过立宪派的活动,偶有一些论及立宪派的文章,也是视之为辛亥革命的反动力量,持全然否定的态度。为了搞清立宪派的活动,耿云志通读了作为立宪派重要舆论阵地的《时报》,从1904年创刊到1911年武昌起义,一天天读下来,费时数月。事实上,大约有两年时间,耿云志都泡在明清档案馆(今国家第一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处,查找当时与立宪派有关的各种报刊、档案材料。到1979年,耿云志开始撰写《中华民国史》有关立宪派的章节,这一章就写了8万字。耿云志在书中指出,当时革命党的力量非常有限,而立宪派有很强的实力,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有重要贡献。拿到耿云志的稿子,李新非常满意,认为材料详实,结论有说服力。后来书出版以后,耿云志关于立宪派的这一部分产生了很大反响,在海外也受到了普遍认可。著名近代史学者陈志让先生称赞耿云志的研究“材料、观点都是新的”,由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耿云志认为,除了关于立宪派的论述之外,《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对革命派的认识也有新意。以前国民党立场上撰写的相关著作,大多只写十次起义,其他一概略去。这样建构起来的革命历史,实际上只是孙中山一系的。“革命党有分派,比如光复会,虽然后人并没有以否定态度看待,但是也不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来写。我们的书则没有这种党派立场的局限。”耿云志说。
总的来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1981年上册,1982年下册)可谓一炮而红。“这是1949年以后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民国史研究著作,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该书‘翔实、公允、清新’。读者的反应也相当不错,该书的发行量很大。直到20多年以后,还有当年购买了此书的农村乡镇读者来函,询问那之后出版了几卷,在哪里可以购买,也可见此书当年的影响。”汪朝光说。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对台湾也是很大的震动。汪朝光告诉记者,在两岸对立的情况下,此书出版,也被台湾学界赋予了某种“政治”的含义,认为是大陆以此“灭亡”台湾政权。所以,台湾的“教育部”组织一些学者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发展史》,以此彰显台湾方面的历史立场。“这套书大体到1990年代出齐,分为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等卷,立论还算持平,比较适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参考。台湾方面的反应,当时也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回应。时任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的孙思白先生特别在1982年的《近代史研究》杂志撰文,说明我们从事的是学术研究,并无‘政治‘意图,并欢迎台湾学者与我们共同讨论历史,共话学术。”
事实上,情况也正是这样演化的。起初,海峡两岸双方在某些问题上(比如对蒋介石、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有不小的分歧,渐渐地,随着政治禁锢和意识形态的松动,双方观点逐渐趋同。
历经40年,“革命”终于成功
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1卷公开出版后,经历了27年的时间,在2005年出版了最后一卷第12卷。《大事记》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内部出版后,1996年一次性汇集出版为5大册。
《中华民国史》的出版“拖”得最长。李新先生原初的计划是争取在1975年编出大部分资料,并写出第一卷书,全部工作争取5年完成或基本完成。后来看来,还是对工作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实际上,《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册)的出版是在1981年、1982年,此时距离最初工作的开始已经接近10年。“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而言,有二三十年的开拓奠基时期,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汪朝光说。
《中华民国史》此后各卷的进度更加“缓慢”,各卷也不是按时间顺序出版:1987年,第2卷(1912-1916)、第3卷(1916-1920)出版;1994年,第6卷(1926-1928)出版;2000年,第11卷(1945-1947)、第12卷(1947-1949)出版;2002年,第8卷(1932-1937)出版。今年,过去尚未出版的第4卷(1920-1924)、第5卷(1924-1926)、第7卷(1926-1928)、第9卷(1937-1941)、第10卷(1941-1945)一次完成出版,又将过去出版的7卷略事修订后重印,同时将“人物传”和“大事记”修订重版。历40年之功,《中华民国史》终成完璧,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8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12册).
汪朝光先生介绍说,这次《中华民国史》一次推出,其中《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修改量最大,新增了100多位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未收录的知名人物传记,对于以往收录的人物传记做了不小的修改。《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也根据情况,做了适当的修改,主要是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删去一些不必要的内容,订正若干错误和文字表述。《中华民国史》除了有5卷是首度面世外,旧出各卷,因为考虑到工作量,也考虑到部分作者已逝或年事已高,还有排版的技术性要求,只订正了其中的史实讹误和极少的文字表述,而其基本的框架结构、史实叙述和评价、文字表述等并未大动,而是基本维持了当年出版时的原貌。“这样,虽然书中有些观点确实还值得讨论,留有时代的痕迹,但也可以从中知晓改革开放30余年来,民国史学科乃至中国学术发展变化的情况,而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的史实没有修改,正说明在历史的叙述方面,这套书是尊重事实的,是遵守学术规范的,也是立得住的。”汪朝光说。
关于具体的修改或订正,汪朝光举了两个例子。《中华民国史》第1卷第1页清朝雍正皇帝的名字,当年出版时写成“胤祯”,这是错误的,应为“胤禛”,这次重版便改正了。再如,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不影响排版格式的情况下,删去了这句话,因为“走狗”这样的表述比较“文学”化,同样的意思,完全可以用更学术的语言来表述。
一部民国史,做了近40年。实际上,这也是民国史学科从无到有,从“险学”到“显学”的40年,是民国史图书出版从“冷门”到热门的40年,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学术文化界从万马齐喑到风雷激荡的40年。《中华民国史》的编纂见证了这一切,也反映了这一切。而这其中,有前辈学者和出版人的努力,也有年轻一代的付出。40年间,参与编写工作的李新、李宗一、孙思白、姜克夫、彭明、夏良才、周天度、朱宗震等先生已先后逝世,中华书局参与出版工作的李侃、何双生等也已离去。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说,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革命尚未成功;诸多学者参与纂修的《中华民国史》历时近40年,如今已经大功告成。我们终于可以告慰李新、李侃等先生在天之灵了。”陈铮先生感慨地说道。
(本报记者 王洪波 郭倩)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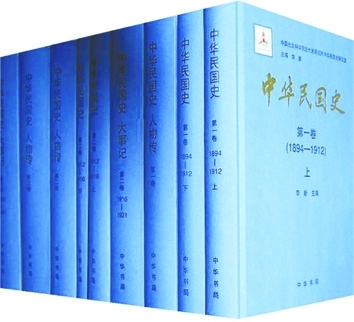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