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去世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但是关于他死因的真相一直众说纷纭。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已经病魔缠身的果戈理在精神上受到马特维神父的控制,神父“向他施加不良影响,说服果戈理放弃文学,献身上帝”。还有,《死魂灵》第二卷手稿的焚烧,究竟是誊清的定稿,还是“一些零散的片断”?一些同时代人的说法是,此乃果戈理神经错乱中的非理智之举。然而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在确凿的事实证据的基础上,提供了更多的背景,恢复了果戈理生命的最后几天的画面……
1852年3月3日(俄历日期,下文皆同),屠格涅夫在给阿克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对您毫不夸张地说,自我记事以来,任何事件都没有像果戈理之死给我留下这么强烈的印象……这样恐怖的死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不会立刻为人所理解;这是一个沉甸甸、阴森森的秘密——应当努力把它解开……但这不会带给解开这个秘密的人以任何欢乐……俄罗斯的悲惨命运要反映在位于距俄罗斯中心最近的那些俄罗斯人身上——任何人,即使是最坚强的心灵,也经受不住整个人民在他内心的斗争——于是,果戈理倒下了!说实话,我觉得他死了,是因为他下了决心,他想死……”
作家之死
在莫斯科,果戈理住在亚历山大·托尔斯泰伯爵位于尼基塔街心花园的住宅里。他占用了一层楼的正房,其中两间房子的窗户面向大街。伯爵住在楼上。诗人和翻译家尼古拉·贝格回忆道:“这里给他绝对的自由,并像照料小孩那样照料他。他什么事都不用操心。午饭、早饭、茶、晚饭,他吩咐摆哪儿就摆在哪儿。看不见的精灵把他的内衣洗好放进橱子里,就差替他穿上了。除了伯爵的一大群仆人外,还有一个他从小俄罗斯(指乌克兰,果戈理出生于乌克兰)带来的仆人在屋里服侍他。这个仆人叫谢苗,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性情温顺,对老爷忠心耿耿。厢房里异常安静。”
1852年初,果戈理还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此时还没有疾病的征兆。
1月26日,叶卡捷琳娜·霍米亚科娃久病之后死去了,终年35岁,留下了七个儿女。这是一位果戈理十分珍视、与他关系很密切的人。她是阿列克谢·霍米雅科夫的妻子,果戈理最亲密的友人之一、诗人尼古拉·亚济科夫的妹妹。她的死使果戈理内心十分沉痛。第二天上午,在举行过第一次追荐仪式之后,果戈理对霍米雅科夫说:“对于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就在那个时候,据果戈理的朋友和遗嘱的证人斯杰潘·舍维廖夫证实,果戈理在死者的棺材前面还说过另外的话:“再也没有比死更庄严的事情了。假如没有死亡,生命也就不会如此美好。”
我们未必能彻底搞清楚,为什么霍米亚科娃之死会对果戈理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但这无疑是精神上的震撼。
回忆录作者们指出,果戈理将霍米亚科娃之死视为针对自己的某种预兆。“他还打起精神安慰丧偶的丈夫,”塔拉先科夫写道,“但从此时起他就有了明显的离群索居的倾向;他开始长时间地祈祷,在自己的房间里念圣诗悼念霍米亚科娃。”“我妻子的死和我的哀伤强烈地震撼了他,”霍米雅科夫回忆道,“他说,她的死对于他来说,意味着许多他所深爱着的人重新又死了一遍……”
霍米亚科娃死后,果戈理经常祈祷。舍维廖夫说:“与此同时,正像我们后来知道的那样,夜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祈祷,不睡觉。”
在死前不久,果戈理在一张单页纸上用孩子似的大字体写过:“怎样做,才能在我心里有意识地、高尚地、永远地记住得到的教训呢?还有福音书上的所有的可怕事件……”传记作者们纷纷猜测,这张字条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谢肉节刚开始时人们发觉他身体有某些令人不安的迹象。2月4日,星期一,果戈理来到舍维廖夫家,说他“没有时间读校样”。舍维廖夫与他的妻子发现果戈理的脸色不好,问他怎么了。果戈理回答说,“感觉不舒服,所以决定吃一些日子的斋,祈祷。”(11日就开始大斋期了。)“为什么在谢肉节呢?”舍维廖夫问他。“就赶到这时候了……”
2月5日,果戈理对来看他的舍维廖夫抱怨“胃口不好,给他的药力量太大”。这天晚上,果戈理到火车站为来看望托尔斯泰伯爵的勒热夫神父马特维·康斯坦丁诺夫斯基送行。从这天起,他中断了一切文学活动。
在马特维神父即将离开莫斯科时,果戈理决定斋戒,即准备受圣礼。从2月5日开始,他几乎什么也不吃,夜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祈祷中度过。塔拉先科夫医生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谢肉节他献给了斋戒;多次去教堂,一再祈祷,格外虔诚;许多食品都严格戒绝,午饭仅喝几勺白菜汤,或是水煮燕麦。……如此剧烈地改变生活方式使他确实成了病人。不过,此时他的病仅表现为衰弱,没有任何其他明显的重要症状。”
塔拉先科夫说果戈理急剧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许多人也跟着他这样说),这未必正确。果戈理是东正教徒,一向遵从教堂的各种礼仪,这并不是他的第一次斋戒。
2月10日,是四旬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果戈理请托尔斯泰伯爵把自己的手稿交给莫斯科都主教菲拉列特,让菲拉列特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不能出版。伯爵没有接过手稿,担心这会肯定果戈理心里有关死的念头。从这天起,果戈理再未出过家门。
2月12日凌晨两点多钟,果戈理叫醒自己的仆人谢苗,让他悄悄地上二楼去,那里有火炉烟筒的挡板,要他点燃书房的炉子,烧文件。……第二天早晨,据塔拉先科夫医生记载,果戈理对伯爵说:“我干了些什么呀!本想烧一些早就准备好了的东西,却把所有的东西都烧了。魔鬼太厉害了,都是他害的我。我本打算送给朋友们每人一本做纪念:让他们随意处置。”
2月16日,星期六,塔拉先科夫医生来看望果戈理,劝说他听医生们的话。果戈理回答得有气无力,但清晰明白,很自信:“我知道,医生们很善良:他们总希望人们好。”然而却没有任何打算听从塔拉先科夫劝告的表示。“他的眼神就像是一个一切问题都有了答案的人,所有情感都已消失,一切话语都已失去意义。”
在这天,据托尔斯泰伯爵证实,果戈理领受了圣礼。
托尔斯泰伯爵想尽一切办法,竭力挽救病人的生命:请求果戈理一向敬重的莫斯科省长伊万·卡普尼斯特劝说他听从医生的安排;去求见莫斯科都主教菲拉列特,给他讲了果戈理病情的危重。都主教让他转告果戈理:“教会吩咐,在病中要服从医生的意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2月18日上午,星期一,约安·尼科利斯基神父建议果戈理接受涂圣油仪式、忏悔和领圣餐。果戈理愉快地答应了。他“手握蜡烛,流着眼泪,完全清醒地”听完了神父朗诵的福音。
据塔拉先科夫医生讲,从这天起果戈理再也没有从床上起来。把莫斯科最著名的医生都请来了,但他完全拒绝治疗。一如既往,果戈理坚信,他的生命掌握在上帝手中,而不是在医生手中。“如果上帝还想让我活下去,我就不会死……”他说。
2月19日,星期二,塔拉先科夫医生来看望果戈理。果戈理穿着睡袍、靴子,手拿念珠,面朝墙,闭着眼躺在沙发上。阿尔方斯基教授来了,他建议给病人实施催眠术,为的是麻痹他的意志,强迫他进食。奥威尔与索科洛戈尔斯基医生也来了。后者尝试着用手做一些催眠的诱导动作,然而,果戈理这时候正默默地向耶稣祈祷,催眠术未获成功。
托尔斯泰伯爵见果戈理病势危重,便召集医生们会诊,结果肯定了奥威尔教授的诊断:果戈理患了脑膜炎,决定对他实施强制治疗。医生们的做法是:把病人放在热浴盆里,往他身上浇冷水;把水蛭放在他的鼻子上,在他的身上涂抹芥末膏。他们像对待“疯子”和“失去自制的人”那样对待果戈理。
强制性治疗大概加速了果戈理的死亡。最后一夜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2月21日,星期四,早晨8点钟左右,果戈理去世。在意识清醒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死亡是何等地甜美呀!”
果戈理之死引发了许多议论。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死于绝食。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坚持这样认为,他依据的是塔拉先科夫医生的回忆录。当代研究者试图为这种推测提供理论基础。著名的神学家和教会史学家安东·卡尔塔绍夫在他不久前再版的《大公会议》中写道,果戈理“在忏悔中拒绝一切世俗的欲望,以绝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唯灵论的功勋”。文学家米哈伊尔·魏尔斯科普夫在自己的《果戈理事件》一书中说,作家之死“是典型的诺斯替教徒的伪装自杀,他以此种方式割断了尘缘”。
然而,正确领会与实行的斋戒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一个人死亡的原因。而果戈理是按照教会精神理解斋戒的,这从他摘录的神父的语录中可以得到雄辩的证明。他在自己的圣经(保存在普希金之家的手稿部)上所作的批注说明了这一点。“斋戒不是通往得救的门户”,他用铅笔在记载使徒圣保罗的话的页边上写道。
果戈理如何理解神主宰下的生命,他的内心生活怎样,周围的人们完全无从得知。没有自己的住宅,一直寄人篱下,他当然经常被迫掩饰自己的斋戒,正像福音书所训示的那样。看样子,只有在托尔斯泰伯爵家里果戈理才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其他的熟人家里,他们并不十分看重斋戒,果戈理便尽力不使主人感到为难……
失落的手稿
果戈理死后,当天就有传闻,说他把自己的手稿烧了。同时代人相信被烧掉的是《死魂灵》第二卷的手稿,指明烧稿的日期是11日的夜间至12日凌晨。第一个公开宣布第二部某些章节被焚烧的是波戈金。他在自己的悼念文章中写道:“第二天早晨他(果戈理)对伯爵(托尔斯泰)说:‘您看,魔鬼多厉害!我打算烧掉早已决定要烧掉的纸,却把《死魂灵》的几章烧掉了。这些手稿是我打算死后留给朋友们做纪念的。’”
然而,在果戈理的最后的日子里,波戈金并没有在果戈理身边,他引用的是托尔斯泰伯爵的话。在手稿发表之前,波戈金将其寄给了伯爵……托尔斯泰伯爵翻阅手稿后给波戈金写道:“我想,最后几行,关于魔鬼在烧稿中的参与及其发挥的作用,可以而且应该放弃。这是对我一个人说的,没有旁证:我可以不对任何人讲,死者本人大概也不希望对所有的人都说这件事。公众不是听取忏悔的神父,对这样一位人物,我们这些身边的人尚且难以理解,他们又怎能理解呢。”不过,伯爵又说,他有病,请波戈金“不管怎样,不要因为我的意见就罢手,这只是一个病人的意见”。
果戈理死前烧掉的是什么?这个问题难下结论。同时代人和后来的传记作者们众说纷纭。大多数人认为,被焚毁的是《死魂灵》第二部的誊清稿。也有另外一些别的推测:被烧掉的是《关于事奉礼仪的思考》。这是政治上有危险的手稿,果戈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写这部书。还有一种说法:果戈理什么也未曾烧掉,手稿被托尔斯泰伯爵藏起来了。所有这些假说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我们甚至还不知道,果戈理是否写完了第二卷。
塔拉先科夫医生这样讲第二卷的完成稿:“《事奉礼仪》和《死魂灵》由他(果戈理)亲手誊清,字体十分漂亮。”这个通告是有助于肯定果戈理烧掉了已完成的第二卷的唯一证据。譬如,科学院版的注释者引用的就是他的话。然而,塔拉先科夫同其他回忆录作者一样,首先依据的也是托尔斯泰伯爵的叙述:他不可能亲眼见到第二卷的手稿,因为邀请他去果戈理那儿是在2月13日,即刚刚烧完之后,而果戈理同意见他已经是16日了。况且塔拉先科夫也并未曾说他见过手稿。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果戈理严防不相干的人见到自己的书稿。
最后一个了解《死魂灵》第二卷部分章节的人是马特维·康斯坦丁诺夫斯基神父。这大概发生在他与果戈理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在烧毁手稿前不久。人们多次指责他,认为正是他怂恿作家这么干的。马特维神父否认果戈理是听了他的建议烧了第二卷,虽然他也说过,某些片断他不喜欢,甚至请果戈理将其毁掉。
1902年第五期的《特维尔教区报》曾刊登过马特维神父的谈话录,其中有这样的对话:“据说,您曾建议果戈理烧掉《死魂灵》的第二卷?”“不,不是……果戈理有烧掉自己不成功著作的习惯,然后再重写,将其完善。他的第二卷未必已经完成;至少是我没有见到过第二卷。事情是这样的:果戈理给我看过几本零散的本子,上面有题词:×章,他一般是一章一章地写。我记得,在一些本子上写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然后可能是第七章。有的上面没有标明。他请我读一读,然后说出自己的判断。我拒绝了,说我不是世俗作品的评判员,然而他坚持请我看,于是我就拿了,读了……还回这些本子的时候,我反对发表其中某些章节。在一个或两个本子中有对神父的描写。该人还活着,谁读了都会认出他来,还增添了一些特征……在我身上没有这类特征,而且还带有一些天主教的色彩,不完全是东正教的神父。我不同意发表这些本子,甚至请他将其毁掉。”
马特维神父的证词对我们来极其重要,因为他当时对于果戈理几乎是唯一的权威人士,甚至还更重要一些——是他的劳动成果的评判员。这种劳动给作者本人带来的与其说是文学上的意义,毋宁说是精神道德上的意义。很难设想,如果果戈理有誊清的定稿,还会拿一些零散的片断给他去评判。
可能舍维廖夫与马特维神父看到的是相同的章节,果戈理在2月11日夜间至12日凌晨烧掉的很可能就是这些章节。
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果戈理焚烧书稿时所体验到的真情实感了。波戈金在悼念文章中曾就此提出过质疑:“这个行为是一个基督徒自我牺牲的伟大功勋,是我们的自尊心所能奉献出的最困难的牺牲呢;还是其中蕴含着深藏不露的最精致的自我宠爱的果实,即最高级别的精神美的果实;或者,最后,在这其中起作用的是一种残忍的精神疾患呢?”
对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解答。果戈理的一些同时代人认为,他是在神经错乱中焚烧书稿的。比如,康·莫丘利斯基就持这种观点。“无疑,”他写道,“果戈理是在神经错乱的状态下焚烧书稿的;清醒过来后,他后悔了,哭了。”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果戈理焚烧书稿并不是突然的决定。波戈金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星期二夜间,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祈祷了好久。凌晨三点,他叫来自己的小厮,问他的另一个房间是否暖和。‘请递给我斗篷,走吧,我要去那儿处理些什么。’他手举着蜡烛向前走,每过一个房间都划十字。走到之后,吩咐轻轻打开烟筒,避免吵醒别人,然后让把柜子里的皮包递给他。皮包拿来之后,他从中取出来用绦带捆着的一叠本子,放到炉子里,用手中的蜡烛点燃。小厮猜到了他的意图,跪在他的面前说:‘老爷,你这是做什么呀!’‘不关你什么事,’他说,‘祈祷吧!’小厮哭了起来,求他不要烧。此时火熄灭了,仅仅烧黑了本子的一角。果戈理发现了,便从炉子里取出那捆本子,揭开绦带,把纸页摆得容易被火燃烧些,然后再一次点燃,这才坐在火炉前的椅子上,一直等到全部化作灰烬……”
这个最完整的记述依据的是仆人谢苗与托尔斯泰伯爵本人的见证。从中可以看出,果戈理焚烧书稿是在长时间祈祷之后,在他的行为中没有任何丧失理智的表现。对史料的认真研究只能得出结论:果戈理的行为完全是受理智支配的。
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果戈理烧手稿,是因为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不满意自己的作品。比如,像尼古拉·吉洪拉沃夫院士这样的权威专家就持这种观点。据他说,死前焚烧手稿“是艺术家的明智之举,他确信自己多年痛苦劳作的成果有缺陷”。然而,评价第二卷的美学的与艺术的成就十分困难,因为看到的只是草稿和片断,所以没有理由谈论创作方面的失败。不知道被烧掉的章节假如誊清之后会是什么样子。须知,我们评价的并不是第一卷的草稿的成就——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作者并没有把草稿呈交给读者。然而,我们还是要指出,听到过果戈理亲自朗诵第二卷的人当中,大部分人的评价都很高。例如,1849年8月29日,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告诉儿子伊万:“我再不能对你掩饰我们一直感到的愉悦:果戈理给我们读了《死魂灵》第二卷的第一章。好极啦!他的才能变得更严谨更深刻了……”
据在1849—1850年期间听到过果戈理朗诵第二卷前几章的同时代人反映,最后的定稿与我们看到的草稿不同。其差别主要在于对作品进行了仔细的润色。尽管如此,保存下来的那些章节无疑有很高的水平,是果戈理为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散文留下的独特的艺术遗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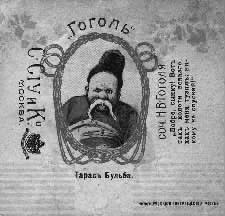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