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一生只留下了两部主要著作,即《道德情操论》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从人皆具有同情心入手,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而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人的利己心出发,构建了一套富国裕民的经济学体系。乍看上去,斯密的两部主要著作之间似乎存在着不一致之处。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斯密在两部著作中对于人性的假定自相矛盾。自此,《国富论》中的“经济人”与《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人”之间的“悖论”,成为学术界所热烈讨论的一个焦点。这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根本不存在。拉斐尔(Raphael)和麦克菲(Macfie)在为纪念斯密逝世20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序言中指出:“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是一个基于无知和误解的伪问题。”陈岱孙先生也提出,“斯密问题”其实只是个假象。
问题的关键是:利己是否意味着赤裸裸地追求经济利益?
《道德情操论》的正文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本书的起点是人具有同情心,部分研究者也许直接把同情心等同于利他,进而得出《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相矛盾的结论。然而在斯密那里,同情心与利他,是完全不同层次上的概念。如果追问同情心的起源,我们将发现,同情心不仅与利他没有什么关系,它甚至是利己心的产物。利己并不同于自私,它是一种“自爱”(self-love),是人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斯密把人自发的为他人的遭遇而悲喜的能力称为同情,但是他又指出,人对于他人的感受并没有直接的经验,因此只有通过想象,使自己置身于他人所处的境遇之下,进而去体会他人的悲喜。他写道,“人们看到此种情景而感到的痛苦并不就是那个患者感情的反映。旁观者的同情心必定完全产生于这样一种想象,即如果自己处于上述悲惨境地……自己会是什么感觉。”也就是说,正因为人具有利己心,具有关心自己利益的能力,它才能够在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之时,体验到与他人相似的感情。
因此,仅仅因为斯密提出人皆具有同情心,而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预设人性是利他的,是丝毫没有道理的。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在很多地方都阐述了人是利己的这一观点:“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会主要关心自己”、“对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来说,我们自己的毫厘之得失会显得比另一个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得多”。斯密指出,人为了追求财富而极度工作是出于实现和维持他的社会地位的需要。人们之所以拼命追求财富,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因为人们肉体所需的必需品很容易就可以满足。人们认为,财富“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也就是说,与《国富论》类似,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同样是把利己心当作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不能因此把斯密看作是一个信奉适者生存法则的理论家。利己心主要指的是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是一种自爱。斯密认为,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决不能跟自私相混淆。斯密深受托马斯·霍布斯的影响,霍布斯排斥了古典哲学对人的理性假设,认为人生而有的激情是推动人做事的原动力。而人的最大的激情,即是保存生命本身。斯密跟霍布斯一样,视人为动物界的一环,因此保存生命是人的第一要务。那么,每个人优先为自己考虑,就毫不奇怪了。
必须同时指出的是,斯密认为这一利己程度是有限的。为此他引入了“公正的旁观者”这一概念,认为人心中内在的良心可以起到约束人类行为的作用。“我们假定自己是自己行为的旁观者,并且用这种眼光来尽力想象这种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能用别人的眼光来检查自己行为合宜性的唯一的镜子。”这样,人既受到利己心的驱使(这是市场竞争的基础),又受到良心的约束(这是社会公正的基础)。
今天我们之所以还在不断重提“斯密问题”,是因为“斯密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性问题,它关系到斯密所提出的理想的经济制度的合法性。个人的利己心如何促成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斯密学说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扑朔迷离”之处。自凯恩斯以来,诸多经济学研究业已证明,市场几乎不可能自发调节到均衡状态,自由市场也存在着社会福利的损失。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重新去探究“看不见的手”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是去为自由放任的经济作任何辩护或者批判,而是要尝试着去理解,在斯密的理论中,一种基于人的利己心构建起来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如何可能的?
斯密语焉不详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看不见的手”。人们似乎一直在疑惑斯密为什么没有对“看不见的手”作出具体的论证。其实,斯密是对此进行了论证的,不过不是通过演绎的方法,而是通过具体的对经济史的考察。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篇中详细考察了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的欧洲社会经济史,这是一段纷乱无序的历史,封建社会各个阶级(尤其是当权者)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大地主沉迷于享乐,不愿意节约资本去改良土地,政府为了维持特权,对农业贸易大加限制,这一切导致了农村发展的迟缓。而在城市,国王为了对抗领主,不得不与市民联合起来,进而催生了后来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自治城市。由于农村状况不断恶化,因此大量农奴逃到城市,这样城市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城市的繁荣反过来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乍看上去,每一个部分都是无序的,但是冥冥之中,它却促成了一个理想的谐和的结果,仿佛真的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这一切。
那么,使社会团结起来,并达到社会和谐的这样一种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斯密的社会理论中,人们之间必要的帮助产生于利己的动机。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缺乏爱和感情,但斯密却认为这样一个社会并不会解体。“社会可以在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爱火感情的情况下,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并且,虽然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或许这就是《国富论》中屠户和面包师的故事的寓意吧,正是利己心把人们连结到一起。斯密把基于利他的恩惠排除在社会原理外面,无疑是很有见地的。恩惠实际上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根本,因为它和人的需要,因而又与人的自我保存这一最根本的激情,起着严重的冲突。
但是他同时明确地为这利己心圈定了一个范围,因为:“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老是相互损伤和伤害的人中间。每当那种伤害开始的时候,每当相互之间产生愤恨和敌意的时候,一切社会纽带就被扯断。”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的自利行为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斯密在《国富论》的许多地方都批判了人的过度利己行为,事实上他把这种现象视作是人由于不能正确分辨什么是自己真正的利益而导致的谬误。如果是真正关心自己并了解自身利益的人,是不会做出那种错误的行为的。
同时,斯密认为人的各种激情之间能够起到相互牵制的作用,从而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他说,“愤恨之情……是正义和清白的保证。它促使我们击退加害于己的伤害,回敬已经受到的伤害,使犯罪者对自己的不义行为感到悔恨,使其他的人由于害怕同样的惩罚而对犯有同样的罪行感到惊恐。”倘若每个人都调动起自己的利己之心,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当别人的利己行为危害到自己的利益之时,该行为就能够得以被遏制,这样,也就保证了各个“经济人”的利己行为能够被自动约束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这样,在斯密的理论中,一个基于有限的利己心的社会就被自发地建构了起来,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力量有助于维持这经济秩序呢?
斯密秉持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主张国家不应该干预经济生活,但他并没有轻视国家对于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作用。斯密认为,国家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每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斯密虽然没有明言,但他似乎是看到了一个建立在人的利己心基础之上的社会的缺陷,因此他给了政府以弥补这个缺陷的职责。利己心的弊端就在于人们容易为了个人利益而侵犯他人利益,且对看似事不关己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因此在斯密的理论里,政府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恰恰维护了斯密理想中的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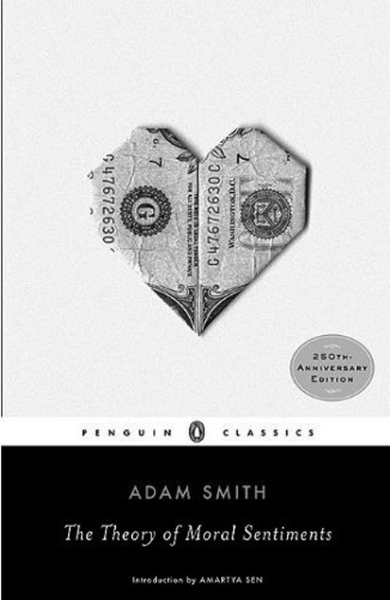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