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说的就是人的灰烬。
灰烬的意思是繁华后的简单。人总是不信灰烬其实是繁华后的一个庄重形式,一种“自然之至”。灰烬,说出来了就是诗。我了解灰烬,因为它是灰烬阿。
灰烬很容易随风去了。灰烬也可能埋下种子。
生之乐趣,就是种子。创作里的生之乐趣说的是“一个人”和“一个人”纯真的情感。创作中成为纯真的“一个人”,是一门艺术,一种气质,一首诗。朴素纯真的成长很贵。过于昂贵,所以人可以放弃。(事实上,大多数纯真的灵魂——也只有纯真的灵魂表现崇高的东西——不能给人带来好奇,哪种纯真不是被浪费的?)但放弃是什么呢?我还不愿意知道。
我是个寻“回忆”、“记忆”的创作者。我几乎不曾依赖现实的个人经历。事实上,真正新颖、典型的东西总是来自过往的岁月。(“回忆”作为过时的东西自然而然成为最高感性思辨的对象。)
但“岁月”像稻草一样,总是漂浮在表面上,想寻找珍珠的人必须潜入水底。
水底很黑。好在创作的本质是,如果没有黑夜就接受不了什么……除了更深更黑以外,没有别的更爱的办法。
创作就是在很黑的暗夜里摸索、行走,寻找独一无二的新视角,寻找独一无二的胆识,寻找独一无二的人心。寻找,就是不肯重复,也不肯相信别的东西。(任何创作说的就是一个个个体,还有一个个缺憾的能力,艺术主要就是表现这些……)因为没有人可以解释我们的内心。就连常识也经常变化。
我总是等待最朴素、最天性、最直接的方法。我等待每种天然到来的事故——等待无知,等待冒犯(无知、冒犯都是创作里的大资本),等待最本质、最单纯的动因——不损坏,你就永远没法(也没有)思考——总是偶然、黑暗、事故、原始的混乱,让我更接近天然。(是天然,不是编造,也只能是天然让人由偶然的不完美回复到完美的本性。)要比自然更赤裸、更偶然、更真实、更天然才能体现自然的游戏。我幻想这种复杂性。
我越是渴望表达,越是显得不够——创作最深邃的时刻表达了这种挫败。因为我还不能达到自然那种深度,因为我还不能到达平淡天然那里。(我不是达不到它,而是鲁莽地越过了它。)
……结果总是残骸,总是灰烬。
创作如此天真、如此灰烬正值一个虚幻,别无其他。知道是一种虚构体又甘心情愿地信仰它。这是何等微妙的真理。
所以真纯之物完全可以不作。不作可能更深刻。——创作什么时候真的被大多数人阅读过?
如何寻找一个不画不述的理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能是合理的吗?我也不知道。
这样的沉默,听起来不错。(像是)胜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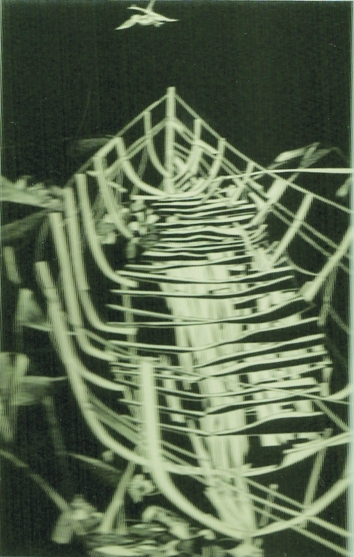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