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您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文字学的研究要取得新的成就和突破,必须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三个结合,也就是传统学术的发扬与现代学术的创新相结合,地下出土古文字材料与传世文献文字材料的运用相结合,个体汉字的考证释读与汉字体系的理论探索相结合。对文字学研究而言,这“三个结合”意味着什么?
黄德宽:所谓“传统学术的发扬与现代学术的创新相结合”,主要是学术传承和发展问题。文字学是中国地道的土生土长的学问,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作为“国学”的根基,传统语言文字学隶属于经学,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方式和传统,历代学者对汉字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文字学不能无视其深厚悠久的传统。西方现代学术尤其是现代语言学传入后,使中国学者开拓了学术视野,深受西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和理论的影响,一个时期内一些学者比较重视西方学术而对文字学自身的学术传统不以为意。我们认为,当代学者研究中国文字如果仅仅停留在继承传统学术的层面,那是不可能取得大的成绩的;如果过于迷信西方学术,那就会脱离汉语言文字的实际,也难以真正获得学术上的创新。只有既重视学术传统,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也从西方现代学术中吸取营养,将二者结合好才能带来古老的文字学的不断创新。
所谓“地下出土古文字材料与传世文献文字材料的运用相结合”,主要是关于文字学研究材料的应用问题。以前研究汉字,最重要的材料是《说文解字》保存的小篆和少量古文、籀文,对汉代之后的隶书和楷书材料都不是很重视。而《说文解字》所使用的篆文主要是秦系文字,是汉字经历漫长发展历史后整理规范的形体,是古文字的终结形态,虽然籀文和古文来源于春秋战国,但是多是辗转抄写,讹误甚多。依据这些材料,研究来源古老的汉字体系,局限性不言而喻。随着晚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殷商甲骨文重见天日和近代以来科学考古学传入中国,一百多年来,先秦乃至秦汉魏晋各个时期的原始文字资料大量发现,展示了汉字不同历史时期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使今人有幸重新看到殷商以来历代汉字的真实面貌和使用情况。将传世的历代文字资料与地下新发现的文字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就可以澄清汉字研究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揭示汉字构造和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更准确科学地认识汉字。
至于强调“个体汉字的考证释读与汉字体系的理论探索相结合”,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字学和当前汉字研究倾向的纠偏。传统文字学主要是为解读儒家经典服务的,“以字解经”、“以经解字”,形成了以单个汉字的分析解读为中心的研究传统,这方面的成果积累也尤为丰厚。只是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的文字学和古文字学研究。长期以来,汉字研究的传统是关注个体考据,忽视理论总结和规律揭示,其结果是汉字的理论研究至今依然显得很薄弱,这又制约了这门古老而重要的学科的发展,直接影响文字学研究科学水平的提高,使得文字学对世界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贡献没能充分体现出来。
所谓“三个结合”不仅是我们在研究文字学中逐步明晰的一些认识,而且也是近百年来文字学研究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读书报:在文字学研究领域,您带领的团队近年来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已出版《汉语文字学史》、《古文字谱系疏证》、《新岀楚简文字考》和《汉字理论丛稿》等著作,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重要奖励。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哪些方向?
黄德宽:从研究中形成一些理论认识,再到实践中有意识地坚持,这是一个过程。虽然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体现了我们对“三个结合”的认识和追求,但是还是很初步的。您提到的这些著作,大体上反映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情况。这些年来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学学术史、古文字考释和出土文献研究、汉字的构形和发展理论研究等方面。此外,在总结传统学术研究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汉字的阐释与中国文化传统独特而深层的联系,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历代许多汉字研究的现象,并且对当代的汉字阐释具有启迪作用,也蕴含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还开展了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这本论文集所收录的有关论文,基本反映了我在相关领域的部分研究工作。
读书报:那么,您如何看待文字学研究未来的走向?
黄德宽:中国文字学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而且已经具有很好的基础条件,我始终认为21世纪文字学的研究大有可为。例如,我国至今尚没有一部《汉字发展通史》,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开展好前期一系列的相关课题研究。这些年来,我们为此也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但工程浩大、难度很大。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能完成这项研究任务。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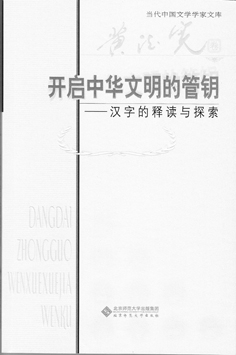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