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好年华,捐躯雪域高山。家国万里,仅仅以一枚铭牌存志。葡萄牙青年与山鹰社的学子,何其相似?但漠漠雪原中的一枚铭牌,相较于山鹰社山难后的激烈争论,曲折而沉重的立碑过程,葡萄牙青年的生与死,又显得比中国人多了一份从容。
这份从容来自何处呢?
来自一个民族对生命的理解,又来自这个民族文化看待死亡的方式。
人之所以为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是有死的。因为有死,生命才成其为生命。又因为有死,生命成为一趟没有返程的列车,制约着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接受还是抗拒。对死亡的恐惧是每个人的本能,但中外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人忌讳死亡,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因为没有上帝,没有天国,没有来生,死亡是一次彻底的终结。
基督教文化下的欧洲人,相信耶稣的复活,期待基督的拯救,相信神的国度会降临,所以人们生时乐于行善;当面对死亡时,又多了一份从容,怀着感恩的心态,感激曾有过宝贵的生命,感激人生一世度过了很多好时光。
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人,死亡之后能留下的只有“身后名”,可能流芳千古,也可能留万世骂名。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盖棺定论。
而基督教文化下的欧洲人,死亡是“安息主怀”,能够评价过去人这一生好坏对错的,只有上帝。
同样,两种文化对生命的理解也非常不同。中国人只有此岸,西方人敬畏彼岸。因为只有此岸,价值观局限于世俗,人的生命有高下贵贱好坏对错,生不平等,死后也没有机会平等。因为敬畏彼岸,价值观可以超越世俗,人生的时候可以不平等,死后通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总有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时候。
或许因此,中国社会多有秩序共处的观念,而西方社会多宽恕、博爱的观念。
1989~1990年,汪建在艾奥瓦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与几位中国留学生住在一起。同在异乡为异客,大家关系处得不错,但也有一位同学比较孤僻,这是正在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的中国同学卢刚,来自北大。
天体物理课程比较枯燥,而且冷门,毕业后不容易找到工作。卢刚毕业一年多,找不到工作,校方留下他当助教,但他没能获得作博士后研究的机会,而博士后的收入远远高于助教。
后来,又来了一位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的中国同学,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出来的山林华。山林华学业出色,人缘很好,担任了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风头一时无两。他不到25岁就博士毕业,并获得艾奥瓦大学年底唯一“最佳博士论文奖”,还收到美国多所学校的聘书。
1991年11月1日,山林华的最佳论文专题讨论会上,卢刚携枪射杀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山林华,然后饮弹自尽。事件震动中美两国。
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科学家,为何会做出极端的暴行?卢刚自述,他的指导教授故意阻挠他毕业、求职、发表论文,甚至当众羞辱他;另两位教授也因偏袒其他研究生而对他多加指责;校方对他的投诉置之不理,甚至合谋孤立他——而这一切,又与他的同胞山林华有密切关系。
事前,卢刚留下一封公开信:“身为物理学家,我相信物质、精神、运动等永恒性。纵使我血肉之身体逝去,我的精神仍是永恒,我将以量子跳跃式进入世界的另一角。我已经达到自己在这里的目的——化非为是。我为自己在此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对马上来到的远程更是充满信心。再见吧,我的朋友!或许我们能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重逢。”
惨案发生后,华人媒体有大量评论,其中许多指责卢刚冷漠、傲慢、自我中心,也有一些舆论为他辩护。而仅仅三天后,罹难的艾奥瓦大学副校长安·柯莱瑞博士的两位兄弟致信卢刚家人,信中说道,“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了要分担你们的哀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时刻,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
超越生死的宽容与爱,读来感人,几乎有撼动顽石、融化坚冰的力量啊!
基督教社会的这种宽恕与博爱,是少见于东方社会的。虽然孔夫子提倡恕道,但他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告统治者“容众”、“宽和”。而当子路问他是否应该以德报怨的时候,孔子回答:以德报怨,那你何以报德?不如以直报直,以德报德。显然,与柯莱瑞兄弟信中的精神不是一回事。
不过,毕竟宗教和文化都是极其复杂的社会机制,如果因此得出基督教教义就是宽恕与博爱,或者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教人向善的结论,甚至于说一个人有信仰,就意味着道德纯洁、意志坚强、严谨自律、待人友善、精神乐观、家庭美满等等预设,则会失之简单,落入公式化思维的陷阱。
即便是以实用主义自诩的宗教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认为宗教与德行无关,宗教说到底是神秘主义,相信某种超越于尘世经验的存在,并相信人的终极福祉在于与这个超越的存在达成和谐。超信仰可以帮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和美好,但它是无法被实践证实的。
人不可能简单地求助于信仰或知识,就能获得解决方案,更多时候,只能独自承受人生的困惑,在人性的波涛中挣扎浮沉,最后还是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为何?
2002年2月27日,汪建的好友、华人科学家黄谷扬枪杀俄裔女科学家坦雅·霍兹玛雅,随后又自杀。消息很快传遍美国和华人世界。
在中国人看来,黄谷扬走了一条典型的“天之骄子”路线:1981年,以上海市第11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遗传系,又在上海交大读完硕士,随后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进入华盛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主任胡德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担任过课题组负责人。
黄谷扬的夫人是他在复旦的同班同学,一家生活“十分美满”。他平时热爱文学、历史,喜欢读黄仁宇的作品,用心研究美国宪法,“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他热情,坦率,在留学生圈子里有很高知名度。
人们疑惑:黄谷扬杀人又自杀的动机何在?
最多说法认为这与8个月之前,黄谷扬从PPD公司分子生物研究部主任位置上被开除有关。决定开除他的人是霍兹玛雅,理由是他一直保留着1998年以来在中国华大基因中心的副主任兼职。而且,作为文化边缘人和高科技前沿的研究者,黄谷扬生活于巨大工作压力下,一年前曾经得过抑郁症,看过心理医生,并大量服药。
就在悲剧发生之前几个月,汪建的夫人接到黄夫人电话:妻子提出要离婚,黄谷扬心理这一关过不去,竟然就买了一把枪!
几个好友一合计,把枪的扳机拆下来扔了,再买再扔,最后他又买了一支藏起来。
2002年春节,汪建追到美国黄谷扬家里,和他聊天,劝解。
可就在汪建刚从美国回来后的第四天,黄谷扬拿上枪跟着送比萨饼的人,把霍兹玛雅杀死于家门口。又到海滩的跑步道上,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天前的一个下午,他和汪建就站在那个地方长聊了六个小时:怎么克服抑郁症,怎么克服眼前的困难,走出心灵的困境……
自杀前,黄谷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你们可以骂我,但这是我的选择,我心里非常平静,祝愿华大走好……
后来汪建到上海参加追思会,黄谷扬父亲说了三句话,时间过去六年,汪建至今还记得:
“我想不明白三件事。第一,我是一个抗美援朝老战士,不明白我儿子、女儿、儿媳妇、孙女怎么全变成美国人了。第二,上海市生物竞赛,黄谷扬是第一名。高考,黄谷扬是全上海第十一名,他在微观世界的研究是那么得心应手,怎么在生活中就搞得一团糟?第三,杀谁,你也别杀那个无辜的俄罗斯女人啊!”
纯朴的语言,生命的悲歌,闻之令人泪下。
人世有善恶,生命有悲欢,无论人类文明如何演变、物质技术怎样发展,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可以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人为造成的恶,但以人类在自然宇宙间的渺小,以我们每个人自身生命的偶然和渺小,我们终须用自己有限的肉体生命承受苦痛,学会宽恕,学会感恩。
(本文摘自《灵魂的台阶》,王石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49.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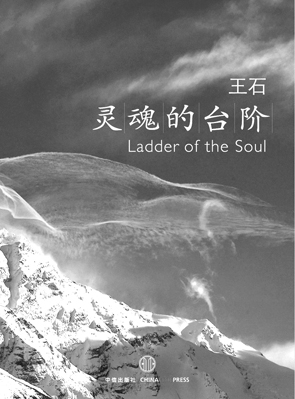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