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的出版,让更多的中国人记住了曹锦清的名字。这本文体如流水账、文字朴实无华的书当年即卖了3万多册,并成为当年全国人代会关注“三农”问题的触媒之一。在新书《如何研究中国》里,曹锦清除了延续一贯的三农话题,也以相当的篇幅深入论述了中华文化传统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并试图将三者纳入民族这个统一体中来理解。
当前,中国的财富增长上去了,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理论问题。“现在在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的那一套学说,我们的各种社会科学对认识当代中国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在何处,将要往哪里去?”这种对于民族气运盛衰的执著关切,于曹锦清,既是立场,也是观点和方法。一切从中国出发,从当下出发,以民生福祉为终极关怀,认识与理解中国,在《如何研究中国》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位学者对当下国情的新的观察与思索,以及充溢于其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情怀。
读书报:当年《黄河边的中国》一出版即产生很大影响,这本《如何研究中国》您自己是如何定位的呢?可以看作是您这几年间思考的成果汇总吗?
曹锦清:这本书里面包括了我这近几年思考的一部分内容,但大部分还没有写出来。说起来很巧,我60岁的时候,弟子们提出要将我的文章、讲稿收集起来出版以作纪念,当时我没有同意。不同意的原因是大部分已经发表过了,而且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但学生们坚持,出版社也愿意出,所以就这么出了。书名也是他们定的,我也不是很满意,口气有些大了。所以对这本书的出版,我是战战兢兢,好在出版以后反响还比较好。
我每天有记日记的习惯,大部分想法都记在日记里了,想写成文章,但始终动不了笔。原来定的题目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与实践”,这门课我在复旦大学开办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培训班上讲了5年,但因为所思考的问题牵涉面越来越广,有点力不从心了。要重新梳理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乃至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思想脉络,势必存在与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也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论的框架如何协调的问题。现在通行的叙事都是从传统到现代化这个框架延伸出来的,很多问题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如果按照现在的立场、经验和兴趣来重新梳理过去,确定现在,预测民族的未来,这样一个工程我觉得自己是无力驾驭的。
读书报:那多长时间内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思想成果的出版呢?
曹锦清:我说的力不从心固然有我个人的原因,如学力不够,但更大的原因是中国的整个发展还没有达到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我们对中国的崛起有足够的自信。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点自信,但这还不足以让学界站在一个全新的立场来衡量东西方,重新回顾我们的历史,这个“时点”还没有到,所以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时间。
读书报:对于中国的崛起,目前国内学术界和西方的评价有很大差异,这是否与您所说的“时点”存在某种关系?
曹锦清:可以这样说吧。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发展(如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给西方以深刻的印象,这样在估价中国的时候,他们往往进行夸大,以此来警告西方,中国已经上来了,一定要做好准备。当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要学会如何和崛起的中国相处,要理解中国,不要重蹈历史覆辙,这是比较温和理性的判断。而中国对自身的崛起还心怀忧虑。如果不能继续稳定的高增长,大规模的就业,环境、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因为期待我们的民族能够平稳地复兴,学术界对于面临的一些问题就会放大性地加以观察,忧虑之心也油然而起。因此,对于中国的崛起,国内学术界和西方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异。但如果中国再持续稳定发展二三十年,那时全部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有可能失去解释功能,这样的一种经验使得中国的学者有信心重建一种理论来解释自身。
城乡关系的新阶段
已经来临
读书报:针对工业化发展战略中农民受到“剥夺”的问题,您主张将农民组织起来。当前这种可行性有多大?又该如何实施呢?
曹锦清:我认为2006年以后这个可能性的空间已经存在了,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工业化积累不再依赖农业和农民,农业税费已经全部取消。建国以来,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只能依赖农业和农民,农业和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了重大牺牲。2004年中央提出,后发国家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引领乡村。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样,农民组织起来的政治上的障碍被扫除了。让农民组织起来,改善农业这一弱势产业的经营状况,维护农民自身的权利,我觉得时候已经到了。
实施方面,可将村民自治组织、各种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等联合起来,在所在县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农民协会组织,这样农民的要求可直接通过农协反映到县政府的各种决策里面,这对城乡一体化建设尤其有好处。类似的协会,二战以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比较有效地发挥了作用。
读书报:当前,城市化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这也与三农问题紧密相关,与西方国家相比,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曹锦清:优势是中国的土地制度:一是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一是城市的土地国有制。这就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劣势是农村的人口庞大,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过如此庞大的人口集群,中国要在短期内让农民有序进城,压力可以说是空前的。农民进城要有住房和稳定的就业,还有相关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目前的问题是农民所拥有的宅基地、农地和林地能不能够置换城市的五项保障。
城乡结合的地方地价很高,转化为城市相对容易些。可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农民原来拥有的房子通过出租可以获得租金,他们对户籍城市化反倒无所谓了。问题在于那些远郊的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来上海、北京的这些人怎么城市化?如何避免出现发达国家早期大量存在的贫民窟的问题,这个任务极其艰巨。好在中国的地权制度不是私有化,解决城市化问题有相对方便的地方,比如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商品房各占三分之一的形式,来逐步有序地推进城市化。目前重庆就是这样做的。
读书报:当前,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大部分都回去了,继之而来的是80、90后的新一代农民,与所有新生代一样,他们也会对社会有自己的要求和期望,这是否会成为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又一大压力?
曹锦清:是的。目前大面积的进城做不到,虽然现在有些城市对已经获得城市居住权、稳定就业和较高收入的农民逐步地开放户籍(县和乡镇这两级的开放度比较高一些)。可在大城市,像上海,五六百万的外来人口到底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将来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为这一代农民工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农业的经验,他们城市化的倾向比父辈要强得多,将来回到农村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现在,90后还比较年轻,再过一段时间他们不能忍受目前的处境,那个时候要完成城市化,住房怎么办?如果有些城市对他们的住房解决得比较好,大量的人涌到这里来怎么办?如果全国的各大城市同时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呢?这些都是问题。
研究方法的两个维度
读书报:您在研究中一直强调历史的维度,强调历史的延续性,这是否与您早年的历史专业训练有关?
曹锦清:是的。目前的社会科学都有这个弱点,第一,理论来源于西方;第二,直接记录当下观察到的事实,忽视其历史沿革。物理学上的时间与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时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社会时间是流变的,不把当下观察到的事实放在一个流变的社会时间里去观察,难以完整地理解事实本身。例如,解放以后县一级官员的回避制和短任期制,一般三年一任。任期为什么那么短?这个短任制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查阅了很多县志,知道是宋以后形成的。这种制度长时段保留着,历史在流淌着、在当下存在着,只有将历史的脉络梳理清楚了,研究其原因,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问题。
读书报:您在调查中强调社会心理,认为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权得到表达。当年《黄河边的中国》打动那么多的读者,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您在调查中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呢?
曹锦清:把调查对象当作老师、当作朋友,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了解他们熟悉的经验,几个来回下来,他们对你就会产生信任感。社会调查有一些是用眼睛可以观察到的:比如住房、家里面的陈设、土地、生产成本、产量、收益等等,但作为一个阶层、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农民有思维有激情,对生活、家庭、孩子,包括对社会生活的变动、各种涉农政策以及地方官员的行为等等都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重要,但这些感受通过问卷很难被问出来,必须深入到农民的家庭和村落中间,和他们在一起才可以慢慢体会到感悟到,然后把这些东西真实地表达出来。社会心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这是那些抽象的数字无法触及的。
读书报: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研究三农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您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是怎样的?
曹锦清: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他用最高级对他那个时代做出了两个极端的描述。看我们今天的生活,确实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看到经济的增长,一个一个的阶层富裕起来,看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看到百年的屈辱终于在这30年中稍稍有点抹平;但从负面看也有比较糟糕的地方,腐败、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等。所以对这个时代的感受,只能用两个相反的判断构成一个整体,左右两派各持一端,都属偏见。然而,将两组相反的判断有重点地加以有机地综合却也十分困难,另外,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了对当下做出精准判断的难度。对未来的预期,时而悲观,时而乐观,随新出现的重大事件而起伏不定。对未来的期待随重大事件而变动,于是对“现在”,并通过“现在”对“过去”的梳理也变得摇摆不定,这大概就是我近几年来的最大感受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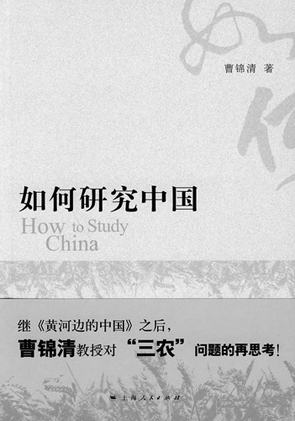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