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纪晓岚的故事说起
每当置身于书店或图书馆,流连森森书架间,往往感觉世上一切的学问,已经被人做完了。但当你认真阅读那些林林总总、千奇百怪的著作时,却发现多数了无新意,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花大力气去寻觅与挖掘资料,所以就只能是千人一面,重复编抄。笔者试以所见,随手举一个例子吧。
清代乾嘉时期大名鼎鼎的名士纪昀(1724-1805),大概没想到在他身后200年的今日竟然如此热络,不仅有专门演义纪氏故事的电影与电视剧,而且研究著述也不下百种。我曾经向一些研究纪昀的专家请教,为什么乾隆帝在众多文臣中偏偏遴选纪昀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呢?专家的说法不一,但却无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但《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八年十月,时为福建学政的纪昀奏称:“坊本经书尚全刻庙讳御名本字,应仿唐石经、宋监本例,凡遇庙讳俱刊去末一笔,并加有偏旁字者俱缺一笔;又武英殿官韵及各经书於御名本字尚系全刻,及加有偏旁字者,俱未缺笔。请将本字及加有偏旁字者并行缺笔,载入《科场条例》。如误书者,依不韵禁例处分。武英殿书板校正改刊,并行文各省一体遵奉,将坊刻各经籍改刊。”乾隆帝准奏,开始了一场改字运动。但此事是否实行?究竟实行到什么程度呢?
其后,我在北大图书馆翻检纪昀好友钱大昕手稿本《讲筵日记》发现,钱氏也提到此事,并记载当时自己分到《周易折中》、《元史》、《清一统志》诸书进行校改,可见纪氏所奏的确在当时得到了执行,只不过后来由于改不胜改而中辍。(乾隆三十年闰二月,清高宗因改不胜改,下诏停止了此次改字活动。参《清高宗实录》卷696,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丁酉(十四日)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1987年版,第17册第804页;又卷731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乙丑(二十日)条,第18而第47页。)
所以,清廷在开《四库全书》馆后,乾隆帝从众多臣子中选中纪昀主持全书之编纂,其在福建时的奏疏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通过这次事件,纪昀一定在乾隆帝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相信纪昀能忠实执行他的修书意图。
各种关于纪晓岚的书籍,记载他是嗜烟好色,所谓“纪大烟袋”,还有书籍描述纪氏是酒量深洪、畅饮无度,而不知纪氏实不能饮,浅尝辄醉。再如世人皆知纪氏卒后,嘉庆帝亲赐祭文,享尽哀荣,殊不知纪氏以高龄老人,晚年奔波于热河等处,自费删改校勘《四库全书》,屡屡被罚俸,以至卒后仍欠赔付之费。还有些剧中演纪氏泼墨挥毫,书法遒劲,竟不知纪氏不擅书法,屡以为恨,常常请人代笔呢。
但在众多研究纪昀的专著与《年谱》中,却都没有上述史料出现,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人愿意耗时去翻阅《清实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这些珍贵的档案材料,更不愿去查证纪氏同时友好如钱大昕《讲筵日记》这样的手稿孤本,甚至纪氏留下不多的著述,也极少有人认真去研读。
但也有以,以大海捞针的决心韧劲来研究学问的,我的学兄吴铭能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近日读到他的《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感触良深,本书是一本论文集,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作者挖掘档案、手札与口述历史等史料后所得之成果,现就读后感受述之如下。
二、书信中透露的历史事实与解读书信之法
吴教授的《历史的另一角落》中,论述的人物如梁启超、徐志摩、陈独秀、雷震等,都是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在国人心目中,但凡伟大的人物,就是正义与英雄的化身,不得有一星半点的缺点与不足。梁启超是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人们对其学行的研究,当然就是以颂歌为主了。但吴教授通过对梁氏大量书信的研究发现,在梁氏一生中,有许多为人忽略的“小事”。
例如,吴教授指出,梁启超一方面写《阴阳五行说的来历》抨击迷信,另一方面又希望将香山卧佛寺旁的坟地与人互换,以求风水宝地,且择“黄道吉日”以安葬其夫人。(《历史的另一角落》,第10页)
吴教授又发现梁氏每到一地,总要约上友朋打麻将,且兴致极高,乐此不疲。“除了临摹碑帖、写文章、抽烟、喝酒之外,打牌是他休闲生活中极重要的部分。许多人说他晚年已把消耗光阴的打牌习惯戒除掉,由大量书信观之,是不符合事实的;何况在牌桌上,与好友纵谈时局大事与发抒写作心得,对梁氏未必是消耗光阴,反倒是有益于健康与文思。”(同上,第15~16页)
这些事实,与人们心目中以及研究者笔下的梁启超大大不同,而正是这些看来貌似细微琐事的研究,却极大地丰满了梁氏有血有肉的形象。吴教授认为:“过去史学家对于历史名人的研究,往往取其大以评论其得失短长,至于其细微琐事,以为‘无关宏旨’,也就无暇措意或兴趣缺乏,此本无可厚非,难以求全。但是如有相当充分条件,应该尽量做到钜细靡遗,方能一窥全豹。学者研究梁启超迄今累积不下数十家,然而真能将梁氏这一个有血有肉、真情至性的人物描绘得真切,几家能够呢?”(同上,第23页)唯有下过摩挲书信原件工夫,这样的话才能说得如此真切!
就档案、日记与书信三种史料而言,档案材料是通过选择甚至删改而保存下来的史料,其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而日记尤其是有意识存留给后人看的,记录者所记也往往是过滤以后的“第二手史料”;唯有书信,往往是当下反映微末琐事,却更能真切地表达一个人当时的内心世界与真实史实。正如作者所说:“书信原迹笔触不经意所反映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细微、最错综复杂的思绪,在后人编纂文集中是不易显见的,同时也最被忽略,唯有深入其间反复模拟想象彼时环境氛围,体会作者悲、欣、愁、嗔等情感,企图使‘场景再现’,透过书信原件的‘抽丝剥茧’,其文献价值自然彰显。”(同上,第24页)吴铭能此言,既是他切身的体会,又可谓要将绣鸳鸯金针度与人矣。
三、在臆想与史实之间寻觅真象
史学工作者,总是想尽量客观地评判历史,但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意识形态等,也总是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人们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我们以《历史的另一角落》书中研究陈独秀的两个例子,看作者是如何以细密的绣花针功夫,来破除臆想,寻觅史实的。
陈独秀有一首写友人聚饮的诗:“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本诗向为学术界所关注,研究者或将其断为1941年7月作,且认为陈独秀也参加了聚饮,或以为是陈氏晚年“贫困交迫”之下“意志消沉”的表现。但吴教授在对陈独秀写给台静农的书札中考证出了此诗的本事:先是,在该年端午节当天,有台静农、魏建功诸人聚饮大醉事,而此时陈氏并不知悉;后得知此事,遂于6月15日复台氏信,称自己“闻兄等痛饮,弟未能参加,颇为惘然”。由此可知,陈诗作于六月某日,且以未能参加聚饮为憾,只不过是常人所共有的普通的一时的“落寞怅惋”而已。(同上,第268~270页)
吴教授进一步指出,研究者多忽略了一项事实,处于陈独秀晚年时代的学者,如魏建功、台静农、陈寅恪等人,皆过着贫穷且多病的生活,“乃是普遍现象,不独陈氏如此”。但研究者显然是将此事件孤立为陈独秀晚年独有之不幸,并想当然地臆断陈氏“意志消沉”。
又如,上个世纪前期,关于汉字拉丁化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许多名流学者都参与其中,陈独秀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力主语言文字大众化,由繁入简,最后目的是汉字拉丁化即拼音文字。但台湾学者郑学稼的《陈独秀传》却认为,“这是中共宣传,非独秀本意”,“独秀绝不会主张‘拉丁化’,而况事实上是‘俄文化’”!吴铭能兄通过陈氏给台静农的书信,以及其《小学识字教本》的编纂等,揭示出陈独秀对于废除中国文字的看法,终其一生没有改变。而郑氏未能深入寻觅史料,却本能地出于反共立场,强做解释而有此误。(同上,第114~116页)由此可见,如果不花力气寻觅史料,而又不自觉地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可能会得出与史实相反的结论。
四、重视名家手迹原件所透露的蛛丝马迹
吴教授在本书中指出,名流手迹出版,大略有三种形式:“一是原稿影印,并附以现代楷体文字对照”,“第二种是仅照原稿影印出版,不提供任何楷体文字对读说明”,“另外一种是仅以楷体文字编排,没有原件对读”。(同上,第271页)
以上三种整理方式,当然是以第一种为最佳模式了,很多研究者在利用到这样的整理本后,便放心地利用其材料,不再与原件对勘与核检,但实际上是靠不住的。名家手迹尤其是书信等,与一般刻本的不同在于:一是它们往往是用行楷,甚至草书来书写,识读为难;二是经常会涂抹删乙,版心边角,书满文字;三是每个名家的书写习惯与书法,皆有不同。正因为如此,即便是长期研究某一名家的学者,也很难保证在释读其手札时完全无误,吴教授在释读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手迹时,经与原件的仔细核校,就发现了整理本的许多讹误。不仅如此,吴铭能还指出:“任何文献的复制品,其纸张的质地与历史感均不可能与原件一模一样再现,换言之,‘历史文献’的复制,最多只能呈现可见的内容,至于研究者对历史事件与人物体会的深浅,披阅解析,境界本就有远近高低的不同。”(同上,第271页)
例如在阅读梁启超书信时,吴教授就注意到民国十三年梁氏在汤山养病期间,因为当地的水质不好研磨,令他深致不满;同时也注意到梁氏在给女儿的信中,曾为新造的信笺好不好专门试笔,并征求女儿的意见。由此通过对墨色与信笺的要求,感触到梁氏“一种文化品位与学者气质,完全在写信中展现开来”。(同上,第22页)又如,吴铭能在核对陈独秀与台静农的书信时,还在台灯下仔细研究近百个信封,有的是以广告纸剪裁粘贴而成,有的是友人来信的封套,拆开反贴重复使用,由此看出陈氏的爱惜物资,并指出“这些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正透露他生活上自奉俭朴的讯息”,并且认为这并不一定和他晚年的困窘生活有必然的关系。(同上,第268页)
五、口述历史:信与不信之间的两难境地
口述历史,是近些年来兴起且越来越热门的史学记述方式。但口述历史的可信度如何呢?如何使用此类史料?学术界也是说法不一。吴教授对台湾有名的“二二八事件”的口述历史材料进行了详悉的对比,从而呈现了“口述历史”的困难。吴铭能以为,“‘口述历史’的困难,不仅仅在于受访者愿不愿意接受访问的问题,也不在于受访者的记忆模糊,而症结在于受访者可能受到不同情境氛围的影响或情感伤痛煎熬导致精神状态不佳,辄对往事做了(可能无意识)过度想像的描述,如果不加细察,往往会陷入一团迷雾中”。(同上,第309页)
的确如此,口述历史的大部分史料,是在事后通过采访或者搜集得到的,而允许采访当事人的时间,往往是这些事件被“平反”或者得出“定性的结论”后,因此被采访的对象,在口述历史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受采访者的目的所引诱,或者受此“定性的结论”影响,要么夸大,要么贬低,要么轻描淡叙,要么浓涂重说,后人皆以信史待之,就会更增一层迷雾。
对于其解决之道,吴教授建议将口述历史与档案史料相配合,口述历史才能得到更有说服力的支撑,“但这之间仍然具有主观因素的成分涉入其中的灰色地带,并不完全能够客观超然”。(同上,第318页)
以上论述可知,《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一书不仅仅是在研究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学行,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对档案、手札与口述历史等史料的释读与运用问题,是一部研究历史并兼谈史料学的书籍,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如果能认真一读,仔细品味,定当有不少的收获。
另外,本书中也有个别错讹之处。如书中引用梁启超约友人打牌之书信,有“春秋佳日易过,一往便当赋,苦热行矣”之句(同上,第13页),案此当断句为“春秋佳日易过,一往便当赋《苦热行》矣”。唐王维、王轂等皆有《苦热行》诗,梁氏此处之意,谓至夏日,则当诵前人《苦热行》诗(或自作《苦热行》)矣。又如书中有“前清干嘉以降”句(同上,第60页),此“干”当为“乾”之误;又“吾粤人知有汉学,实先生道之”(同上,第62页),此“道”当为“导”之误,这些显然是汉字繁简转化不当出现的错字。希望本书在再版时,能再细勘一过,以便读者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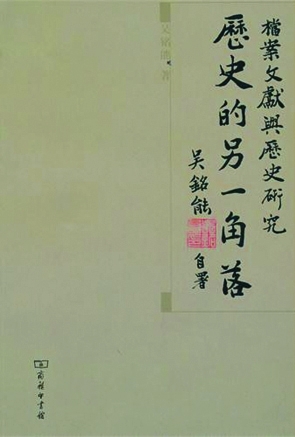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