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封家书和谭安利74岁的身体一样,在一点点衰老。
这个湖南茶陵的普通家庭,经历了百年沉浮。谭安利的母亲曾和陶铸假扮夫妻,保护地下党机关,也为了革命工作不得不舍弃自己的两个孩子。现在谭安利已经很少和孙辈讲起那些故事,“毕竟时代不同了”。
每一封信背后都是一次别离。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看来,谭安利保存的1500余封书信集结在一起,就是一部家史,“由此扩大到一个又一个家庭和家族,这些构成某个乡村、某个社区的历史,然后再扩大到某个地区或区域的历史,再扩展,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没有个体的贡献,就没有国家历史的宏伟大厦”
谭安利的家,几乎要被深圳的高楼大厦淹没了。他和老伴住在不到60平方米的老屋子里。如果不是保存在屋子里的一封封家书,它看起来和周围许多普通家庭没什么两样。
从老家湖南茶陵到长沙、衡阳,谭安利在定居深圳之前数不清搬过多少次家,衣物和行李都扔了不少,“鞋子永远只有一双”,但这些信却大部分都保留下来。
他11岁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寄宿,很少和母亲见面。“文革”中母亲被隔离审查,哥哥在另外的地方上班,弟弟成人以后,就作为知青到了农村。一家人分开的时候,多于团圆的时候,四散在各处的家人,通过书信保持着联系。
他曾想过要孙辈继续写家书,就像小时候母亲教他和弟弟写信那样。可是“现在孩子学习太忙了,日记都写不了”。谭安利每周都和几百公里外的女儿、外孙视频,可“都是在就事说事,很少谈心”。
书信的衰落让谭安利担心。他想尽各种办法保存这些脆弱的纸张。在报纸上看到有博物馆收藏家书的消息时,他立刻就联系了捐赠。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是中国首家以家书为主题的博物馆。学历史的张丁看重的是每一封家书背后的家庭历史,“平民并不仅仅是历史舞台的背景,也是在舞台前部活动的演员。没有每一个个体扎扎实实的贡献,就没有国家历史的宏伟大厦”。
1500封家书勾勒一个家
谭安利的1500封家书拼凑在一起,一幅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悲欢离合画面也逐渐被勾勒出来。
14岁离开家以后,母亲谭珊英就一直在四处漂泊。在厦门的地下党机关,她第一次见到陶铸。那时的陶铸“穿一身青布学生装,留着分头”。假扮夫妻时他们住的屋子“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外,别无他物”。谭珊英晚上睡帆布床,陶铸就用席子摊在楼板上睡。早餐啃大饼馒头,中晚餐买一份盖浇饭充饥。
除了谭安利兄弟3人外,谭珊英还有一双儿女。第一个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节,是个女孩儿。那时,谭珊英正在“白色恐怖很厉害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上海的生活艰苦极了,女儿出生后,她没有喂过一口奶,只买了一磅奶粉,就被丈夫陈柏生用绒毯包着送去了美国人办的公共育婴堂。后来,她和陈柏生去苏联学习前夕,又生了一个男孩,为了不耽误行程,她把孩子送给别人照看,不到一周岁就病死了。
经历过那么多分分合合后,谭珊英变得越来越平静。谭安利和大哥陈洣加都不记得见过母亲悲伤或者愤怒。但在1961年,当3个儿子中有两个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才在正月初七无奈地给谭安利写信:“本来以为你和哥哥都会回来过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谁知你俩都不回来……这又多少使我失望。”
那时物质匮乏,“回来除了精神上痛快外,吃是没有多少吃的”,乡下种的菜也都被人偷了去。即使如此,谭珊英还是随信给儿子寄了自己做的糯米粑粑,“十二个糖的,卯了红点,八个菜的,共二十个。另外给你附来一点腊鸭蒸盐菜,鸭的味道不错,不过份(分)量不多,给你尝尝”。
这些家书“也打开人性的一扇窗”
谭安利一家一直在时代的潮流中起伏。少女时代就离开家的母亲,直到1948年才彻底回到茶陵。那时这个家庭和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
外祖父的1个儿子和3个女儿中,母亲是那时唯一归来的。家里没有她的田地,她只好在村子里的宗族公共食堂吃饭。直到1950年,谭珊英才有了工作,在小学教书。
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跟谭珊英取得了联系,写信告诉她:“你的工作除已函告湖南当局通知茶陵县政府为你设法分配工作外,此次见到谭副主席(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记者注)又当面与之谈过,当一定为你设法也。”
当时谭珊英也可以去银行机关工作,但是她还是选择留在小学。从那时直到退休,她一直都是当地普通的一名小学教师。
在那个年代,这个家庭并没有享受多少团聚时光。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在这个家庭里掀起波澜。文化大革命开始,谭珊英因为陶铸的问题被牵连,隔离审查,然后是关牛棚,下放五七干校。其间整整3年,都无法和家人见面,连通信都断绝。
谭珊英也曾写信给孩子,希望“能回来转转,多给我以思想上的帮助”。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愿望只能落空。谭安利回忆,在母亲被关牛棚无法与兄弟见面的那3年,都只有他们兄弟3个凑在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谭安利决定把1500余封家书全部捐给家书博物馆。如今,已经有5万多封家书藏在这里。这些来自普通家庭的书信,曾经和中国最重要的文物一起,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也在最近登上了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的舞台,和张涵予等明星一起,在网络上“红”了一把。
在这档以读信为主的综艺节目中,“不仅打开历史的一扇窗,也打开人性的一扇窗”是总导演关正文一开始就定下的选信标准。
关正文说,之所以观众有共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丰沛的价值认知”。本来无意发表的书信,“就像一个人在自己家客厅一样,穿着随便”,展现的都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打开历史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获得关于历史的知识,而是帮助你认识社会和自身。”
“夜晚仰望星空,心中几多梦幻”
谭安利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家庭的重要性,他努力把家人团聚在一起。可是如今在深圳待久了,他已经慢慢不能习惯老家湖南的气候和氛围。
去参加革命前,谭珊英已经从湖南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在当地谋一个教职并不是难事儿。但是这些,都比不上热闹的革命气氛给小女孩儿带来的吸引力。再次回到茶陵,就是差不多10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一次回茶陵,她生下了大儿子陈洣加。谭珊英本来给孩子取的名字是“洣家”,“洣”是距离茶陵美吉村不远的洣水,“意思是要以洣水为家”,但是在那不久,她带着孩子又离开了茶陵。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也没有回到茶陵的家。
从苏联回来后没多久,谭珊英的第一任丈夫陈柏生就因为肺病去世。1942年国共合作期间,谭珊英经人介绍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李华柏。李华柏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副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谭珊英随着工作四处搬家,随身带着的“只有一个包袱和一个皮箱子”。茶陵老家的房子因无人居住渐渐荒废,最后卖给了别人。
谭安利记得,因为生父李华柏的关系,“初中以后所有事情都靠边站,不能入团不能入党。”高考他成绩再好也只能被第三类院校录取,而且只读一年又被“扫地出门”。生父的身份甚至让谭安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次参加高考,而曾经和谭安利做过一年大学同学的李国杰,后来重新通过高考于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他记得,那时和李国杰是谈得来的好朋友。他们经常在操场上看星星。书信在两个渐行渐远的好友间维持着日常信息的交流。最近一次的信写于2009年,在这封介绍近况的信中,谭安利写道“我不能忘记,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岳麓山下同窗共读,夜晚坐在草坪上仰望星空,心中几多梦幻”。
书信提供的认知价值
当这家人再次分散于全国各地,整理并出版家书是谭安利和亲朋重新建立联系的途径之一。
家书一遍遍翻看得多了,谭安利对家和家人有了更多理解。他理解了父亲也是参加抗日,只不过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曾经的勤务兵带来父亲的大女儿在湖北的消息后,谭安利几乎想都没有想,当天晚上就给胞姐写了信。“尽管四十年前我母亲谭珊英正式声明与李华柏脱离家庭关系,我的籍贯也一直确认为茶陵,但血缘方面的关系仍是客观存在的。”
后来,他和三个胞姐见了面,最近一次见面就在去年,一起吃了饭,热闹了一天。谭安利还专门录了像,刻了光盘。他明白,这样的相聚机会不多了。在世的姐弟几人中,他最年轻,也已经74岁了。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书信产生兴趣。《见字如面》火了以后,关正文甚至开始收到有人专门手写寄来的书信,“明明大家有微信,有电子邮件,但还是要手写一封信”。
(《中国青年报》4.19 陈卓)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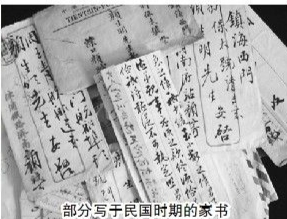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