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阅读,是因为我想在别处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一天读书8到10小时,日日年年都如此。甚至更多。读书是我最喜欢的事,再无其他。当我七岁那年,在一辆巡回贵格城的流动图书馆上借书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了。用弗兰索瓦·拉伯雷的话说:我天生如此。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阅读如此痴迷:我阅读,是因为我想在别处。不错,我身处的世界、特别是这个社会还算差强人意,但书里的世界更美好。一个人要是特别穷,或者缺胳膊少腿,这种感觉就会更明显。当年,我受困于保障房内,面对表现糟糕的父母,才开始了疯狂的读书生涯,好像没有明天。而且我深信,这种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会产生的逃离现实的欲望正是人们读书的主要原因。他们阅读,是为了逃入一个更激动人心、更有价值的世界。在那儿,他们不会讨厌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伴侣、他们的政府、他们的生活。
读书本是闲情乐事
我不做快速阅读。读书本是件闲情乐事,快速阅读似乎违背了它的本意。13岁那年,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发现一个工具,可以通过转动手柄调整速率,令一把小尺在书页上滑动,就像死亡神庙的大门,一行行遮住字句,强迫使用者提高阅读速度。我猜它的效果不错,但用起来肯定叫人火大。这是那些六十年代做码表时间研究的专家发明的。在我小的时候,快速阅读十分风行,人人都想学会这一招。那帮大腹便便、胡话连篇的专家一再向我们保证,学会这个技巧,功名利禄便唾手可得。虽然他们自己是永远不会知道的。我从来不会在吃饭和看电影时快进,所以,我为什么要在读书时快进呢?只有那种很烂的书,我才会考虑速读。但现如今,我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读烂书了,除非有人出钱叫我写评论,或者是遇到那种因为差到极点而引人注目的书。
除非有人给钱,不然我才不读商人或政客写的书,关于这些人的书也包括在内。我也不建议别人去读。这些东西都差到不能再差。他们用的是同样的代笔人、同样的书稿顾问,哪怕那些自称亲自写作的,也会落入暴躁、平庸的文风俗套,显然是从他们同僚花钱雇用文人写的那些书里学来的。这些书读起来都一个样:励志,真诚,杀伤力大。评论这些书就好比评论刹车油:用起来不错,但谁又在乎?
艺术不简单,文学比杀人还难
我有几百本硬壳精装书,其中不少是有一定年代的。但我的大多数藏书都是平装本。现在的平装本包装得十分吸引人,故意引读者上钩,让他们以为里面的文字也和外面的设计一样迷人。事实往往并非如此。画一幅漂亮的画,或拍一张诱人的照片,要比写一部漂亮的小说更容易。毕加索的名画有几百幅;拉尔夫·艾里森只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艺术不简单,文学比杀人还难。
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我一般都会在书的内页签名,写上购买日期及书店所在的城市。如果我没有在内页签名,那是因为我已经确定此书不值得保留。至于书店的名字我是不记录的。恐怕因为内页上有了“鲁昂书店”、“城市之光”或“烂封面”,总会召来愉快的记忆,而“博德斯”,则完全无法引发联想。话虽如此,我在博德斯还买过不少书呢。
没办法用Kindle做的事
我有时会读朋友们推荐的书,但不怎么借来看,几乎总是自己去买,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我很早就养成习惯,在阅读时勾画印象深刻的段落,并把奇怪的或者不常见的词记在书后的空页,方便以后查字典。有时候我甚至会把自己的便条、待办事件清单、时间表之类也写在书上,不过我通常只有读诗时才这么做,因为诗选留白的空间很多。
在自己的书上写东西很开心,这也是我不看电子书的原因之一。书是我的护身符,是死亡的象征,也是玩具。我喜欢和书玩游戏,给它们做记号,留下访问过的痕迹。我喜欢把它们堆在架子上,移来移去,按照新的参数重新排列——高度、颜色、宽度、产地、出版商、作者的国籍、主题、我读这本书的可能性。我喜欢从架子上拿下书,朗读美好的段落,难为那些来我家的笨蛋。从我拥有一本书的那一刻起,哪怕还没翻开第一页,我已经觉得它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像对待衣服、鞋子和唱片一样对待书;我使用它们。你没办法用Kindle做同样的事情。
讨厌被别人强迫看书
我讨厌被别人强迫看书。我一直认为,把别人不想读的书硬塞过去,会给人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就好比问也不问人家喜不喜欢香菜,就强迫别人吃印度鸡肉焖饭一样。强迫我去读的书,就好比我不想吃的圣诞布丁、我不愿听的克莱兹默唱片,会被我一直搁置在原地。为此我不会受到良心的折磨,因为强迫别人读书的人并不想把书要回来。他们自己也没读过,甚至没有阅读的打算。
《时间简史》卖了八百万本。这个星球上能看懂这句话的可没有八百万人,八百人都没有。可能有八个人能看懂吧,但我不是其中之一。买下这种书的人会把它放在靠近前门地方一年左右,有时候会用来压一压邮票,或者砸向变心的情侣的后脑勺。然后,这书就被放在了私家车的后备箱,直到有一天丢给某个看起来挺聪明,足够理解这本书的人。借书给别人其实是清理房间的狡猾办法。
作家才是分发圣餐的人
我喜欢讨论书籍,但我不喜欢和群氓讨论。爱书人和不爱书的人在一起时,后者会主导谈话的方向。话题只能是你们都看过的书,而这个交集小的可怜,要用显微镜才能找得到。
在脑海中虚幻的房间里,爱书人和作家进行着亲密的交流。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他之所以读索尔·贝娄的书,是因为贝娄看起来人生经历丰富,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些东西。我对自己喜爱的作家也有同样的感受。如果你已经老了,想早点退休,应该先读读《李尔王》。如果你已经人到中年,想和比你小的女人结婚,不妨咨询下莫里哀的意见。如果你还年轻,相信真爱天长地久,还是先看一眼《呼啸山庄》再做长远规划吧。
爱书的人觉得作家透过纸页,在直接和他们说话,甚至在关照他们、为他们疗伤。他们有时忘记了作家才是分发圣餐的人。人们老说,他们之所以热爱这个或那个作家,是因为他或她就某个话题写出了读者想说的话。在他们看来作家是某种通灵的容器,为没有声音的东西发声。我从来不这么想。我觉得作家用我永远想不出的方式讲出了我永远想不出的话。
(摘自《大书特书》,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版,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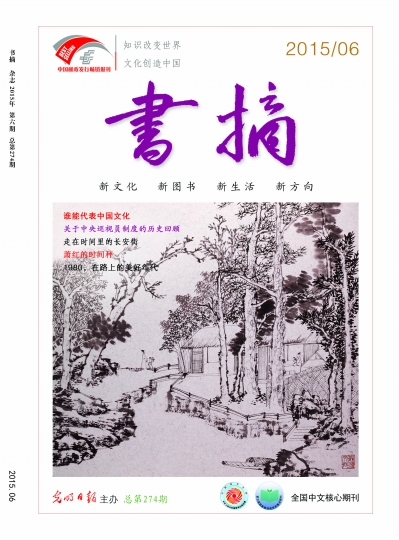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