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挤的车站,混乱的码头,岁尾年关千里奔袭、穿越风雪的摩托车队……说到中国农民候鸟一般从乡村到城市,从异乡到故乡,你难免会想起这些奔忙于路上的种种场景。和“出埃及”一样,“在路上”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没有“在路上”,也就不会有希伯莱人的“出埃及记”。没有“在路上”,凯鲁亚克的著名公路小说也不会流传为经典,更别说在其后催生出与“在路上”相关的一系列文化。
1980年代(有人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从1976年到1989年),伴随着大批青年回城,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也开始试图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宽阔城市。
这是一个让人讴歌的年代。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万物开始解冻复苏,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在朦胧的爱意里竞相绽放。
毫无疑问,此前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告别“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与领袖崇拜便已经代表着某种政治理性的回归。至于社会理性在什么时候开始回归,似乎没有可量度的标准与标志性事件。不过,找到一些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并不难——当然,这同样得益于政治上的部分解禁。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政治禁书”、“被流放的知识”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视野之中。
对于那个书籍极度匮乏的反智年代里的悲伤故事,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略有记载: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余生也晚。和王小波比,虽然我也曾经在乡下生活了不少岁月,但我似乎要幸运得多。因为当我青春萌发,开始极度渴望知识与书籍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热与文化热。
1980年代的十年,文化热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尤其从1984年开始,有关哲学、政治与社会的讨论大量增加,文化活动四处开花。一些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陆续在郑州、上海、深圳、武汉等地举行,许多名牌大学也都建立了关于文化、文化传统、儒家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中心,各地纷纷组织面向公众的传统文化讲习班,无数关于文化的文章充斥各类刊物,各种文化类书籍摆满了书店。那个年代还没有哈里·波特,但正如陈彦先生在《中国之觉醒——文革后中国思想演变历程》一书中所描绘,1984年到1988年间的中国,南南北北像是中了“文化”一词的魔法,“文化这个词与主题成了当时中国真正的时髦”。而1984-1986这三年铸就的黄金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环境较为宽松,文化热可谓如日中天”。
和今天堆满大小书店的各类考试学、成功学书籍相比,八十年代人们的读书生活显得更有品质。此时,哲学、美学、小说、诗歌、科学等各类书籍纷纷涌现,欧美的各种经典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诸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等都成了无数才子佳人的枕边书。1984年3月,首套“走向未来丛书”12种出版。第一批书仅用了4个小时便在成都售罄。3月底,出版社重印了3万册,又在几个月内全部卖光。其后的“五角丛书”,几年间销售了一千多万册。
尽管仍然实行着严格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九十年代初我离乡上大学时甚至还必须从家里寄上一袋大米给学校——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十年代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远不如九十年代以后那么明显。那时候,即使一个像我这样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小学生,也经常有机会被母亲带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课外书。母亲识字不多,每次都会请教书店里的读书人我挑的书是否真的有助于学习。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有时还会让隔天进城的村民将我要买而未买的书给捎回来。然而,这个中间环节可能会出问题。比如,有一次我发现有本作文书前面少了几页,却又不好意思责备给我捎书的村民买了一本残书,只好将就了。直到几年后,我才在无意间知道这位村民因为半路内急,撕了前面几页擦了屁股。这个细节在我看伊朗儿童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时总会想起来——成人总是在不经意间毁坏儿童的世界。
拜赐于当年的读书热,我在中学的图书室里也没少找到流行于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让我备感吃惊的是,2008年我重回母校时,发现由于近年来农民拖儿带女大量外出,当地生源急剧减少,学校因此变得无比萧条。而当年那间让我垂涎欲滴的图书室如今空无一书,像遭了洗劫一样,只剩下满地的灰尘与几块断裂的架板。据留守的教师们说,许多老师都去沿海“打工”了。而当年那位曾经住在图书室边上的有志青年,早已弃教下海,远走他城。
时光悄然流逝。我已经记不清在这所学校读过什么书——舒婷、北岛、三毛、席慕容、彭斯、歌德、泰戈尔、海顿斯坦、聂鲁达、普吕多姆、蓝波、雨果?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身处乡下,借着当时席卷全国的文化热与读书热,我还是有机会读到过几本即将影响我一生的书籍,有机会亲历《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里文化相遇之奇境——只不过,那位最初影响我的外国才俊不是戴思杰笔下的巴尔扎克,而是英伦岛上的雪莱。在我的书房里,至今仍保留着我在14岁那年买到的杨熙龄选译的《雪莱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正如傅雷的译者献辞为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锦上添花——“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杨熙龄写在雪莱诗选后面的《译者附言》同样让我一生受益。
我相信,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每个人在其年少时都可能有着某种兼济天下的理想。回想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更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歌加论文”的年代——在此之前,写《未央歌》 的鹿桥曾经用“诗歌加论文”来形容他在西南联大时“有理性,亦有心灵”的美好人生。因为诗歌,许多人在清贫而跳跃的生活中一厢情愿地做起了精神贵族。若非如此,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样一本薄薄的《雪莱抒情诗选》能够畅销10年,足足卖出50万册。此前,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本诗选从1964年排出清样到1981年终于出版,足足等了17年。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意与想象的年代里,才有了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姐姐,今晚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样温暖人心的诗句;才有了《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这样共写心灵史诗的流行音乐;才有了雄心勃勃、壮志满怀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夜晚,当我偶尔听到电视里播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老歌,想到当年高唱凯歌的年轻一代如今纷纷下岗,心中竟涌起一种莫名却又难以抗拒的伤感。然而,即便如此前途茫茫,谁又能否认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刚走出时代“黑屋子”时的意气风发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无比赤诚?
我在梳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记忆时,找到了一些相关的影像志。它们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那个时候的人们虽然处在一种普遍的贫困中,但是整个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在外电报道中,这次会议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壮观的政治仪式,而是一次做出重大决策,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民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第一次邀请外国记者参加,并事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驻京外国记者感叹道,上一次召开人代会的时候,外国记者都被送到天津去旅行,人代会就像一次地下会议,甚至不许代表们告诉自己的家属,只是告诉代表们要带些钱和粮票。
在这种气氛之下,有人担心自己怕是要遇到什么麻烦了。这次会议也是充满直率的、生动的言论的会议,第一次出现了人民代表毫不客气地质询部长的场面。国外报道的结论是,中国正在谨慎地,逐步地成为较为开放的社会。(《电视往事》解说词)
我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美好年代,是一个“恶补禁书”的年代,并非要武断地赞美那个时代完美无缺,或者断定它比现在这个时代好。
我上面提到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同样以其坎坷见证了时代命运之波折。1979年2月,当谷建芬在家里为这首歌谱曲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受到批判。三十年后,谷建芬坦 承这首歌给她带来了灾难。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反党歌曲,他们甚至给谷建芬扣了一顶帽子,叫“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还有一顶帽子是“用资产阶级的音乐毒害青年”。而谷建芬 的另一首歌曲《烛光里的妈妈》也被定性为建党以来最大的反党歌曲,因为里面用了这样一些句子形容“妈妈”——“您的黑发泛起了霜花”、“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您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不愿牵着您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等。有人说“妈妈”就象征党,你把党说得这么糟,这还了得。那时,在北京举办的创作研讨会上,电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也被批判为流氓歌曲。
我只想在此强调,那个心灵与理性的花朵并蒂绽放的年代,在其匆匆落幕、戛然而止之前,人们已经重拾生活的美好理想,紧随自己命运的召唤,开始追求心中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追求一个甘于平凡的理想的世界。
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刚刚从社会混乱与政治高压中走出来的他们,已经看到了隧道外的一丝丝光亮,初尝了长在新时代路边的一枚枚禁果,像是怀着一种初恋的心情,试着一步步走向开放与自由。
(摘自《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新星出版社2015年2月版,定价:4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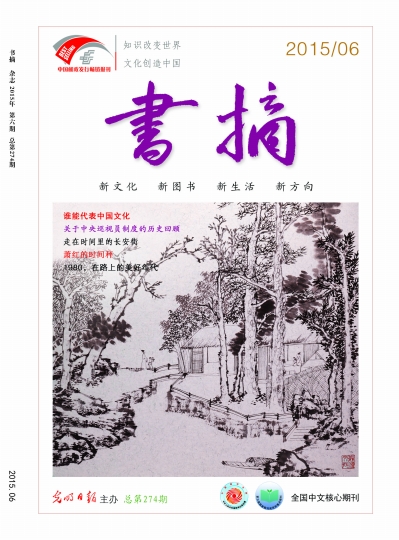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