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闻天、弼时等搬到杨家岭后,和主席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接触越多,了解越深,也就越加敬佩他。从各个方面讲,他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从他的身上得到的教益终身难忘,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之中,历历在目。
我是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任务是参加七大,然后回莫斯科汇报。因为当时派个洋人到延安来执行此项任务实在困难,也几乎不可能。回国之后,我才知七大的召开推迟了。恩来决定将我安置在弼时那里,名义上是弼时的秘书,实际上给主席担任俄文翻译。我的国际身份在中央只有主席、弼时,恩来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1942年末,苏联的飞机到延安来,捎来共产国际的口信,让我回去汇报工作。那时苏联的飞机差不多是一年来一两次。
听到苏联同志带来的这个口信,主席一愣,眼睛望着我,意思是要我表态。
我马上说:“不回去。”
主席说:“那好,你和他讲。”
我当着主席的面对苏联同志讲:“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国局势紧张,任务繁重,我不能回去。”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我将国际的来电译出之后读给主席听。主席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然后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你也不用回去了。
1940年我回到国内时,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经牢牢地确定了。但他每走一步都要再三试试,对大小事都是如此,都要摸准、吃透,要有十分把握才做。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一定要观察上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能力、为人和表现如何,才决定是否起用。主席常讲,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由于种种原因,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罗迈(李维汉)这些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当年我都不便过多地接触,对王明、博古就更不待言了。延安整风之后,1943年1月,我到边区保安处去工作,后又被派到绥德、关中。经过几年基层工作的考验,到七大之后,主席大概认为可以使用和信赖我,于是让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他这样对我说:“现在你担任了书记处办公室的工作,我有事就可直接找你,有话也可以找你谈了,比你在弼时同志处工作时要方便得多。”其实我从1940年末起一直为他做俄文翻译。
康生很会钻空子。1944年夏天,他将我从保安处调到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他告诉毛主席:“师哲已调到中央社会部,住在枣园,主席如有什么事找师哲很方便。”康生对别人说是他将我介绍给主席的。其实毛主席早已和我有电话联系,有必要时就找我。
我刚到枣园不久,主席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很奇怪,主席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搬进枣园呢?他将我找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由此知道康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
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抗日战争期间他反复地讲对敌要狠,对内要和。
张闻天的理论修养较高,有威信,但对问题的态度有时没王稼祥那样明朗。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一票起了关键性作用,主席十分重视此事。主席很注意团结他们,请张闻天和中央的五位书记一起住在枣园;整风时让王稼祥当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成立时,召开成立大会,主席不但出席而且亲自主持。但是稼祥当时表示对这些都不积极。我在研究室算是王的第一助手,我向他请示工作,他大多不吭声。研究室的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
主席让他们参加重要的座谈会、出席中央会议、政治局会议。不仅对他们如此,对他们的部下,如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等,也吸收列席政治局会议,对他们在生活上的照顾更不消说了。
遵义会议后,对遵义会议决议不理解,顶得最厉害的是凯丰,但主席对他也是采取团结的态度。
1937年底,王明从延安到了武汉。当时,武汉有政治局委员四人: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王明企图搞成第二中央,对这点凯丰是不同意的。毛主席把这些都记在心里。
1942年,主席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让凯丰主持会议,并讲话。
凯丰是个有主见的人,头脑清楚,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七大闭幕后,军委召开座谈会批评彭德怀,找了许多老干部,特别是苏区的干部,范围较广,连我的夫人周惠年(她在苏区待的时间很短),也接到通知参加了会议。凯丰却不出席会议。一天他到枣园来玩,对我谈了一点情况。他说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主要批判彭总两个问题,一个是百团大战;一个是说他一贯不听毛主席的话。凯丰讲:百团大战,彭总请示过主席嘛,当时主席也没有讲过什么话。彭总虽然当过旧军队的团长,但这是入党之前的事,是过去的事了。彭总态度有些骄傲,有些过于自信,但是也不能这样搞。凯丰认为,彭总在理论上,出谋定计方面都不如主席,但是他性格耿直,拥护真理、坚持到底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即使凯丰有不同的看法,主席仍是团结他、任用他。
主席很重视地方干部,他讲过:“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他也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他特别讲道:“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刘志丹牺牲之后,毛主席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说,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了,按资历就数高岗了。当时高岗在内蒙工作,主席把他调回来负责西北局的工作。其实高岗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有限,特别是他的品德不好。但主席对此不了解。主席看人不仅从大处着眼,而且也注意一些小事,观察你的衣着、表情、言谈和举止,以了解你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比如,我在国外住得较久,养成打手势的习惯。西方人认为打手势可以加重语气,主席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年轻人在年纪大的人面前、在长辈面前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解放后,立三对总理讲:师哲在苏联做保卫工作的,讲话用辞一贯粗鲁。总理转告主席。主席一听心里自然明白,说:我还是用师哲当翻译。主席用人考虑很周到,不仅看你的表现、才干,还要看你的历史、社会关系、工作态度以及所能起到的作用。因李立三在苏联受过冤枉,坐过牢,他如果用李立三当翻译,苏联会怎么想。我出国时,主席请刘亚楼做翻译。
主席炯炯的目光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共约十八年之久,从未看到他发脾气以至到了拍桌子打板凳的程度。他是很有涵养的。有一次,我对他说:“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
他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这就更不容易了。
主席的目光炯炯有神,非常敏锐。他狠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错了。他讲话很注意逻辑,也很注意分寸。我在他面前讲话,有时讲错了一句话或一个词,他就用眼睛盯着我,说:“你再讲一遍。”就这么一句话,便能提醒我,使我马上发觉自己讲错了,赶快纠正。
我们住在枣园时,时常到杨家岭礼堂看戏。主席坐宋庆龄送的一辆救护车。许多青年人向车上爬,凡是挤上来的都可以去礼堂,主席从不干涉。大家坐定了,在路上,有时主席问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讲话时,他的眼睛注视着对方。事后,这些年轻人对我讲:“我看见主席就害怕。他望着我,几乎要把我看穿了。”
主席的厉害也就在这个地方,他把什么事都要看穿,弄个明白。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专注,入木三分。
主席对干部是爱护的,特别是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你做了错事,他要是处罚你,就表明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他不再记在心上。初进中南海时,我去丰泽园,偶尔看到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院子里晒太阳,满头大汗,却一动不动。别人告诉我:“你不要管,这是主席罚他们呢。”主席不是朝三暮四的人,干什么事一定要干到底,要干出个结果来。如果被罚站的人中途走开,那,主席就不能原谅了。主席处罚人就是这样,处罚了,很快也就原谅了。
主席生活简朴,从不挑剔。只是爱抽烟、喝茶。偶尔搞到鲍鱼、鱿鱼,可以吃,没有,不吃,也没关系。他进了城,生活改善了一点,也就是每周吃一两次红烧肉。
主席自己有个小灶,有炊事员专门给他做饭。他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大多是白天睡觉,夜里工作。有一段时间有人要求中央领导人过集体生活。办公厅决定首长们都到饭厅吃饭。主席来了吃了几口米饭,说:“这是什么东西?稀饭不是稀饭,米饭不是米饭。”
我说:多数人都要求把饭做得软些。
他说:“那要牙齿干什么?!”就吃了这么一次,他再也没有来过。主席吃饭十分简单,生活一贯简朴,他的炊事员、理发员、司机一直跟着他,都从陕北到了北京。
我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工作时,对首长的警卫员不从警卫团里挑选,而是从前方野战部队选调,先送进中央党校学习、培训,然后直接分配到各个首长身边。这个规矩从在枣园定下后,一直沿用到进城。主席对警卫员的态度是很好的,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甚至连他们的婚事也都管。阎长林、李银桥等同志都有回忆录,我不再赘述。
主席一心为公,身体力行,不仅将全部的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独立、自由、自主的事业上,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妹妹、妻子及其他亲属参加革命,为革命献出了六个人的宝贵生命。这种情况不仅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就是在全党党员中来说也是少有的。毛主席就凭这几点:一、绝不爱钱,不为私;二、不让亲属子弟沾公家的光;三、全心全意奉公;四、牺牲自己及亲属。我们还能再说什么,还有什么苛求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主席也有弱点、错误,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弱点是出国次数少,对国外、国际间的事了解得少些。他总是以中国人的意识、思维方式进行逻辑推理,这是不够的。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才用聊天、讲故事的方式谈出我的想法,用以提醒他体察国外的风俗人情。但我从不坚持己见,他能听多少就算多少,就事论事地谈谈。须知主席是位个性十分倔强的人,好胜的人,从不服输的人。列宁讲得好:“鹰有时可能比鸡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
(摘自《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版,定价: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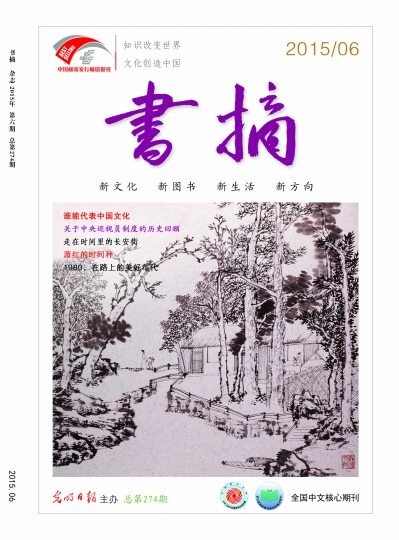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