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董遇是个好学之辈,又勤于劳作,便把读书习文的事儿放在三个时间段,即:“夜为昼余,雨为晴余,冬为岁余”。由此可知,董遇是个北方农民。“夜为昼余”不必多言。雨时不能耕作,便是“晴之余。”冬天大地封冻,无农活可做,又近年关,便是“岁之余”。
我喜欢这“三余”,因为我做不到利用所有的“余”来读书习文。于是,我给自己的书房挂匾:“三余堂”。
有了“三余堂”,我的那些“余”,依然被我随意挥霍。不是事务繁忙,不是红尘猛烈,是我没野心或无大志矣。
读钟嵘的《诗品》,对一段话感受颇深:“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窃以为,此乃全书立论之基石也。
诗,一定要有“气”。
我对一首诗的判断,首先看其是否气韵贯通,气势灵动;然后再看其“气”之落脚处以及方向,至于温婉或磅礴则属诗人个体特征。
“气”是诗人外化的情感,“气”要动,动才是创造。诗人“气”动,才能让天地、鬼神动。当然,“气”与“动”要匹配得当,就是叙事与抒情的平衡,是词语在表达现场隐身而彰显趣味与意味。
外表的建筑无论多美,没有内在的诗人自己的感情贯穿,也是豆腐渣工程。
《春秋三传》中,我不喜欢《公羊传》。
《公羊传》看来看去,像几个人在写一篇命题作文,或者是开一个庸俗的作品研讨会。如果这几个人不是围绕着《左传》去说,我是一定看不完的。认真地说,《左传》并不客观,也不可能客观,像《史记》一样有着作者的主观色彩。如果把《左传》改成《左丘明中短篇小说集》,那么,《公羊传》就是几个在研讨会上看“红包”说话的评论家和编辑。
迎合、甜腻、穿凿附会、主观随意是《公羊传》的特点,尽管这老几个是举着天下大一统的大旗,但我觉得,旗下的阴影里藏着他们想要得到的功名利禄。
自己获利而遗祸后人,导致以讹传讹,罪莫大焉。好在这老几位评述的是《左传》。
呜呼,这部《公羊传》曾是汉代国立大学的教材。
若是其他一些几近垃圾的文字也有几位名嘴、名家口吐莲花地“微言大义”一番,当时明眼的人看了是踩着了狗屎,后来智慧的人看了就要不断地吃苍蝇、骂祖宗了。
名嘴,重要的是要管住嘴。我们曾经的教材里不少“名篇”,误导了几代人。
我很喜欢曾国藩的一句话:“未来不迎,当下不杂,既往不恋。”希望“名嘴”们也喜欢。
又有几个写诗的朋友练毛笔字,并寄来给我看,我真是欣喜过望。
用毛笔写字原本就是诗人的基本能力,就像吃饭要会使筷子一样。时代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过快,诗人仅会写诗,用毛笔写字的成了书法家。
古时,所谓“才子”,一定是诗人,而诗人必备的几样功夫是:刃、酒、琴、棋、诗、书、画。现在这七项,已经是七种职业了(也造就了这七种“产业工人”)。这七项,现在的诗人会几项?我觉得,未必都样样操作,但样样了解是应该的,了解、认识这些是借力,借力意在得巧,而非使用。
唉,我常讥讽好为人师的人,这不,我就好为人师啦。人的弱点之一,就是评判别人容易评判自己难。
文房四宝中,诗人最像笔,毛笔的特点是:尖、圆、齐、健。这四项内容矛盾着也协作着,有对立但不可分。笔之心,当有万般风云。
好的笔,腰的弹性要好,要健,只对纸墨鞠躬。腰挺住,笔锋就能立住。笔锋立,墨就实,气就贯。字好不好看,是后人去说的事。
这不是诗人吗?
时下,收藏界十分热闹,收藏家遍地都是,而且一个赛一个地牛。各种物品的拍卖纪录也不断被刷新,刺激得拍卖行业蜂拥而起,生意兴隆。我一向对收藏家心存敬畏。一个好的收藏家应该是个学者,其所藏之物,应该是历史变迁、世态变幻的见证;是人类文明进程、艺术发展脉络的记载。我们许多说不清的历史,弄不清的艺术流变,都是靠收藏家所藏之物,才得以厘清的。而近些年,有一部分“收藏家”,我着实有些看不懂。主要是对他们的身份存疑。
当然,部分投资者以收藏家的名誉招摇过市,似可理解。可就有那么一些自诩为收藏家的人,处处大谈收藏、炫耀自己如何收藏、收藏了多少稀奇珍宝的人,其实是钱多了,饱暖生闲事或附庸风雅。我就见过一个自称是大收藏家的人。我相信他一定收藏了许多东西,也绝不怀疑他根本不懂收藏。一个胸无点墨、无历史常识、无艺术感受力的人,会成为收藏家?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我和这位收藏家聊了一会儿,就恨不得扑过去揍他一顿,或者求求他饶了收藏家的名号吧!可他就是趾高气扬地认为:他是天下第一藏家。他收藏的东西是五门八类,只要有人撺掇他,这个、那个东西好,值钱,他就收。不问价钱高低地收。收了干嘛,他不懂也不问。我觉得,他就是把钱换成东西了。若真能遇珍拾之,集成稀宝,也是对历史负责,给后世留下福荫。可听他高谈阔论时,发现他收了许多假冒伪劣,这不是客观地刺激了造假售假者们的行业嘛。不懂就被骗,是正常的结局。换个角度,如果他不以收藏家身份和我聊天,而是一个文物和艺术品的保护者和我闲侃,我还真的要敬重他。
想起读过清代文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的一篇《废纸》的一段话:
萧山蔡荆山出示册页一本,其中所潢裱者,乃成化时某县呈状一纸,万历时某科题名录一纸,崇祯时某家房契一纸,隆庆时某年春牛图一纸,宣德时某典当票一纸,弘治时某姓借券一纸,天启时某地弓口图帐一纸,景泰时某岁黄历太岁方位图一纸。数百年废物,以类聚之,亦入赏鉴,可谓极文人之好事矣。
看看,这“数百年废物”,没有“一纸”是好出身,更没有名人名家的手笔,但蔡荆山先生喜不自胜地收了。乐其事,不为保值升值。据查,蔡荆山先生既不是官宦家庭,也不是富豪士绅,甚至都不是上层士大夫。当然也不是“官二代”、“富二代”。蔡先生就是一个书生,一个真正的儒雅之士。可以料想:蔡先生喜好收藏,可财力不足,便走了“人弃我取”的路线(估计也是在类似潘家园那样的旧货市场里用慧眼去淘)。这样既满足了个人的收藏爱好,也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佐证。
还有,收藏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事。若收了一件东西,就像买了某只股票一样,天天盼着它涨,那不是给自己找病嘛。收藏,是美学和社会学范畴。不能给你带来审美愉悦,你收之何益?当然,收藏也可以是投资范畴,但投资者不在儒雅之行列。所以,投资者就大大方方地谈钱,别把收藏家的高帽往自己的头上戴。一个投资商或投机商,硬把自己装扮成收藏家,就像活生生地把虎头豹额的张飞装扮成拜月的貂蝉,你喷饭不?你还不喷饭?我是恶心至极了。
(摘自《三余堂散记》,作家出版社2015年3月版,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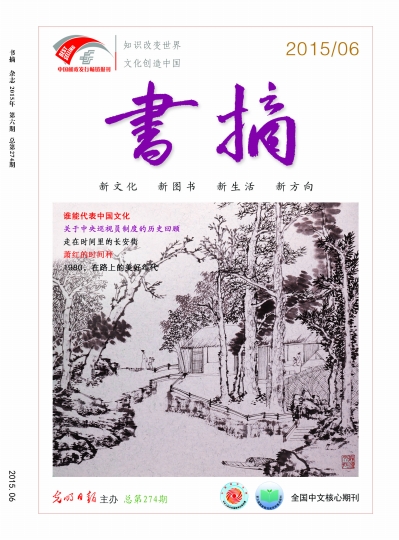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