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女士生于名门,外祖父是有“台湾太史公”之称的连横(号雅堂)先生,本文是她回忆外祖父与书的故事的一篇文字。
我的外祖父连雅堂先生在他五十岁之秋,曾与比他年轻的黄潘万、张维贤两位朋友,在台北市太平町三丁目二二七番地(今延平北路)合作开设“雅堂书局”。当时日本占据台湾已经三十余年,正积极推行日本语文,逐渐禁止中国语文,从而达到消除中国文化之目的。然而,“雅堂书局”所售的各类书籍,及兼营的杭扇、湖笔、徽墨、诗笺等物,却都是来自大陆的国货,一概不卖日文书籍及日制文具。古文书籍,以线装经史子集类居多,同时也出售与新思想、新文化、新文艺相关的书,如《三民主义》、《中山全书》,以及吴稚晖、胡适、鲁迅等人的著作。
“雅堂书局”开办之初,外祖父每日上午十时左右到店,略事巡察后,若无顾客,即取书埋首研读。店内的新旧书籍各种,他都兴味盎然地饱览,遇有疑虑,必查究字书类书。有时买书的青年人请益讨教,也会热心指导。中午回家午膳,下午二时许再到书局。晚间关店前,他总是选一本书带回家阅读,次日归还书店。
文人不擅长营商,而“雅堂书局”的风格又与当时大环境的走向相左,这个专售汉文书的书店,初时业绩还不差,除台籍人士光顾外,甚至还有任教于大学及高校的日本学者前往选购。其后则逐渐因为收入不敷开支,加上日人没收禁书超过资金四分之一,虽以少采办,多卖存货苦撑了两年,不得不结束收场。
外祖父撰著《台湾通史》,编纂《台湾诗乘》,《台湾诗荟》的心意,乃为台湾保存史料,维护祖国文化,甚至开办“雅堂书局”而专售汉文书籍,中国文具,也显然可见用心深刻。在书店开办的期间,他也曾主持汉学研究会,于晚间七时至九时授课。至于他个人的兴趣和最投入的研究对象,则逐渐转入台湾语言和文物考古方面,这成为他日后出版《台湾语典》及《雅言》的基本;而在那一段时间里能够拥有一爿书店,日日埋首书中,遇有大小疑难即可就便查考,定必为他最满足欣慰之事。
书店结束后,他在距店址不远的台北桥附近赁一楼房,廉售存书。其后,遂以余书委托台南的兴文斋、崇文斋、浩然堂等书店代售,而他也移居于台南故里。
台湾为日本人所占据,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外祖父始终不甘为殖民地民。他五十四岁之年,撰一书函与张溥泉先生,令他的独子震东先生携书投奔祖国。此函句句凄怆动人,有言:“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地,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怒?”
舅父震东先生在国内的工作安顿后,为了保存台湾的文献,外祖父仍在台南继续研究撰著。越二年,五十六岁之春,因为我的母亲夏甸女士(外祖父长女)婚后居住在上海,而姨母秋汉女士(外祖父三女)也已自淡水高等女校毕业,外祖父毅然决定携眷内渡,遂其终老祖国之志。
行前,日本台湾总督府委托尾崎秀真,向外祖父洽请将所藏的台湾文献割爱。通史既久已刊成,而此行恐暂无返期,外祖父便将书以半卖半送方式出让。他旧藏的书刊,一部分归台北帝国大学图书馆所有,另一部分归总督府图书馆所有。唯后者于二次大战期间,因遭盟机轰炸,竟无片纸幸存。
外祖父和外祖母晚年居住的寓所在上海江湾路公园坊八号,是我父亲林伯奏先生的房产之一。我的母亲就近照顾了双亲的晚年生活。
外祖父定居上海以后,仍以读书写作及持续关怀台湾文物为生活重心。他五十九岁之年六月二十八日,因肝癌逝世。身后遗留的许多文稿和书籍,由于舅父当时远在西安工作,所以部分由我的母亲承收保管。
抗战胜利之次年,我们举家自上海返归台湾。在众多琐物间,母亲竟然把外祖父遗留的书籍也安然带回来。而在繁忙的家务之间,我常见到有时她会抚摸那些已呈黄褐色的旧线装书。她必然是在怀念着她的父亲吧。
及至母亲自己也衰老时,她把外祖父的书送给了我。母亲过世后,外祖父遗留给她的书,遂成为母亲遗留给我的宝物了。我小心摩挲着书面虽然微损而内页仍完好的这些书,怀念着母亲,也怀念着外祖父。
外祖父逝世时,我尚未满三岁,仿佛记得一些事情,但其实许多事情也可能是听母亲的叙述,或者竟是日后阅读他的诗文,乃至于阅读他阅读过的书籍而想象亦未可知。
外祖父遗留的线装书之中,我最珍视的是一套四册的《庄子》。这套郭象(子玄)注,陆德明音义本,系民国二年扫叶山房石印,于民国三年三月出版。外祖父曾言:“台湾僻处海上,书坊极小,所售之书,不过四子书、千家诗,及二三旧式小说。即如屈子楚辞、龙门史记,为读书家不可少之故籍,而走遍全台,无处可买,又何沦七略所载四部所收也哉?然则欲购书者,须向上海或他处求之,而邮汇往来,诸多费事,人关之时,又须检阅,每多纷失;且不知书之美恶,版之精粗,而为坊贾所欺者不少。”(《台湾诗荟》第十八号“余墨”)四册线装书虽然年久而发黄,封面略有渍迹蠹痕,但内页十分完好。非仅原书的大小字都清晰可辨,外祖父在字旁所加朱笔圈点,乃至工整的眉批,亦皆历历犹新。
不知道圈点批写这些字时,外祖父是怎么样的境况?几案之上除了书籍笔砚外,尚有一只小茶壶为伴吗?他不嗜酒而好茶。那只常年使用的小小茶壶,后来,母亲也送给了我。他阅读的时候,可能把眼睛近贴着书。黄得时先生在《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四期有一段回忆他年少时的文章:“另有一次,我到开设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功学社对面)的雅堂书局去买书。当时,只有先生一个人在看守店里。但是他的近视眼却贴着手里的书,一心一意正在看得入神,完全没有感觉有人进来。等到我向他打招呼,他才吓了一跳,猛然抬头,脱去了眼镜说:‘哦,得时君,你来得正好,昨天商务印书馆寄来了英国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写得非常好,你看看吧!’他随即从书架上拿下那本书给我,立即又套上近视眼镜看他手里的书。”
黄先生回忆的文章,写得极为传神,把一位爱书提倡阅读的老人栩栩生动地呈现在我眼前。摩挲着手中微黄的书叶,指尖追踪那上面的朱笔圈点和眉批,仿佛可见清癯的深度近视眼的外祖父正认真地逐字逐句细读着这一本线装书《庄子》。
(摘自《写我的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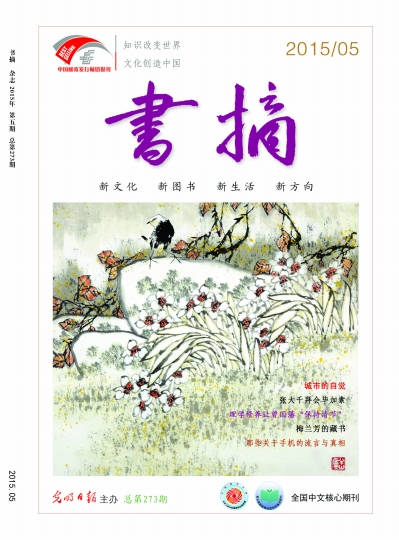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