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繁花》,是看轻时代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就算它重要,也是因为这几十年,我们活着,所以觉得特别重要。我们看历史书,翻一页就是五百年。人的一生,不是一棵树,是一片树叶,最后都会不知所终。
我们在上海作协的食堂吃面。方桌铺着猩红的餐布,穿白色制服的大师傅在柜台后捏着勺子,可以帮你再添一碗。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小洋楼建于1926年,是建筑师邬达克的作品,原本属于富商,1952年收归国有,后来成为上海作协的办公楼。阴雨和藤蔓植物弥漫着墙面,穿过门口的罗马立柱,中心楼梯盘旋而上,楼梯边是废弃堆叠的办公桌椅,浓重的社会主义“单位”气息。
我说我也以写字为生,金宇澄说,你一定要找出自己最擅长的地方,要多认识人,多发表东西,慢慢地,大家就知道你这个名字了。他逐一就每种文体,指出可能的方向、人际路线。至于小说嘛,他低头搅动着凉面,如在《繁花》中频繁出现的那个词,不响。他说,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小说编辑,我是知道的。
知道什么?1985年,三十三岁的金宇澄在《萌芽》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失去的河流》。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传奇年份,同龄人王安忆发表了《小鲍庄》,莫言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文坛上论争不休,“寻根文学”正热。1988年,金宇澄调到《上海文学》做编辑,他逐渐放弃了小说。1990年代,中国急速转向消费时代,一切东西都可卖,文学无法进入定价体系,被社会浪潮甩脱。金宇澄钟爱留恋的1980年代,像一场狂野的大火,被浇熄了,灰烬埋于地下。直到2011年5月10日,他在弄堂网上写下第一句:“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金宇澄把方言、文言和普通话,锻成新的节奏。小说人物絮絮叨叨,或是不响,玩许多小心思,都是不彻底的人物,上海这座城市的世相。二十多年过去,火灰酝酿,成为肥料,不意长出树来,树上繁花似锦,引来许多人观看,惊异相询,哪里来的这么一号人物?
小说这条路如此漫长艰难,荣誉到来时,又如此出其不意。
金宇澄高而瘦,棉布衬衫,短裤球鞋。很少见到谢顶的男人仍如此斯文清癯,边缘的头发散逸在肩上。声名来得太晚,他仍不能适应,一开始就说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有问题”,纷纷寻来的采访令他苦恼。他并不注视采访者,而是望向空无一人的前方,聆听和回答问题,语句缓慢悠长。办公室里,为了遮挡阳光,窗户上贴了许多印有“上海文学”字样的信笺。
在新的文学地层中,年轻写作者常常急于操持话语,弑去八十年代的前辈。在“文革”中成长的作家们,没有完备的知识结构,也难以接受时新理论,但是他们富于想象、譬喻,世界在他们的眼里是具体可见、充满细节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叙事的激情,总怀揣许多故事,琢磨一个不一样的形状,放在读者面前。这就是小说家。
《单读》:我有一个发现,在中国其他地方,咖啡馆里都是年轻人,或者是所谓的商务人士,但是在上海,咖啡馆里中年男女很多,有些还在里面谈恋爱。和《繁花》对照,我就想,在今天的中国,每个城市年轻人的生活不会差太多,不同的恐怕就是中年人、老年人的故事。上海毕竟城市的历史比较长,生活也比较复杂。
金:你这么一说,是有这样的地方,包括餐馆、老式蛋糕店,一般是老店。这些店中午生意特别好,因为年纪大的人晚上不愿意出来。老上海菜,松鼠鳜鱼那种,也有老概念西餐,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看报纸,很安静地小声说话的样子。也有六七十岁的男男女女,不知道身份的,穿戴整齐,背带西装裤,普通蓝布中山装,中午慢慢进来吃饭,看不清具体身份。这个大概就是一座城市的复杂性。
《单读》:上海的中老年人,不仅经历丰富,同时个人生活、人情上也比较复杂。比如《繁花》写到的中年男女,关系非常暧昧,这种人际关系恐怕是属于城市的。你还写道,上海女人有三宝,作、嗲、精,跟北方人特别不一样。
金:有个北方朋友看了《繁花》,说原来你们上海就是这个样子,灰蒙蒙的,曲里拐弯的,看不清的男男女女,它有许多灰色地带。城市越是密集,接触的人越是五味杂处,人的生活越是复杂。村子里头,做错一件事情,所有人都记得,你跑到城市里边来,就像一个海洋一样,人就消失了。
有一个上海女读者说《繁花》“很黄”,上海的陈村认为《繁花》一点“解渴的”都没有,肯定被编辑删节了,分歧在这里。我只是觉得,上海跟俗世脱不开关系,很多面貌,很多暧昧,很多的意思,可以说都有,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俗的魅力就是这样的。旧上海这一块内容更完整,到如今也生机勃勃。最丰富的总是灰色系的无穷变化,年代在变,更密集的人,更活跃的声音。也有某女读者有疑问,我们上海女人这样低俗吗?上海的高雅女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上海高雅”就像“上海旗袍”,已经重复无数遍,差不多是上海的代名词了,它们背后那些暗淡的弄堂街道呢,普通面孔呢,普通人的生活,不那么标准的三围,便宜的印花纹样等等呢?那是《繁花》感兴趣的地方。
《单读》:小说里写到很多市井故事,这么多的素材哪里来的?您有记录的习惯吗?
金:有意思的事,是不大会忘的。《繁花》开头引子那一节,一个通奸的人,整条弄堂闹得沸沸扬扬一塌糊涂,是二十几年前我听人讲的,就这么几个关键字。这还需要笔记吗?根本不需要。我就觉得太奇特了,非常生动,就记住了,而且特别符合中国人这种热热闹闹的样子。西方也是,很多小说取材于社会新闻,比如说《洛丽塔》,就是一个案子。
我吃晚饭的时候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老太太在家里死了半年多了,盖着被子,邻居都闻出味道了,电视台就冲到她家里去拍,公安局什么的都去了,太恐怖了,家里乱七八糟。电视台采访老先生,老先生说,我一点都没觉得有味道啊,我晚上睡不着觉,手一碰,我老太太在我边上,我就睡着了。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就是生活。有一个小说《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就是这个啊。生活就是每天在我们面前,这种东西看到了就不会忘记。
只不过《繁花》是集合在一块儿的声音,各人的故事习惯,散点的日常百姓的情况。西洋人自己吃自己一份,中国人叽叽喳喳一桌人吃,想想我们那些饭局,听那些碎片,基本是这样,每人都一直在说有意思、没意思的。中国式消闲,是素材聚会,天南海北,都这样讲和传来传去。
《单读》:您曾经谈到上海被误解,这是什么意思呢?
金:奈保尔最近来上海书展,主持人一直在问他对上海印象如何,他说我还没有看,还没有出去过啊。他出去了会是什么印象,我想起他的“印度三部曲”,整体对印度没有什么定论,局部倒是非常清晰到位。上海也这样吧,是模糊的,看不清楚,是容易误解的上海,但它的局部可以看清楚。
上海一直在急剧地形成中,开埠时代、太平天国时代、日本人打上海时代,都有那么多人跑进来,人人差不多都希望往这里跑,往租界跑,那里安全、自由,有商机,适合生活。那么多作家都喜欢租界,住上海亭子间,引人注目,也引人议论,这是没法的事。殖民主义引来大量的人,大地主、大知识分子跑到上海躲各种事,做各种事。鸳鸯蝴蝶派文人包天笑是苏州人,他回忆说在学生时代,苏州的长辈们都一致讲,上海是个“坏地方”,轻易不能去。可是苏州最有能力的人,最后都住到上海来。以后新中国成立了,户口三十年不流动,一开放,还是大量人口跑进来,富人、知识人都愿意来这个“坏地方”发展。这个聚焦说起来历史很短,就好像说美国年轻,实际欧洲最能干的人、最有想法的人,欧洲村子里最开通聪明的人,都跑去美国。传统欧洲也一样认为美国是“坏地方”,但也知道这种“坏”很有价值。这就是我说的误解。
其实对上海人的评价,经常是知识分子对上海小市民的评价。你做研究,就该以上海小市民和某地小市民做比较才合理,是不是?小市民其实都差不多的,就像各地知识分子也很相似。
《单读》:这种误解,大概也和上海比较早接受了西方的影响有关。人们面对上海,也许有面对西方的复杂情绪。
金:是不土不洋的风景,种种碰撞集中在上海。我写了这个小说,越来越觉得上海陌生,好像一座原始森林,个人怎么可以了解它。我只看了附近一小块地方、身旁的植被、一小队蚂蚁,很难想象我可以做个总结,可以全部了解它。最普通的上海旧马路、旧弄堂,只不过百年,我眼里却像是有千年的老态,存了更多的房客和气味那样。即便是名人宅邸,也是秘不示人,或者就是拆没了的那种。就比如上海书展这块地皮,过去是人人知道的哈同花园,从伊拉克来上海的英国人哈同造的,他迷中文,迷中国人这一套,园中收了几个故宫的太监,建学校,进来出去的都是风云人物:隆裕皇太后、王国维、孙中山、徐悲鸿……包括一箭之遥的民厚里,住了戴望舒、郁达夫、毛泽东、郭沫若,这一带是上海的焦点。后来男女主人过世,日军进园子拆,哈同的养子养女大打继承权官司,都是当年的新闻头条,再后来一把大火,成为废园,最后造了这苏联式建筑,我小学时代是“中苏友好大厦”。现在一个牌子都没有,历史结束了。
我在写作、修订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轻易给出判断。环境大变了,如今的读者应该比作家聪明,和我的年轻时代完全不同。1980年代最用功的学生,一定考中文系,念文学。这二十年来文字最优秀的学生,一般读金融或其他。不吃文学饭,但最懂文学,有最好的鉴赏,都在暗处看你这个文学。如果到现在还真以为作家无所不知,还是庙堂的高度,是很可笑的。普通的作家也就是讲讲人,讲他所知道的人和事,与读者应该平等,把自己知道的那点告诉他们,就行了。博尔赫斯喜欢《一千零一夜》,慢慢讲话,讲他所知道的事,提供给读者消遣与感动,也就够了,醒世教化,大家都懂的。《繁花》等于开门请人来坐,不是豪宅,只是普通人家、芸芸众生,让你看看跟北京胡同有什么不一样,就这么简单。
小说还是要回到你最熟悉的生活。即使你是知识分子,你也还是生活在市民中,你的亲戚朋友、三姑六婆都是小市民,这是分不开的。也有人说,这本书写了上海的小市民,现在上海还缺一本写知识分子的书。但是我觉得,我们只有建立了中产阶级的国家,才会产生知识分子的作品。现在我们的生活就是三姑六婆。像钱锺书先生写了几个知识分子的《围城》,看完后掩卷一想,还是市民生活啊,是市民的狡黠、市民的刻薄,还是市民味道。这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没有改变。
《单读》:这里也涉及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市民生活大家好像更喜欢看,这种题材也富有行动、情节,但是现代小说强调个人写作和阅读,很多作家声称不在意读者,《繁花》因为是在网上写作,直面读者的反应,这是很特别的。
金:是的,假如独自写作,不会做到每天均匀地写一大段。每一大段都用突然结束的办法,是网络的作用,是为了吸引读者才这样的,每一段“且听下回分解”,是留有悬念的,与一般的长篇小说不同。我以前也写过四五万字的中篇,只面对自己,一路推进,没有每一节为读者考虑。最主要的是对自己的怀疑,怀疑我这样写是不是可以。就像画画,画了几笔,退后去看。但是这种心理在网上写的时候完全不需要了,下面有人议论啊,你只要看他们议论就够了。有时候我写了一段非常静态的,底下的回应就很沉闷,没有几个人,我就会警惕:这段是不是太闷了。这个网站里面都是看小说的,五十岁上下的小学中学老师特别多,人也客气,不会骂你。他们应该代表了基层的文学读者。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方式。哪怕你闷在家里写,最后也一样是给读者看,我不过提早让小说进入被阅读的过程。
写作心态上是逐渐地升温,蛮好玩的,写了一段,突然就有读者了。等于你就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你会相当谨慎,特别敏感、兴奋,也特别周到,复杂的氛围、责任感,就像一列火车慢慢开动那样,最后找到一个速度,同时考虑每个站怎么样,速度带着你跑,慢慢占据所有的时间,也不觉得累,醒来就是坐在电脑前,只要清醒的时候,速度和时间就带着你往前。
小说一旦产生,就一直注意它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好状态,以后写长的东西一定要这样来。就好像说本来一个人喝闷酒,找一帮人喝酒不是很好吗?写作我也不把它看得特别高,我们曾经看高了多少小说,实际也不过如此,它要经历时间的考验。
《单读》:所以说如果没有网络,您就不会再写了?
金:肯定不写了。网上闲聊是个意外,最后触动了我,觉得不对了,是一个小说了,因此有一些东西被唤醒了。包括修改二十遍,都是过去的习惯醒了。
《繁花》是一个奇怪的经验,我跟王家卫对谈时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个老太太突然怀孕的经验,不足为训。只能说上帝对我很好,很顺利,我的努力超常实现了。
也因为这本书,我非常惊讶媒体的力量。这种快速的反应、相互之间的影响、连续性的报道,八九十年代是没有的,我很害怕,也很不习惯。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一直说文学被边缘化,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有那么多读者喜欢看小说的。我非常看好目前文学与网络时代犬牙交错的状态,我相信会有更好的作家出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前一阵讨论的网络写作,遇到过一些网络写手。我知道网络写手是不被娇惯的群落,香港书展的宣传文字里已经认为,网络作家是将来香港写作的希望。所以说,每个时代的表现都不一样。我和《繁花》,是看轻时代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就算它重要,也是因为这几十年我们活着,所以觉得特别重要。我在《繁花》里面写到,人的一生不是一棵树,是一片树叶,最后都会不知所终。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这一代怎么样。我们看历史书,翻一页就是五百年,所以说,《繁花》里面到最后有一些虚无的东西,我觉得是对的,我们的传统就是虚无。虚无不是说让你怎么潦倒,它是正能量,正是因为这种虚无,所以要珍惜当下,很好地表现生活。包括人生的终点,文学不大表现,我们小说都表现得很有信心。
(摘自《单读08漫游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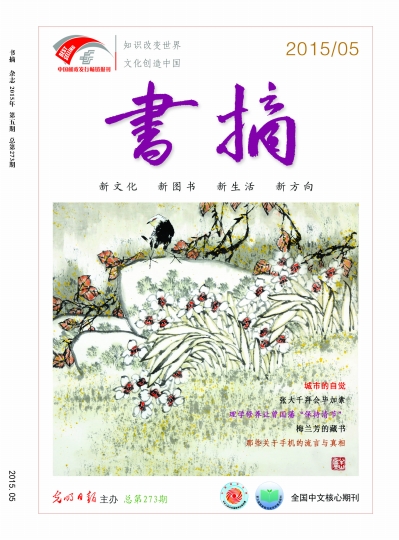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