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0年和1991年参加了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全过程,有幸听过先后主持这项工作的胡乔木、胡绳两位同志许多次讲话。
说“有幸”,不是例行的套话,而是由衷之言,因为这种机会并不容易得到。胡乔木和胡绳是党的历史中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又长期领导党史研究工作,有着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在随便谈话中也往往能对党史说出一些常人没有想到的重要看法,可以启发人们去思考。
他们讲话时,大多只有四五个人在场,并不是准备发表的,所以说话比较随便,只要听的人明白就行了,甚至有说半句的。有些话对不了解当时语境的人来说不容易看明白。将来成为废纸也实在可惜,一直想把它整理出来,对后人还有点用。
当然,要整理也有顾忌:他们两位都不在了,我不敢肯定整理的记录是否百分之百都符合他们的原意。有些是他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未必都是考虑成熟的意见,把它发表出来好不好?但想来想去只要说明这只是记录稿,不是他们字斟句酌后写定的文章,整理出来总比变成废纸好。
写《七十年》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是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来的。这个领导小组成立于1985年3月,由杨尚昆任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任副组长(以后又增加了邓力群和胡绳两个副组长),但没有组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它的办事机构。
那时党史著作往往只写到1949年,少数写到1956年,只有个别的写到改革开放。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早就有意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还考虑写一部篇幅不太大、便于更多人阅读的党史简本。
正式提出编写《七十年》这本书,是在1990年3月8日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
当时还有一个背景:中国刚经历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国际上先后出现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上思想比较混乱。这就把加强党史研究、宣传和教育的任务更加突出地提到人们面前。正确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圳,进行具体分析,分清是非,对人们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回答。
胡乔木:“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
3月8日的会议以后,胡乔木立刻要党史研究室先草拟出一个比较简明的党史编写大纲来。4月20日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送给他。他看完后,谈了一段比较长的话。
胡乔木:写这本书,事情比较大,最好请力群、胡绳同志一起开个会。不是抄老本子就可以做到,要提出一些见解。没有见解,这本书人家就不要看了。写出来要使人读得下去。
实际上在八大以后,党内是有两个指导方针。(注:从他前后多次讲话来看,他不是指领导集体内有两批人,各有一个方针。而是指领导集体内、甚至同一个人头脑里存在着两个思路、两种趋向,起伏不定。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一会儿正确,一会儿错误。胡绳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到“文革”时错误的思想占了上风,就出了大漏子。)当然话怎么说,要考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小平同志讲,1957年以前毛主席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20年犯了“左”的错误。一方面有“左”倾,一方面又有抵制“左”倾。“文革”前有一个时期,发生严重困难,毛主席认识到有错误。八字方针(注: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执行了一段,经济有恢复;另外一面,七千人大会以后的十中全会又强调阶级斗争。虽然说不要妨碍经济工作,但慢慢地还是没有法子。到1966年初就搞不下去了。
当天下午,胡乔木向胡绳说:看了提纲,觉得要写好这本书很不容易。要使人看了后觉得是内行人说的,是懂得情况的人说的。
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胡乔木又找了几个人去(我也去了),比较系统地谈了他的意见。
胡乔木:从提纲的题目看,感觉思路不清楚,条理不清楚。
思路不清楚,比如“合作化高潮”不宜都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一波同志的书里说了,是人为的高潮。1955年下半年,从组织原则上讲就不合适。三次会议,第一次决定放慢,第二次会议就批判了。(注:指批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右倾)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情况怎么能几个月就忽然变了?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这是举例来说。
1957年以前,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已经表现出来了。讲集体领导,很难说。比如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没有任何调查、讨论,就定他是反革命。毛主席写按语,把胡风所说三年后文艺界的状况可以改变,说成胡风是在讲三年后蒋介石会反攻大陆。这件事的过程,我没有参与。周扬原来送去的按语,毛主席重写了。要周扬研究,交中央讨论。我提出过这个问题,说这类问题究竟怎样论述?还有潘汉年的问题也没有讨论,说是内奸。发展到1955年,形成了影响全党、全国人民。合作化本来决定要放慢,一下变成要加快。这么大的变化,是影响几万万人的大事。
这个提纲中,“文革”中间的“斗、批、改”运动呀,“批林批孔”运动呀,不能这样写。是有这么回事,但是不能照用这个提法。
林彪事件发生了,本来应该批极左,批林扯上了批孔,就莫名其妙。林彪和孔子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是滑稽的,把林彪和孔子并列是荒谬的。这时毛主席批孔是怎么扯出来的?还是江青他们利用他从前的几句话?本来林彪叛逃事件可以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次转机,像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以前本来也是一个转机。但毛主席不肯放弃他原来的想法。林彪事件的发生说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问题,彻底暴露了“文革”毫无意义。毛主席已经感到这个党经过“文化大革命”,党“分裂”了,“阴谋诡计”盛行了,所谓反修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毛主席没有那么糊涂,还是要依靠老干部、国务院、邓小平,但他仍陷于不可解脱的矛盾中。既然要用邓小平,就是承认“文革”这一套不行了。可是,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到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
当然,毛主席仍有他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虽然有“文革”,党没有垮,因为有毛主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毛主席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但是遇到最根本的问题,他还是明白的。
对于过去的一些说法,不能全盘接受。那样,写不出党的历史。另外,“八字方针”作为通俗用语是可以的,在正式的著作中最好少用这种很难懂的话。
八大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后来背离它,犯了错误,要纠正,又犯错误,错误更大。然后试图回到八大来,当然历史已经变化了。总是这么个趋势,在党内还是很强有力的。两种趋势,结果“左”的倾向还是要起来。这根本上可以说是历史的、盲目的惯性,还是要靠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对党的历史的脉络,胡绳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好。这些错误,一方面是要搞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有个不断加深的过程。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事实上,社会主义要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个认识过程是很困难的。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这样想过,斯大林还是这样。赫鲁晓夫尽管批了斯大林,还是说是要很快搞成共产主义。毛主席也说中国可能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思想然后发展到越穷越革命。社会主义不能这样干,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社会主义是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认识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是很不容易的。改革开放十年来,这一点肯定下来了。
1990年8月27日,胡乔木又找几个人谈了一次,胡绳、邓力群也参加了。
这次已经写出一部分初稿,他比较系统地谈了应该怎样来写一部简明中共党史。
我当时的印象,胡乔木本来是准备由他自己来主持编写这部书的。多次有关会议和谈话都由他主持;编写提纲的初稿先是送给他看,他再嘱咐也送给邓力群、胡绳看。我的记录中,胡绳第一次召集我们谈这件事,是这年11月9日,并且一开始就说:写这本书,我有点力不从心。看来,那时才刚刚明确要他担任《七十年》的主编。
后来看到胡绳写的《胡乔木和党史工作》中有一句话:“胡乔木同志由于健康状况,他不可能按预定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胡乔木是在这年9月确诊患有前列腺癌的。
胡绳:不好说共产党内有几个派系
大纲初步拟出后,就分别执笔撰写初稿。初稿的撰写,实际上由执笔者自己作主,并没有受原大纲多少约束。
9月间,胡乔木的癌症病况已经确诊。胡绳接手这项工作。
胡绳12月6日的日记写道:“(王)忍之处来电同意龚育之参加党史工作,即告沙(健孙)、郑(惠)。”沙健孙、郑惠那时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我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忍之是中央宣传部部长,龚育之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在《送别归来琐忆》中回忆道:“是因为我参加过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要我帮助他修改这部党史建国以后的部分。”“后来决定由我负责建国后17年那两章。”
1991年1月,《七十年》的初稿都已写出,准备参加修改的人员大体也已确定,决定集中到玉泉山工作,预计在半年内完成。
到6月下旬,时间已很紧张,改革开放这部分修改的工作量还很大,这时又增加了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胡绳6月24日日记:“到玉泉山,谈定7月7日为最后完成期,王梦奎已到。”这次修改的幅度非常大,许多部分接近重写。执笔修改的分工如下:第一、三、四、五章,金冲及;第二章,沙健孙;第六、七章,龚育之;第八章,郑惠;第九章,胡绳(第一、二、七节)、沙健孙(第三节及第六节前半)、王梦奎(第四、五节及第六节后半);结束语,胡绳。全稿由胡绳统改定稿。
在改稿过程中,胡绳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他不仅反复阅读各章的初稿和改稿,随时动手进行修改,并且举行了十多次讨论会,主要是由他讲话。谈他认为应该怎样修改的意见,然后由负责该章的人进行修改;第二或第三次是他看了改稿后再次谈还需要做哪些修改,再次修改,最后由他自己动手,修改定稿。胡绳后来带着秘书黎钢也在山上住下来。
胡绳1月22日日记:“到玉泉山,讨论第七章(1956-1966)用了几乎整一天,五时回。”
胡绳: 庐山会议开始时,虽然提出了一些反“左”的措施,但领导思想没有真正转过来。有人说:如果彭德怀不干扰会如何如何。事实不是如此。实际上已经有“左”的思想在抬头,恰好你碰上来,就有了一个标兵。
“大跃进”错误地搬用民主革命时的经验,认为淮海战役这样大的战役是靠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人多就好办事。
毛主席讲一穷二白的“白”本来是指文化落后,后来成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改换了概念。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毛主席一个人,这在当时是党内的潮流。这叫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
胡绳1月26日日记:“看文化大革命稿(这是党史研究室同志写的第二稿)。”28日日记:“下午到玉泉山,讨论第八章……”
胡绳:“文化大革命”这是个难题,怎么写?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它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上的错误领导造成的。这个错误不能说没有历史原因,不能说只是毛主席发了昏,大家阴差阳错,搞成这样。又经过了那么多年,又有了苏联、东欧的教训,应该更深入一点地来讲。
毛主席想要搞社会主义,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看,毛主席有些观念是不是也还有些本来正确的东西却推演出错误的东西来。毛主席经过了那么多的胜利,骄傲了。伟大的胜利是跟个人领导分不开的,这是一方面。但他又老是担心政权靠不住,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他提出这个问题有点远见。他不是认为创立的事业已经那么稳固了,没有一点问题了。也许他这个想法是从抽象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没有跟实际结合得很好。
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张白纸上建立,必须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一切东西是又继承又批判地改造,不是简单的“破四旧”。他看出跟资产阶级还有斗争,后来又看到它的复杂情况,但还是老的公式: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错误在哪儿?这要分析。只讲现象说不清楚。
为什么毛主席要反对刘少奇?毛主席怕刘少奇推翻他?没有这个可能。刘少奇一向跟毛主席很好地合作,有错也检讨,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为什么非要把刘少奇搞下来?这个问题不说明的话,人家就会觉得无非是共产党里面争权夺利。
比这更难的,为什么会出现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这个绝不是简单的几个人的事,有一批人跟着他。
说是无产阶级里面的几个派,也不好吧。定性还是野心家,个人主义。我跟少奇同志聊起来讲到过,中国这个环境下,我们参加革命,最初是个人找出路。慢慢地发现个人不行,还是要依靠党,依靠阶级,觉悟提高了。但总有些人没有真正改造好,成了共产党人还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目的。这部分人很多实际上是游离分子、流氓无产者。鲁迅讲是流氓。土改开始时起来的常有不少人是勇敢分子、流氓,有些破坏性,也没有原则性。农村出来的有些领导人,甚至到了军、师一级的,政治觉悟低,文化也很低,跟着跑,一下子就把落后性都表现出来了。
过去长期都是大搞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是成功的经验。不但毛主席如此,大部分干部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他这么大的权,又那么自信,放出来了,他认为我能够收。他以为天下大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以为我控制得了。在社会主义之下,搞天下大乱这个局面,根本不行。
如果1967年毛主席死了,历史会有不同,但就会改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也不可能。如果毛主席死了,周总理健康,也会不同。他不用抓“四人帮”,他有威信,但可能转得慢一些。“文革”十年很坏,但是走到极端,就物极必反。
对《七十年》各章已大体讨论一遍。
2月15日是春节。胡绳在这天日记中写道:“既然放假,懒得做事,只看了几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月4日,胡绳日记中写道:“到玉泉山,与山上四人‘谈虚’(非谈具体某章),主要谈了对中间十年的看法。”这次谈话,是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起的。
胡绳:我把剑桥这本书大体上看了。费正清所讲的探索中国道路中,有些问题。他是从争夺权力的角度出发来讲的。
派系问题。费正清是从延安领导人的分裂讲起的,认为党内有不同派系。我的观察,很难说那时刘、邓是一套,林彪、康生是另一套,实在看不出来。当时领导干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比较务实的,一种是有着浪漫主义的情绪。1958年大发作了一下。好多人有时候这样看,有时候又那样看。陶铸在“大跃进”的时候也讲过吃饭不要钱,他在农村搞公共食堂也很起劲。包产到户的试点也在广东搞过。少奇同志到南方去,我跟着他去。少奇同志说,不要种那么多地,种一半地就可以了。路上他只提了一个要注意劳逸结合的问题。一贯比较务实的是陈云同志。有些同志随风倒,也不能完全说是品质问题,对新问题一时没有一定的主见,这个也可以试试,那个也可以试试,都说是投机也不一定。一定说江青、陈伯达在1961、1962年的时候就结合在一起,我也看不出来。(注:胡绳的意思是,那个时候,对社会主义怎么搞缺乏经验,谁都不很清楚。又想摆脱苏联的那一套,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有时候这样讲,有时候又那样讲,说这个是投机,是派系,其实都难说。胡绳当时的直接观察,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有浪漫的一面,也有务实的一面。少奇同志一进城,我就听他讲反“左”(注:指刘少奇从天津回来)。但反右的时候,他也很厉害。彭德怀和毛主席之间可能有一些历史疙瘩。毛主席那样信任林彪,我不大懂。罗瑞卿就是因为林彪告了一状,大家就异口同声批罗,也不知道林彪讲的是真是假。当时要彭真同志写个报告,彭真就托我找吴冷西,问罗瑞卿到底是资产阶级还是地主阶级?领导同志有个人的想法,有历史的疙瘩,这种倾向是有的,但是讲派系也很难说。可能也反映了进入社会主义的那种复杂情况,找不到一个统一的认识。只有毛老人家有威信,他说反“左”就反“左”,他说反右就反右。
陈云同志的确比较一贯,很多人不大一样。七千人大会后,少奇、陈云、总理在一起。少奇让陈云在各部委的党组会上讲话,得到热烈鼓掌。但他也没有完整地、全局地提出一整套的东西,听得进就说,听不进就不说,七千人大会上他就不讲话。
我们党也奇怪,当时问题那么严重,但到1962年以后又好了。外国人很难懂。
这十年确实是在探索,整个党在探索,个人也在探索,有这样的,有那样的。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十年最后就一定发展到“文革”?它不仅仅是为“文革”做了准备,探索中间也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准备的成分。
“文革”后小平同志一出来就提出这些问题。他是在总结经验,总结更多的是前十年的经验。这十年的探索中,有务实的倾向,也有浪漫的倾向。最后浪漫倾向占了上风,甚至把不倾向浪漫的打倒,这是一个大悲剧。
胡绳日记,7月25日:“在玉泉山最后一日,上午看了郑惠的第八章第五节,至此全部定稿。午睡后与诸人同拍照。三时进城。”
(摘自《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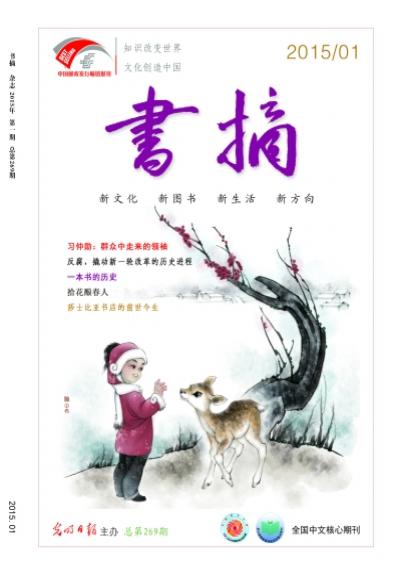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