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历了中国近代最反复的政权更迭——从没落的清王朝开始,到共产党政权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中国的一切,早已融入他的灵魂,而独特的视角与位置,也让这个美洲人,看到并了解到关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许多个另一面。他是1949年之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1919年春,我来到北京。那时全中国上下互相倾轧、矛盾重重。对我来说,在这个各方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的时代里,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拜访不同阵营,了解敌对各方的情况。于是,我开始主动拜访中国的官员,为的是让他们了解基督教大学的宗旨,为了以示他们对于基督教教育的友好,我们有时也会向他们筹集资金。
颜惠庆、陈树藩
颜惠庆博士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他是中国政坛上的显赫人物,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中国驻其他国家公使和北京政府首脑。他是个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人,并且拥有超凡的政治才能,他供职于燕京大学理事会多年,并且还曾几次出任主席。第一次和他会面时,我试图说服他帮我为修建男生宿舍筹集资金。1926年,大学迁往新址,那年北伐战争爆发了。在颜惠庆博士的许可下,傅泾波进行规划,用我们筹集来的钱对学校围墙进行了修葺,这样做是为了将校园包围住,免得受到社会动荡的牵连。
陕西省的督军陈树藩是另一位我早年结识的高官,他和颜博士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将土地卖给燕京大学做校址,并且将其中三分之一的付款归还给燕大,他提出要在校园里留出一块地方给他年迈的父亲做别墅,这座别墅后来被改造成为一座纪念堂。他曾提议我可以去西安看看,并在教育方面为临时政府提出一些建议。我答应了,并在1921年的早春带着会谈的结果启程了。陪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位仆人。最开始,我们沿北京——汉口线走,在一条新线路的交叉口我们下了车。这条东连大海西通西安的线路还在修建之中,我们向西飞速驶去。下了火车,我们又走了一个星期,中途需要穿越过一个区域,那个地区土匪肆虐。督军为了安全起见,特意派了一班士兵来护送我们,一台驴轿由两头驴身上绑着柱子,撑着一架有顶棚的小屋。里头铺好了床褥,地方足够一两个人躺的,也还算舒适。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得到了督军额外送来的一匹马,佣人喜欢躺在轿子里,而我喜欢骑马,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种旅行方式让我亲眼看到了未受到现代和西方文明侵蚀的土地上的朴实农家风情,这对我来说十分宝贵。
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都在督军那里做客,在这段时间里我逛遍了古都西安周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并且出席了很多社交活动。陕西的达官显贵为我举办了多次盛宴。有一回,在督军和省长联合主持的宴会中,两人坐在了一起。宴会为他们各自特别准备了食物,以防止对方下毒。他们两人身后都跟着保镖护卫,而且这些保镖护卫都隐藏在不显眼的地方。有个护卫的枪忽然在宴会中掉在了地上,顿时,全场一片惊慌。而在发现是一场虚惊后,大家又装得像是莫逆之交一样,稳稳坐好继续进行着亲切的聊天。
西安的风光令我陶醉,我甚至想将教育计划实施在这片土地上,让督军的中学与燕大有一种特别联系。督军在我离开陕西时送给了我一匹马,这匹马跟着我回了家。刚入北京,就听说省长成功发动了对督军的起义。陈树藩回到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而后的岁月里,我常常去拜访他。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中国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你有多足智多谋,最终都是竹篮子打水。这些事情经历过后,我就知道与当权者打交道的重要性了。
乱世军阀
山西都督阎锡山是另一个在那个混乱时代中的显赫人物。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和伯顿教育委员会一同旅行中。而后,我又对他进行了几次拜访。从总体上看,他在能力和人格方面给我留下了比较正面的印象。最初,阎锡山的梦想是做一个“模范都督”,但是这个梦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改革并不是人们所想要的,而且又接连有外国人和中国人欺骗他。尽管山西在实际中成了“国中国”,但事实上,他的本意是让山西处于民国治下。他被迫逃到日本是因为反对蒋介石,日本人设法拉拢他,尽管并没有成功。他忠心耿耿地为国民党打江山那是以后的事情了。1936年,他邀请我去山西帮他搭关系,那时他想要在省内大力发展工业。虽然一些计划在当时制订下来了,可日本人很快打了过来。
孙传芳是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的总司令,他和浙江督军打了一场江浙战争,随后他在蒋介石1927年发动的北伐中被击溃。他曾经在一次与我的会面中问:“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中国教育中国人?”
我的回答是:“文明无国界,文明属于国际。如果想要对彼此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认识,就应该将全世界的文明汇聚在一起。携手中国传统文化一起努力开拓出新的文化是我们的目标。”
“谢谢好意,那你来见我的目的是?”
“筹集资金。”
“和您改天再谈。”孙司令站起来后,露出了一脸不感兴趣的表情。不过他后来还是给燕大捐助了100美元,之后又给了2万大洋。燕京大学里后来出现了孙司令一个儿子的身影,他学习非常努力。日本侵华后,他因要从事“爱国壮举”而离开燕大。司令本人在解甲归田后在佛堂被刺杀,他是被一个欲报夫仇的女子暗杀的。
另一个独立的地方高官是韩复榘,他能够在国民政府之下保留自己的势力。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进步的统治者,比如他清剿了全山东的土匪。不过他这个人十分独裁。日本人几次三番地想要拉拢他,他本人虽然也想站在一个坚定的立场上,但又担心蒋介石不支持他。
1935年,我去见蒋委员长,韩主席拜托傅泾波和我同去,以确定他的态度。一上来,蒋介石就勃然大怒:“国策这种事,这些地方官员无权过问。国家大事自然有人处理,你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向他辩解:“理是这个理,可数百年来中国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中国文化中,最高尚的品德是忠心。想让他成为你真正的朋友,就需要和他搞好关系。”
蒋介石被我这番话气得够呛,最后他冷静下来说:“好吧,你跟他说,他只要坚守阵地,我就会不离不弃。”
回到济南,我们建议韩复榘去拜访蒋介石。后来,他去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谈话,并取得了其谅解。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关系,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人到了山东。1937年,日军发动进攻,韩复榘没有守住立场,他犹豫不决,最后带领军队向西撤退。他被蒋委员长派去的人逮捕,最后在军事审判后被枪毙。
和韩复榘经历相似的是宋哲元,但不同的是,他直到去世之前都在对入侵的日军进行抵抗。当时,河北省由他负责管理,他曾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无法抉择。我曾对蒋委员长劝谏,如果宋哲元能够得到政府的适当支持,那么他一定会忠心耿耿,誓死抵抗入侵的日军。卢沟桥事变之后,他被蒋介石督促去省会保定抗战。但是,他却在一次日军的奇袭后悄悄溜走了。等他后悔开始积极抵抗占领北方的日军时,已经晚了。
冯玉祥
冯玉祥是在中国叱咤风云20年的人物,他有时会被人称为“基督将军”。他是个体态庞大、脸颊很宽的人,他性格豪爽、强势、直率,可惜却喜怒无常。他曾经皈依基督教,那是因为感情上的问题,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问题,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克伦威尔和早期的冯玉祥很像,他们的军队都纪律严明、组织严密。有一段时间,他的军队里甚至还有随军牧师。但当他被张作霖打败以后,这些牧师就不见了。
我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当时,他对蒋介石颇有微词。他到达南京后,官居一职,可因为不满又离开了。后来,他去了泰山隐居。傅泾波和我曾经去拜访过他一次,当时,他正在读一本古籍,并练习毛笔字,他的书法十分有名。“如果他们不再互相倾轧,我就回南京去。”他语气狠狠地对我说:“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他们愿意抵抗日本人,给我最高官位我能做,给我最卑微的差事我也认了。”
有一回,我肩周炎发作了,正巧去拜访他。他知道我的问题后,立即拿出了一种膏药。这膏药是北京一家有名的药店出品,成分以熊脂和虎骨粉为主,冯玉祥司令一直将这种膏药随身携带。他坚持亲自为我上药,我将左肩的衣服脱下,他在我肩膀的前后方各贴了一块,这期间,他的助手还照了张相。最后,也不知道是药膏的作用,还是美国传教士大夫的治疗,又或者是逃离了南京潮湿的气候,总之,当我抵达北京后,疼痛就完全消失了。而后在一次重庆的招待会上,这件事被冯司令当作笑话一样地讲了出来,下面的宾客被逗得哄堂大笑。
最后一次见到冯玉祥时,是在重庆。当时,他正在读乔治·华盛顿传记的中文译本。谈起美国的革命,他颇有兴致地讲到卖国求荣的叛徒,饥寒交迫的民众和溃不成军的部队,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中国人还没受过这样的罪,所以,一定能够熬过难关。”
(摘自《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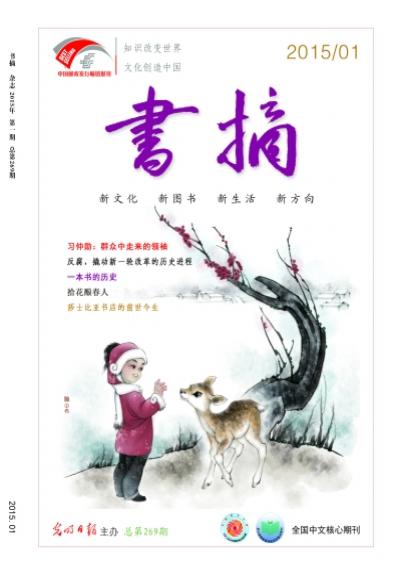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