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叶行一回老家湖州,回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一瓶臭苋菜。菜装在一个像农药瓶的家伙里面,只差在瓶上画一只白骨人头,下面交搭两根白骨。我解开塑料袋,里面散发出一股能臭死人的味道。我问叶行一:“你是坐火车回来的吗?”他说:“是的。”我说:“这东西如果你在火车上解开,估计有一多半人要跳火车。比日本麻原彰晃放的沙林毒气还厉害!”我拧开盖子闻了闻,臭得有点杀眼睛。我说这东西比我们这边的臭芥菜厉害多了!这浙江人历史上得遭了多大罪,才研究出这么臭的一种食物。
周二先生曾经写过这个臭苋菜,说佐粥很相宜。臭苋菜真正能吃的是它的茎秆的中间组织,像吸果冻一样。一大碗粥里面几根臭苋菜就够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很多地方的人喜欢吃臭的东西,但基本上以植物臭为主。皖南有一种臭鳜鱼很有名,是把鳜鱼放在木桶里让它轻微变质。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住在富春江边的渔夫,打到鳜鱼之后先要用盐“码”一下。然后挑了到附近的山里去卖,鱼因为处理过了,可以卖好几天。虽然有点味道,但是下重油,下红辣椒和大量蒜、姜,味道也相当好,产生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异香。我曾经看过一本研究香料的书,书上说香和臭也就是毫厘之间。很多臭味在稀释很多倍之后,产生的就是香味。后来有好事的人就把活蹦乱跳的鱼放臭了再吃。这个鱼具体要变质到什么程度是有讲究的,现在有的饭店控制不好这个度,索性在里面放一勺臭芥菜汁冒充。一般外地客吃吃,“哦!臭鳜鱼就是这种味道。”植物的臭和动物鱼类的臭是不一样的臭法,动物的臭弄不好有一股死尸般的恶臭。
马克·吐温写过一篇小说,是说两个人押车。说好是押一车步枪和一具朋友的尸体。路上越来越臭,这两个人只好轮流把鼻子伸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车厢外又是大风大雪。后来这股臭味越来越大,两个人简直没有办法忍受,只好把身体半吊在狂风大作的车厢外。其中一个可怜的人受凉得了病,也是要死不活的样子。他们默默坐在那里想,这个木箱里的朋友大概是浑身流黄汤了。后来的情节我不大想得起来了,可能是其中一个人发了狂,用撬棍撬开了木头箱子,准备把这个臭朋友扔到荒原上,却发现原来是一大箱子奶酪。在路上转运站把货给弄错了,他们那个可怜的朋友也不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想马克·吐温写这个故事的用意,大概就想证明一点——奶酪比死尸都要臭!
安徽沿江一带很有些地方的人喜欢吃臭的东西。以前我在芜湖上班的时候,经常晚上到白马山后面一个小菜场买人家做的油炸臭豆腐干吃。冬天洗完澡出来,就坐在小菜场里等炸臭干的老太太出摊。老太太有个小孙女,她先用小板车拉来矮桌子,跟北方的炕桌差不多高,再把几只小板凳放好。老太太不紧不慢地收拾东西,样样收拾清爽后就开油锅。夜气中有好闻的菜籽油味道,我看着臭干子在油里慢慢浮出来,像一个花样游泳的运动员。臭干子在油里慢慢变得大起来,浑身布满小包,癞蛤蟆的背一样。老太太把炸得差不多的推向锅边,她的孙女就将炸好的臭干子一只一只夹起来。然后问旁边闻香的人:“你吃几只?你吃几只?”现吃现炸。
这家炸臭干的干子是自己家做的,放在几只木桶里,上面盖着灰白色的布,码得很整齐。臭干子像江南人家的屋瓦一样,上面的黛色是一种臭卤的颜色。春天的时候沈书枝回南方,早晨吃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臭干子。她说小时候在家吃粥,听见卖臭干子的来了,就跑出去买一块放在碗里蘸辣椒酱吃。我说我小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吃,黛色的皮下面是嫩得蛋花一样的干子。这个老太太家的臭干子就炸得这样好,好像里面白色的是流质的。吃的时候要拿一只手在下面托着,似乎随时可以流下来。这祖孙俩一晚上卖两百块干子,等到她们带来的矿石灯发红的时候就收摊子。她家做的辣椒糊也好吃,一种青辣椒糊,一种红辣椒糊,用两个黄釉子瓦罐子装着,一个写红,一个写青,能吃辣的人自己舀。
我老家的饮食习惯也喜欢吃臭的东西。但鱼和动物变质,坚决扔掉。不大用酱油,有的人家终年酱油不进门。烧鱼和肉,就到院子里的酱钵里挖一勺酱放在锅里。芥菜每年冬天腌一大缸,腌半个月就能吃。有的人家讲究,还在里面放上姜丝。这个时候芥菜掏出来炒肉丝非常好吃,勃勃地能下几大碗干饭。但这种好日子不大有,平常也就是掏出来,连油也不搁,一人碗头上夹一揪咸菜吃去吧!肠子枯得要死,岂止是嘴里淡出鸟来,连鸟都淡没了也未可知。等腊肉晒好了,日子又好过了。中午蒸腊肉,家里按人头数,一人一块,透明如黄玉般的腊肉铺在臭咸菜上。碗里的油和菜汁可以浇饭,这个东西又不容易到口,刚盘算好,我堂弟早把饭扣在碗里了。到了初夏季节,菜就开始烂了,发出一股恶臭,像田间地头沤烂植物的臭气。咸芥菜发酵后会变成泥一样的东西,连颜色也和塘泥一般无二。
这个时候的臭芥菜好蒸豆腐了。从坛子里把臭芥菜的卤盛出来,浇在豆腐上。上面放一些姜丝和红辣椒,放在饭头上蒸。一直蒸到豆腐上起蜂子窝,夏天人胃口不好的时候拿出来吃,相当杀饭!过去没有青霉素的时候,老痨病人就天天吃这种臭咸菜水,吃到肺部病灶钙化了,病也就好了。可能是成功率比较低,只是作为一种偏方在乡下流行。如果林妹妹知道这个方子,也许不会死。不过怎么让她这样一个冰清玉洁的人儿吃这种能臭得死人的臭卤,也是一件让郎中很挠头皮的事情。我听说有些地方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臭着,冬瓜、豆角、辣椒或者白菜帮子。我们当地还有许多人爱吃臭鸭蛋,鸭蛋在咸的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了,或者是混进了生水,或者是——谁知道呢,反正腌出来的鸭蛋不是红白相间,反而带点绿色,触鼻地臭,连拿过鸭蛋的手都是臭的。有的人就爱这一口,爱到有点变态,如果家里腌一坛子鸭蛋没有坏掉,几乎都可以把他气得半死!因为臭了别人不要吃,他可以一个人独享了。
安庆人有喜欢吃一种臭白菜的。冬天矮棵白菜从田里铲了来,晒蔫了放粗盐,放在大木盆里用手揉,把水分挤出来,一棵一棵码到坛子里。最后把揉出来的菜汁也倒进去,用一块大石头把菜压住。坛口封紧,这个时候不急着动它。一直等到夏天,坛子盖一揭,外面的绿头苍蝇如同听到玉音放送一般,全涌进家里。这说明臭白菜做成功了。夏天晚上把家门口的地用水浇了,凉床、竹笆子、躺椅通通用水洗了。煮一大钢精锅绿豆稀饭,中午吃剩下来的饭炒一炒。菜就是这种臭白菜,里面加大量的红辣椒,炒蒸都很相宜。我问安庆人,说臭白菜其实是酸白菜腌坏了的产物。夏天晚餐,几乎家家都准备这道菜,只不过有的臭,有的不臭,臭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摘自《橄榄成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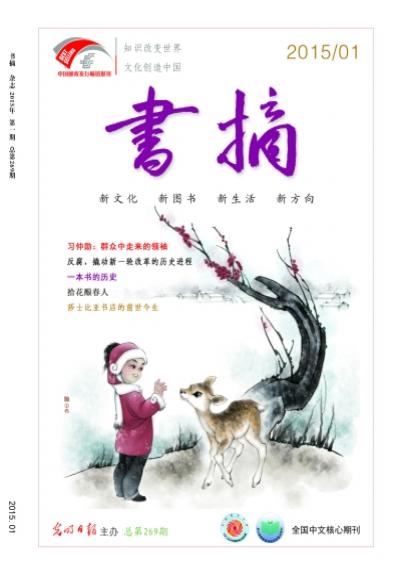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