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小聚,偶尔谈到某热播连续剧,有人戏称之为“中产阶级堕落宝典”,当场被一位淑女善意提醒:“您可别成九斤老太啊!”于是哄堂大笑。
话题很快切换,我却不禁暗自浮想联翩起来。哄笑之由,并非座中一客被誉为“九斤老太”,乃因说者自居时髦,却一本正经吐出一个很落伍的词,这就多少也有点幽默。
“九斤老太”,鲁迅小说《风波》里一笔带过的人物,与阿Q、祥林嫂、闰土、假洋鬼子、孔乙己一道,一度成为货真价实的流行语,但如今已不甚流行,虽然比谌容《人到中年》里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名气更响,较之也曾奔赴鲁迅笔底、永远保鲜的国骂,可就短命多了。
新词迭出,表征社会进步。比如“发扬”什么,自幼用惯,曾几何时已被“弘扬”取代。上下一心,咸与“弘扬”,“发扬”就黯然失色;有些场合改作“发扬”,反而不够庄重。从红色年代过来的人都熟悉“光辉”一词,当时只觉臻乎其极,无以复加,孰料又有“辉煌”取而代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盛大场面若无“再造辉煌”“共创辉煌”予以描写,烘托,似乎缺了什么。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感情”单独使用很可能变成“敏感词”。小说中写不写感情,写到什么程度,主体是谁,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现在不也被风光无限的“情怀”代替了吗?话筒在手,舍“情怀”而就“感情”,恐怕通不过。还有“文化意识”换作“人文精神”,“安居乐业”换作“诗意的栖居”,“杰出人物”换作“一道亮丽的风景”,“下岗”换作“待岗”,电脑代替毛笔铅笔圆珠笔钢笔的“写作”偏说是“书写”,刚刚还“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一声令下,全改“感动”,连先进模范也成了“感动某某年的几大人物”。“难忘的一刻”已深入人心,忽然升级为“视觉盛宴”乃至“视听饕餮的盛宴”。“表现”刚冲破“再现”的封锁扬眉吐气,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演绎”收编,演艺界的凡事“演绎”几乎等于万能胶性质的“搞”。“呈现”较之“出现”已然踵事增华,不料还有“巨献”黄雀在后。“隆重推出”够隆重了,更有“盛大登场”“倾情上演”,真是鲜花著锦,烈火烹油。许多人一起走路曾被冠以“事件”“风波”,乃至陷入命名的尴尬,换成“群体性事件”,则别开生面,境界全出。“四化”“小康”何其“辉煌”,但几十年下来,乔治·奥威尔所谓“新说法”如雨后春笋,更新之速,惟房屋拆建道路翻修可以媲美。再用旧词,若非“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也只能是“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检梳妆”了。
但语言发展并非一味舍旧图新,也有推陈出新。末世论相信一切所言最后都要被审判,语词一旦造出,就不会废弃,至多存放在人所未识的永恒里,一朝激活,照样流行。据说英语最不济,任何新事物都得铸造个性化新名词,海量增加,因此难学。不像汉语,几个常用字稍加组合,就应变无穷,如“扫黄”“打非”“低保”“博客”“上网”“灌水”“环保”“全球化”“脑残”“伪娘”——对旧词或旧用法或疏离,或回归,或仿造,脱胎换骨,点石成金,似新实旧,可旧可新。
成语与器物无关,系乎文化心理,稳定性更大。许多从《尚书》《诗经》开始就雷打不动,绝无废弃(存放)之虞。《尚书·禹贡》述尧至暮年有“南巡”,“共工”“驩兜”“三苗”“鳏”,恰为“四罪”。尧死,百姓“如丧考妣”。舜之德政,“百兽率舞”。《诗·蒸民》有“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小雅》有“万寿无疆”,《关雎》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至今沿用,不绝如缕。
奥威尔说过,“和语言滥用现象搏斗往往皆显得多愁善感古趣盎然”(《政治与英语》)。说“搏斗”有些夸张了,放手滥用,也翻不出语言之网。许多簇新语词其实只不过是旧词重新包装而已,比如当今“网络红人”漫天飞舞的那些诨名绰号,不都是“多愁善感古趣盎然”吗?语言的惰性令一切创造事先变得陈旧。张世禄先生曾以《诗经·君子于役》为例说明汉语里许多“基本词”,“经过千百代保存下来而没有加以变化”(《汉语历史上的词汇变化》)。“活在当下”、陶醉于词语爆炸的绚丽光芒、好像天天在做仓颉的人,大概不会承认,但这恰恰也是马列经典作家的语言信念:“基本词汇是基本上完全保存下来的,并且使用为语言的词汇的基础——把千百年积累起来的基本词汇消灭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间内创造新的基本词汇,那就会使语言瘫痪,使人们完全丧失相互交际的可能。”(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究竟人“说”语言,还是语言“说”人,真的很难讲。
算不得“基本词”的“九斤老太”是否也会咸鱼翻身,重新流行呢?要打赌,或许可以稳操胜券。
(摘自《时文琐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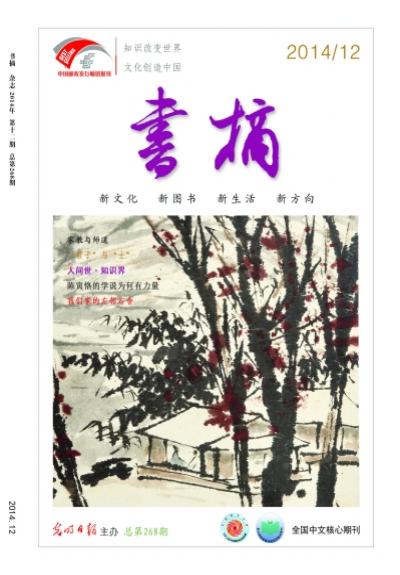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