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提要】
《洗澡》,借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描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书中的主角许彦成是一位举人女儿的遗腹子,读大学期间,聪敏又老实的个性被“标准美人”杜丽琳看中,在母亲逼婚压力下,许匆匆和杜结了婚,婚后两人先后出国留学。全国解放后,许彦成兴高采烈回国了,夫妻被分配到文学研究社工作。他对妻子尊重体贴,但杜丽琳有时要怀疑,自己是否真正抓住了他的心。
姚宓的父亲姚骞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抗战前夕没有随校南迁。北平沦陷后,原有的不少房产祖业渐渐卖光,被人看成败家子,却不知他的家产多是通过国学专修社的中共党员资助了北平地下党活动。抗战胜利前夕,姚骞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太太闻讯亦中风瘫痪,女儿姚宓为给母亲治病,抵押房产,辍学到大学图书馆作管理员。姚骞的“国学专修社”,政府接管后改为文学研究社,姚宓被安排在该社图书室工作,就近照顾母亲。
罗厚是个“野小子”,和姚宓在大学同班,还是远亲。姚家败落后,很多事靠他帮忙。姚宓品行纯洁,人格高尚,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自然美。罗厚曾为保护姚宓而与流氓打架,对姚宓崇拜爱护,但两人没有想到要谈情说爱。
姚宓在工作中常与专家老先生们打交道,看不惯有些人对漂亮女人的馋相,怀疑他们是假道学。但许彦成不一样,他很有气质,对她客客气气,却很友好,她对他也不存戒心。彦成常到图书室来翻书和借书,也欣赏姚宓读书多,悟性好。他们偶尔谈论作家和作品,很说得来。人丛里有时遥遥相见,彦成会眼神一亮,和她打个招呼,饱含“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温情。两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实为思想改造运动的所谓“洗澡”,互相了解加深。但两人约好,只做君子之交。
一
姚宓到姚家赠书的博文图书馆报到,图书馆长亲自接见了她。馆长说:“你该知道,管理图书是专门之学。咱们国家从前曾经派送多位专家出国学习,如今健在的只有梁思庄先生一人了。你去见见梁思庄先生,向她当面请教。”
姚宓到新北大进修。同宿舍的学生是个高个儿的女孩子。她很热心,帮她打开铺盖卷儿,还帮她铺床,又帮她整理书桌。
那女孩子学名李佳,大家都叫她小李,是独养女儿。父亲是最高学府的中文系主任李先生。
姚宓觉得她天真可爱。她跟小李同吃了晚饭,小李又带她上四楼屋顶一一指点:哪里是图书馆,哪里是大礼堂,哪里是教学楼等等。她忽然遥遥指着说:“快看!快看!”
真是无巧不成书,姚宓看见杜丽琳挽着许彦成的胳膊,亲密地向校门走去。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姚宓暗想:“他们准是又在吵架呢。”
她问小李:“你认识他们?”
小李说:“啊呀,姚姐姐,他们是新来的外语系教师,女的专教口语,她最洋,绰号‘标准美人’,可是我爸爸不喜欢她,说她太‘标准’。姚姐姐,你是天然美,你是一级,她只是二级。”
小李告诉姚宓:“我爸爸很赏识许彦成先生。”她觉得姚姐姐一惊,好像脸都红了。她说:“姚姐姐认识许先生吗?”
姚宓只好说,许先生从前是她的老师。小李顶乖觉,她怀疑姚宓看中许先生,或是许先生看中姚宓。她说:“爸爸说,标准美人出风头,不稀奇。许先生淡定低调,装得自己庸庸碌碌,装成庸中之庸,很不容易啊!他老是忧忧郁郁的,肯定和那个标准美人合不到一处。”
姚宓装作不经意地说:“许先生和杜先生很要好的。”
二
1957年早春,全国都在响应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陆舅舅很起劲,他对姚宓说:“阿宓啊,你瞧着吧,学生都动起来了,要上街了!”
姚太太和王正、马任之是很要好的。每有什么政治运动,马任之总叫王正过来跟她们母女打招呼,叫她们小心,别犯错误。他俩是负责文教工作的领导干部,学校归文教部门主管。他们来看姚太太,和姚太太交换过对整风运动的个人意见。姚太太和女儿私下讨论,姚宓说:“我不是党员,不用太积极,只求‘安居中游’。不过,中游也不稳当,最好少发言,只说自己‘觉悟不高’,‘认识不足’,总比多说话稳当。”
姚宓不敢把王正、马任之他们的意思说出来,可是爱护舅舅,还是劝了一句:“舅舅,说话小心啊!”
陆舅舅说:“你小孩子家懂什么,这可是国家大事啊!”姚宓就没再多说。
陆舅舅没想到早春天气,阴晴不定,第二天醒来,风向突转,气候大变。他的鸣放言论,让他犯了大错,受到猛批。他吓得不能睡,饭也吃不下,他病了。半夜起床,中风倒地。他瞪着两眼,伸着一个指头,不知指着什么东西,好像想说什么话,却一命呜呼了。
陆舅舅去世后,原单位派来的服务员全撤走了。陆家花园,没人收拾了。姚太太、陆舅妈、陈姨妈、沈妈几个女眷住在偌大一座宅院里。日子久了,打开花园门一看,只见一片荒芜。
姚太太是个有主意的人,凡事采取主动。她知道陆舅舅单位早晚会收回陆家花园,顶多给陆舅妈安置个小住处。姚太太打算早些搬入她家的老四合院,免得临时手忙脚乱。于是又让姚宓去与马任之夫妇商量,向他们求助。
王正告诉姚伯母和姚宓,最高学府有些事没做对,说:“我问过党委有关负责人,杜丽琳一向紧跟领导,发言最正确,怎么会发右派言论?那位负责人说,她开会的时候说,她‘同意方才那位同志的话’。她结结巴巴,学舌也不会,只说‘听党的号召,响应号召,大鸣大放。’我说:‘听党的话,没错呀!’可是那位领导只呆着脸。我想杜丽琳是凑数弄上去的,每个单位都有划右派的指标呀!我知道这位负责人得保全自己的面子,我也得顾全他的面子。我就笑笑说:‘谁叫她说错了话呢。错误既不严重,就对她从轻发落吧。’另外一个是政治经济系的叶丹。他不懂马列主义,他教政治经济学,肯定出毛病。可是上课说错了话,并不等于就是右派言论呀。还有历史系一个刘先生,也是讲课说错了话,也没有右派言论。”
王正接着说:“伯母,我对您是推心置腹的。我和任之当年在地下活动,全靠姚伯母和姚宓的掩护。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任之撤退了。我和几个地下党员还照常在文学社工作。伯母,您是我们地下党的大恩人呀。姚骞先生是阔公子,人家说他把家产都败光了。其实还不都是支援了地下党活动嘛。他是对新中国的建立有功的。”
王正又感叹说:“哎,生活在不断革命的时代,日子过得真快,一场斗争刚完,接着又是一场。任之和我满心想为伯母和姚宓做点什么,报答一下您一家人的恩情,却始终没能实行。现在你们那个陆家花园已被很体面的大人物看中了,你们可能也住不下去了。我们很高兴能为姚伯母整理一下四合院,帮助搬个家,让我们尽尽心意。”她提议这个周末就与任之陪姚宓同去看看那所四合院。
三
杜丽琳不幸划为右派,立即工资降了三级,限期下放劳动改造,来到皖北一个荒僻的山村落户,初下乡就遇上了闹心事。那里家家墙上都画着大大的白圈。在行的人,就知道当地有狼。他们吃饭、住宿的两个席棚,又不在一处,大家心上寒凛凛地害怕。
有一个人发表了他的高见。他说:“一个村子也有好几户人家呢,狼是合群的。如果有狼群,早把村里人都吃光了,几个大白圈顶什么用呀!照我看,这里的狼只是失群的狼,准怕我们成群的人。咱们一群人也不少呢,寡不敌众,那一只两只失群的狼,咱们不用害怕,防着点就行。”
大家觉得这话有理,出了宿舍总结队同行。女同志都挨着壮硕而比较友好的男同志,指望他们保护。
很多人愿意走在杜丽琳旁边保护她呢。她对这些人很少看得上眼的。有的两眼贼溜溜的,有的一双眼睛好像害了馋痨。她留心挑选,中意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比较壮硕,一个很文秀。文秀的就是那个断定村里没有狼群的人。他个子高些,比另一个瘦。他对杜丽琳最冷漠,好像对这位美人漠不关心。
一次,丽琳中意的那个壮硕的男同志走在她旁边,他故意放慢脚步,落在一群人的最后面了。他站定了对丽琳说:“瞧,夕阳西下,多美啊!城市里倒是看不见的。”
他们不敢走远。附近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在女宿舍西边的大树下。那儿有块大石头,可以坐两三个人。那人带了杜丽琳去坐在石上。他忽在杜丽琳胸口摸了一把。杜丽琳立即反手重重地打了他一巴掌,飞快逃回宿舍。她自己都惊奇,“我怎会这么泼辣呀!”她也警惕地对自己说:“黑地里男人会变相。看上去老实的人,黑地里会变流氓。”
第二天,那个吃了大巴掌的人照样对杜丽琳殷勤保护,昨夜的事好像不曾发生。
杜丽琳存心要试验一下,那个文秀的人黑地里是否也会变相。她故意和那人走在最后,模仿昨天那人的话说:“看,夕阳西下,城里是不多见的。”
那人说:“我早注意到了。乍一见,是很美,可这里太干燥,没有一点云彩,太阳一下,天就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杜丽琳想把他领到那个隐蔽的大树下去坐坐。那人说:“那边不是好地方,说不定还会碰上失群的狼。”
他忽然很聪明地问:“你是不是去过了?”
丽琳撒谎说:“没去过。”
那人说:“那么我警告你,谁要带你去,你不要去,那人准是不怀好意。”他只送丽琳走近女宿舍,就急急回自己宿舍去了。
这人叫叶丹,是本校政治经济系的教师。丽琳和他不熟,现在却心上念想着他。
他们俩没机会深谈,丽琳心上老在跟叶丹说话,老在想他。丽琳忽然明白,她是爱上叶丹了。她细细观察,同队来所有的人,数叶丹最聪明,人品亦好,是她最中意的人。她只恨自己是有夫之妇,不能追求他了。
她回想当年追求许彦成,只是为自己找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丈夫,她从来没有为他魂思梦想。
同时,她也注意到,叶丹对她的淡漠是假装的。他常在偷偷儿看她。
有一天,叶丹忽然问丽琳:“你到了这里来,怎么没寄过家信?我妈已经给我来过四次信了。最近的信是八月中秋。”
丽琳到了这个劳改营,从没想念过许彦成,从未写过家信。丽琳从没有写过家信,许彦成不知她的地址,怎能来信呢。丽琳经常感到自己的孤单。这时听了叶丹追问,不由得一阵心酸,眼泪簌簌地掉入饭碗。
叶丹是很聪明的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丽琳爱他,他哪会不知道呢?可是丽琳对丈夫的情谊,他无从得知。叶丹虽然不由自主地迷恋着丽琳,他却不愿拆散别人的家庭。
叶丹说:“丽琳,现在天越发长了,七点以后才天黑,你宿舍西头的大树底下,天黑了没人,今晚八点我在那儿等你。八点。”
丽琳点点头,急忙走了。
晚上,杜丽琳赶到大树底下,叶丹也刚到。他们都准时。他们就在大树底下的大石头上坐下。
叶丹说:“我约你来,不是为了谈情说爱,我有要紧话问你。我们得把话缩得越短越好。这里很危险,如果给人知道了,咱们俩就永远不能见面了。”
丽琳点点头。
“我先问你,你和老伴儿感情很好吗?下乡那天,他不是扛着你的大铺盖卷儿送行吗?你是不是变心了?”
丽琳说:“他不过是可怜我罢了。他无情无义,我一片痴心地爱他,他只是嫌我。他有他的意中人。”
“那么,你应该和他离婚和我结婚。你愿意吗?”
“我不做女朋友。”
“当然,我现在好比跪着向你求婚。爱我,就说:‘叶丹,我爱你。’”
丽琳说:“叶丹,我爱你。”
叶丹紧紧抱住她,吻了她一下。这一吻,直吻到她心窝深处了。她是结婚多年的女人,却从没有体会过这种情味。
杜丽琳和叶丹私定终身之后没几天,主管他们劳动的头头,把丽琳、叶丹和同校一个历史系的刘先生叫到他办公的地方,对他们说:“你们来了快半年了吧?你们的学校召你们回去了。这里没一个大右派,都要回原单位了。你们三个是第一拨。你们赶紧把该办的手续办妥,带了自己的东西回北京吧。”
车到北京,约摸是下午五点。杜丽琳到校,正是黄昏时分。按了一下门铃,开门的是罗厚。他正在许彦成家陪伴独居的许先生呢。
杜丽琳问罗厚:“许先生呢?”
“出去了。”
“你怎么在这儿?”
“是姚伯母叫我来陪伴许先生的。啊呀,我家出了许许多多事。陆舅舅去世了,他差点儿成了大右派……”
他看到杜丽琳疲倦的脸,很知趣地说:“咱们要谈的事太多了,您且歇歇,我给您做饭去。”他先给坐在沙发里的杜丽琳沏了茶,倒了一杯,端给她。
杜丽琳喝了几口茶深深吸了一口气,闭着眼说:“哎!我总算回家了!”
罗厚见此情景,不等许先生回来,做好饭就走了。
许彦成回来就见到了已经吃饱喝足的杜丽琳。对她说:“丽琳,你怎么不写封信来告诉一声?”
他挨着杜丽琳,坐在她身边。她是刚下火车的人,身上又脏又臭,他不愿碰她。
杜丽琳对他看了半天,立即起身,坐得更远些,把她在火车上想好的话,一口气说了出来。她说:“许先生,请你解放了我,你有你的意中人,我也有我的意中人,我和你从此分手吧。”
许彦成心里快活,他抑制了自己,客客气气地说:“你的意中人是叶丹吧!”因为送行那天,看见这位帅哥和杜丽琳在卡车上坐在一处。
杜丽琳点点头,鄙夷地看着许彦成。
许彦成说:“我明天就走,让出这屋子给你将来和叶丹同住。”
杜丽琳说:“谢谢你,不过眼下不行,叶丹和我还有刘先生都还得监督劳动呢。况且我和你还没有离婚,咱们先得把离婚手续办了。”
许彦成知道丽琳不会做饭,所以照旧到经常吃饭的小饭馆去吃,然后又买两份饭,装在他自己带去的饭盒里,让傍晚回家的杜丽琳和叶丹煮煮热再吃。这样,他在学校宿舍又住了一段时日。
四
许彦成正要回四合院那天,罗厚忽然来了。彦成把他的喜讯告诉了罗厚,罗厚“嘣”一下坐在沙发里,又拍手,又跺脚,高兴得不知怎么好。许彦成说:“你来得正好,告诉你吧,我已经和杜丽琳办了离婚手续。”罗厚为许老师的最终解脱长出了一口气。
许彦成笑着说:“我将来是姚家倒插门女婿,你是李家倒插门女婿;李家阔,不会要你费力,我可负担着姚家的生活呢,姚宓是最孝顺的好女儿。”
两人说这话,杜丽琳和叶丹就回来了。
罗厚涎皮赖脸地招呼了杜老师,对杜丽琳和叶丹说:“我们都担心你们下放要吃苦了,谁知道你们是去谈情说爱的,一个找到了如意郎君,一个找到了心爱的美人。”
杜丽琳马上接话说:“你们哪里知道我们这群倒霉蛋过的是什么日子,半死半活的天天受罪。说一句没良心的话,我们干脆死了,倒也不知不觉。人家还以为我们多浪漫呢,劳改劳改,倒是去谈情说爱了!”
杜丽琳恨恨地说:“我早打定主意了。我们俩要是留得性命回北京,再也不做倒霉的教书先生了。当然我们怕是也没有资格了。想当年,我做校花的时候,也是好一朵校花呀。做了教书先生,胭脂、粉都不敢用了。咳,现在竟变成犯人似的了。不过,即使是劳改犯,也有个刑满的日子,到我们劳动期满,我们就该滚蛋了,有什么脸做降了级的教书先生呀!我现在想想,从此我就隐姓埋名,哎,我当个大户人家的老妈子,多享福呀!”
叶丹说:“我也在想从此改行了,你当老妈子,我开饭馆,都能过日子。”
许彦成说:“别开什么饭馆,饭馆不是好开的,得和流氓、瘪三、混蛋打交道。我倒有个好主意,叫叶丹学照相,将来可以开个照相馆,把自己最美的照片摆出来做‘招牌’。”
杜丽琳说:“照相是叶丹的专长,不用学。”
罗厚说:“太好了!你们开照相馆吧,你们两个照一张漂亮的结婚照,放在橱窗里。你们专给明星照相,也照名人,说不定还有领导人来照标准相呢!”
杜丽琳看看许彦成:“也给名教授照相。”
许彦成笑说:“我只是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一辈子不会出名,只是个穷教师。我预祝你和叶丹发大财!”
叶丹拍手叫好,他说:“我们这样也能过日子,只求后半生两个人能够厮守在一起足矣。”
叶丹随即把他们半饥半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苦况向他们诉说。
杜丽琳叹了一大口气说:“穷人是穷惯的,我们却是忽然间从上面倒栽下去的,到现在头还没着地呢!”
叶丹说:“大约等我们两个结了婚,成了家……”
大家默然。四人坐在客厅里谈到夜深。
第二天早上,许彦成醒来,罗厚已经为他们做好早饭,许彦成和他同在厨房里吃了。罗厚说:“许先生啊,你是在伺候他们两个!你伺候杜先生也罢了,她毕竟是你多年的老伴儿。那位帅哥,又凭什么受你伺候呢?”
许彦成笑说:“感谢他解放了我吧?”
罗厚说:“我可看不惯,他们的劳动没个完呢,你就老陪着他们?陪到几时?你难道要等着和他们一对儿一起结婚吗?”
许彦成说:“我不忍叫他们两个没饭吃呀。”
罗厚嘀咕说:“许先生啊,你就是心肠太好。杜先生欺负得你还不够吗?我这会儿就为他们找个阿姨,要求住在东家吃一顿夜饭,白天为家家干活的阿姨肯定有。”
不一会儿,果然来了一个干干净净的林妈,她先看了自己的房间和厨房,都满意。罗厚就预付了半个月的工资,说明是伺候下乡劳改才回来的一对未婚夫妇。罗厚吩咐她多买些小米儿,连带一天的小菜也让她随意买点回家。他把许先生的钥匙给了她。
他要和许先生一起回四合院。许彦成不肯,说要当面和杜丽琳、叶丹交代清楚,马上就回来。
杜丽琳和叶丹都回家了,许彦成介绍林妈见了两人,彼此都表示满意。
许彦成说:“已付了半个月的工资。”叶丹要还他,丽琳只说了声谢谢。彦成接着又说:“明天一早上,我就走了,祝你们幸福快乐。”
许彦成就此和多年的老伴儿分手了。他临走利用学校热水方便洗了一个干净澡,好像把过去的事一股脑儿都冲洗掉了。
从此姚太太和女儿女婿,在四合院里,快快活活过日子。
中秋佳节,李先生预备了一桌酒席,一来为姚太太还席,二来也是女儿小李和罗厚的订婚酒。时光如水,清风习习,座上的客人,还和前次喜酒席上相同,只是换了主人。
(摘自《洗澡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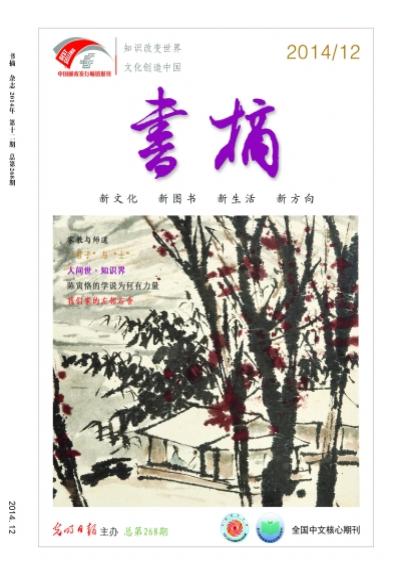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