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昭和二十)年8月6日,广岛天气晴好,无一丝云,却出奇地闷热。
清晨7:09,空袭警报拉响,因为城市上空出现了3架B-29轰炸机。但飞机很快就飞走了,7:31,警报解除,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的节奏。然而,45分钟后,另一架B-29轰炸机“伊诺拉·盖伊”号盘旋而至,然后从市中心的上空投下了一颗长3米、直径71公分、约3吨重的“新型炸弹”,代号“小男孩”。炸弹在距地面570米的空中爆炸,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为150米的巨大火球,放射出耀眼的异样光芒。火球缓缓上升,直至6000米高空,形成一团蘑菇云。蘑菇云的下面,成了地狱:爆炸中心点方圆500米以内,全部人和物被3000~4000℃的高温烧成焦炭。截止当年11月,据日本政府发表的统计数据,逾7.8万人死亡,8.4万人受伤,1.4万人失踪,6万户家屋全毁或半毁。其后,因核辐射而罹患被称为“原爆症”的不治之症,最终死于该症者,不计其数,乃至精确的统计至今仍无法完成。1976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说,死于“热线、暴风和放射线的人多达14万(误差1万)”。一个繁荣的城市,就这样被一颗神话般的“新型炸弹”彻底摧毁。
从军部、政府到普通国民,完全不知道受到了何种武器的袭击。8月8日,刊载于《朝日新闻》的“大本营发表”只是说:“6日,广岛市受到敌B-29轰炸机的攻击,发生相当程度的受害。敌在攻击中,似乎使用了新型炸弹。其详情目下正在调查。”爆炸发生时,正在位于广岛宇品的陆军船舶司令部服役的一等兵、战后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政治学者的丸山真男,结束了一次紧急集合,暂时解散后,刚回自己的房间。看到房间里的情形大吃一惊:“首先,入口处大门的合页脱落,门朝里倒下。有的桌子翻了个个。到处是散落的文件,一屋子净是玻璃碴子。”F中佐踉跄着进得门来,头上脸上被纱布包扎,只露出眼睛。丸山问:“中佐,你怎么了?”中佐“嗯”了一声,大声说道:“日本也要尽早造出好的炸弹!”当晚,丸山从短波收音机中听到了杜鲁门的声音:“投下了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随后,杜鲁门又谈了几句原子弹制造和试验的由来,说起初“源于德国的开发”。虽然丸山的英语听力有限,但他还是捕捉到了“Atomic Bomb”(原子弹)的表述。他边听边笔记,然后火速把笔记送到参谋室。可参谋们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这位东大法学部的毕业生在说什么。
与此同时(8月8日),大本营派遣了一个调查团飞赴广岛,实施受害调查。该调查团由陆军中将有末精三带队,包括陆军省的高阶军官和理化学研究所(“理研”)的精英科学家,其中就有仁科芳雄博士。仁科芳雄,1890年出生于冈山县浅口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科。1921年,赴欧留学,曾长年跟随卢瑟福和尼尔斯·玻尔等大师精研量子物理学,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具有前沿国际视野。回国后,于1931年在“理研”内设立仁科研究室,推进量子物理学研究,是主导战时日本原子弹研发活动的核心人物。
黄昏时分,运输机抵广岛,在城市上空盘旋了好几圈。仁科博士脸紧贴舷窗,俯瞰机翼下满目的废墟,低声自语道:“这是原子弹……”登陆广岛后,通过X光片被感光等事实,仁科迅速断定这种“新型炸弹”就是原子弹——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紧接着,8月9日,长崎复遭“新型炸弹”的袭击。五天后,仁科飞赴长崎调查,再次确认了“被爆”的事实。广岛、长崎先后“被爆”,首先意味着日本在原子弹研发竞争中的彻底败北。
正如广岛核爆后,杜鲁门在广播讲话中所言,二战期间世界主要大国间的原子弹研发竞争,确实源于德国。1938年1月,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和菲里茨·舒特拉斯曼首次取得了铀235元素原子核裂变实验的成功。论文发表后,举世震惊。彼时战祸未起,欧洲还是“太平盛世”,故该成果才能为世所知。
最受震动的是美国。当时美国有很多受纳粹迫害,从德国逃亡而至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首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希特勒很可能已经开始着手原子弹的研发。于是,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说如果德国先行造出核弹的话,势必会称霸世界,因此务须先发制人,“这种炸弹如果用船运,假如在港湾爆炸的话,一发就足以让港湾和周边的部分设施毁灭”。爱因斯坦写这封信是1939年8月,一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随即下达了原子弹研发的指令,同时批准了6000万美元的预算——此即后来所谓“曼哈顿计划”的雏形。至1942年9月,美国为开发计划共投入了逾50万人和2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在国内相关各州和加拿大建设了数万英亩的研究、实验和制造设施。作为民主国家,可以说破例构筑了旨在赶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核弹的“举国体制”。
与美国相比,在核裂变现象的发现和实验阶段,德国虽一度领先,但在核弹研发过程中,却丧失了先机。主要原因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排犹政策,“恨屋及乌”,觉得“原子物理学是犹太人的科学”,而“美国作为犹太人统治的国家,没啥了不起”。大概是早年失意的小布尔乔亚艺青经历使然,希特勒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全无体察,认为两年后才有可能研制成功的原子弹无非是“明天的兵器”,远水不解近渴,而他迫切需要的是导弹等“今天的兵器”。尽管有施佩尔等人拼死谏言,却终未得到希特勒的理解和支持——德国事实上放弃了核弹的研发。而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日本统治集团却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陆军和海军方面均做了相应部署,设定了战略目标,铺设了研发体制,其主导者就是仁科芳雄。
不过,与美国不惜以“举国体制”打造的“曼哈顿计划”相比,德国在原子弹研发上的投入少得可怜——全部加起来只有约100名科学家和1000万美元。日本又如何呢?约翰·道尔认为:“与美国所投入的研发经费进行准确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与美国研发计划的规模之差到底有多大,是可以感觉到的。如果粗略地以战时1美元兑4日元的汇率来估算的话,曼哈顿计划所投入的20亿美元应该是日本的3000倍以上。”
3000倍,是什么概念?何况这还只是研发资金上的差距,如果再加上人力和物资要素的话,两国的差距真不可以道里计。战后,透过曾参与战时原子弹研发工作的科学家所写的一些回忆文字,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窘况。如加热实验必须使用砂糖。因砂糖在当时是珍贵的战略物资,属于珍稀奢侈品,陆军方面迟迟不予配给。彼时在“理研”负责六氟化铀制造实验的一位名叫木越邦彦的年轻研究员实在等不及,不得不回家,从自家的厨房“监守自盗”,偷偷带回实验室,乃至遭到母亲的训斥。事实上,虽然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一些精英出于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焦虑感,锐意敦促原子弹的研发,但绝大多数日本科学家却认为不仅日本,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交战国,不可能在战争期间完成实弹的研发和制造。甚至连研发活动的核心人物仁科芳雄本人也作如是观。
战后,日本学界和传媒界也对战时日本原子弹制造研发的失败多有反思,但这种反思基本上不是围绕原子弹研发本身之罪错的道义原则问题,而是针对何以美英等民主国家能调动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和资源,应对在当时看来不啻为天方夜谭的大规模原子弹制造研发工程,反而是帝国日本和纳粹德国这样的极权国家却失败了,缘何如此的“历史教训”的检讨。1953年,曾负责铀矿探索的原陆军技术军官山本洋一发表长篇回忆,严厉批判对原子弹研发工作的负组织、主导之责的仁科芳雄等民间科学家,“只重视纯科学,对应用科学和技术则缺乏理解”。
毋庸置疑,在美日原子弹研发竞争中,日本远远落在了后面。确切地说,与美国倾其国力、志在必造的“正经”研发活动相比,日本充其量停留在研究的水平,尚未进入研制阶段。但对这一点,日本直至“被爆”的一刻,似乎并不知情。
历史往往相当吊诡。1941年12月6日,罗斯福总统一声令下,“曼哈顿计划”悄然启动,重金人海,秘密涌向几个特定的实验室和基地——美国原子弹研发事业正式起跑。翌日,珍珠港便遭日本“奇袭”,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之耻,对美国核打击目标的确立起到了何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此时,美国的敌人还有纳粹德国——德国将携其理论原创的原子弹对美制造第二个“珍珠港事件”,成了美国的梦魇和推动原子弹研发的动力。
经过近两年紧锣密鼓的竞跑,至1943年5月,美原子弹研制终于有了眉目。一般人会以为,当时美国还在跟德国打仗,原子弹的首要目标是纳粹德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72年,《海德公园协定》内容首次曝光,令世人大跌眼镜:早在1944年9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已然达成了要对日本动用原子弹的约定。1945年4月23日,“曼哈顿计划”的指挥官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中将在致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将军的信中坦言:“我们的目标一贯是日本。”据说,1945年2月至3月期间,史汀生将军的副官哈比·邦迪便已经草拟了关于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的声明文本,文本以“今天……于日本投下……”的措辞开头,只有时间是空白,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赶在苏联对日参战之前,迫使日本投降,以争取对日占领的主导权,遏制苏联。德国投降后,苏联单方面撕毁《雅尔塔协定》,闪电“收割”,把此前遭纳粹铁蹄蹂躏的东欧诸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绝不容忍东欧的“悲剧”在冷战“桥头堡”日本重演。日本投降一旦延迟,那么德国投降三个月内,苏联进攻日本的承诺期限就将到来,美国将在对日占领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此时的课题,已不是日本投降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投降的问题。
围绕日本缘何非遭遇美国核打击不可的问题,一个几乎见诸所有历史教科书的耳熟能详的说法是:因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宣言》,所以美国决定对其实施核打击,苏联也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对美国而言,此乃所谓“尽早终结战争,避免造成更多流血的日本本土战的最佳策略”。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未必站得住脚。
据半藤一利的研究,1945年7月26日,联合国军方面发表了被视为对日劝降的《波茨坦宣言》。翌日,日本接报。裕仁天皇看到文本后,对东乡外相说:“结束战争总算有了眉目。原则上对此只能接受。”但彼时,日本政府已经在私下委托苏联斡旋停战,正在等候苏方的回复。出于“信义”,客观上无法立马接受宣言的条件,而推掉苏方的“调停”。
日本人做梦都不会想到,斯大林此前已得到杜鲁门对日将实施核打击的通报,只盘算着如何能早日对日进攻,是完全无意斡旋和平的。在这种情况下,28日,首相铃木贯太郎基于“无可奉告”的意图,对新闻界表达了“默杀”的立场。29日,日同盟通信社将铃木的表态译为“ignore”(无视),并向全世界报道。日本时间29日当夜,英国路透社和美联社(AP)又分别在自己的报道中,将同盟通信报道中的“ignore”译成了“reject”(拒绝)。表面上看,至此,英美媒体完成了“日本拒绝《波茨坦宣言》的条件,决意将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的信息传递,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对日最后一战”的共识。但其实,7月24日,在《波茨坦宣言》发表之前,投掷原子弹的秘密指令就已经下达,形势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当杜鲁门总统最终认可的原子弹投掷方案出台的时候,日本的政府高官们还在焦急地等待着苏联的“和平斡旋”。以近卫文麿为全权代表、众多实力派重臣为特使的应对体制已调整就绪,准备一俟莫斯科有回复,立即切入和平交涉。日本的时代错误在于,在该讲政治哲学和道义的时候,过于迷恋实力,动辄“亮剑”;而明摆着是肮脏的政治交易,甚至是赤裸裸的欺骗的时候,却以“武士道”的“清流”面目出现,言必称“信”。回首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日本确实曾一再扮演这种“不合时宜”的尴尬角色而不自觉。
回到本文的主旨:那么,美国究竟为何非要动用原子弹不可,为什么是日本呢?窃以为,如此结局背后,至少存在如下四种动因,正是这些动因的错综作用,导致了美国对日本动用核武的唯一结果:
第一,原子弹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志在必掷”的实用武器研制的。要知道,美国原子弹制造研发源自纳粹德国核武研发的刺激,带有极强的危机感。罗斯福死后,杜鲁门继任总统,他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何时、在哪儿使用炸弹(指原子弹)的最终决定权在我,这一点不容错位。我一向把原子弹看作是一种兵器,理应付诸使用,对此从无任何疑念。跟随总统左右的最高军事顾问们曾劝诱我使用之。我与丘吉尔会谈时,他也曾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过‘如果有利于终结战争的话,赞成动用原子弹’的话。”可见,既然是兵器,使用没商量——是美国战争政策最高决策者的意志。
第二,至少从1943年5月开始,日本就已经被设定为核打击的首要目标,且越往后,越具体化。
第三,对苏牵制。美国历史学者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在其著作《原子弹外交》一书中,论证了美国如何以原子弹为砝码,在对苏外交中争取主动的过程。杜鲁门继任总统是在1945年4月12日,他面对的最大课题是如何终结战争,并在战后格局中争取主导权,而最吃紧的问题就是应对波茨坦会议。由于彼时,原子弹研发已到了核试验的最终攻坚阶段,杜鲁门尽量想把会议日程向后推迟,以期能拿到踏实的“原子弹牌”。波茨坦会议上,美英两国首脑在第一时间分享了“孩子诞生”(指核试验成功)的情报,但通报斯大林则是在一周之后。斯大林并未显得很吃惊,若无其事地说了句:“是嘛……那么就可以在日本使用了。”暗中却加紧了从“满洲国”进攻日本的进程,同时下令莫斯科的原子弹研发工作提速。
第四,对日种族歧视。这一点,作为深层动因,很少表面化,特别是在战后民主主义主流话语体系下,一向鲜为人提及,但却是一个颇为现实的因素。日本军队在战时的残虐暴行,也强化了西方对东洋社会所抱有的“日本人性恶论”的既有成见。杜鲁门有句名言——“对兽类要像对待兽那样”——说的就是日本。当然,歧视从来是双向的:有日人针对白人的“鬼畜英美”式的妖魔化,便有美国人对日人所谓“猴子”的侮辱性蔑称。既然是诸如“兽类”、“猴子”等非我族类,动用“新式武器”歼灭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回过头来看,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的惩罚,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落后就要挨打。但惟其如此,日本对其“被爆”的悲剧,也基本上抱着现实主义的应对:接受“宿命”,因为“我们应该认识到,先于哪个国家最初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它制造成功,它就会使用”。日本国内甚至不乏“原爆拥护论”者,如上文中提到的原陆军技术官僚山本洋一便认为“战争就是战争”,遑论对殖民和侵略战争持严厉批判立场的传统左派。
正因此,1945年8月6日,广岛“被爆”后,日本政府虽然通过瑞士等第三国表达过对因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制造的反人道罪行的抗议,但面对美国政府,时至今日,却一次都未曾提出过直接的抗议。而这一点,至今仍鲜为人知。
(摘自《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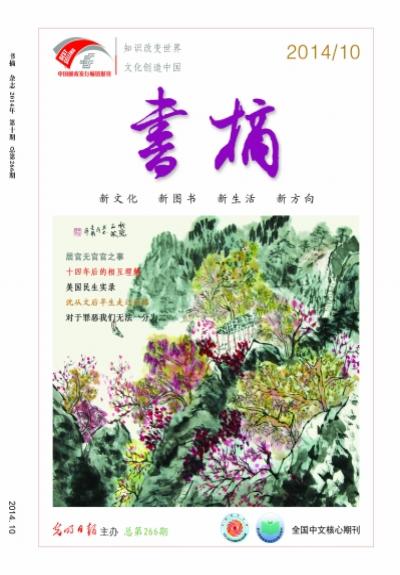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