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 逝
在大千居士最后一次入医院的前几天的下午,我去摩耶精舍,门者告诉我他在楼上,我就直接上了楼,他看见我,非常高兴,放下笔来,我即刻阻止他说:“不要起身,我看你作画。”随着我就在画案前坐下。案上有十来幅都只画了一半,等待“加工”,眼前是一小幅石榴,枝叶果实,或点或染,竟费了一小时的时间才完成。第二张画什么呢?有一幅未完成的梅花,我说就是这一幅罢,我看你如何下笔,也好学呢。他笑了笑说:“你的梅花好啊。”其实我学写梅,是早年的事,不过以此消磨时光而已,近些年来已不再有兴趣了。但每当他的生日,不论好坏,总画一小幅送他,这不是不自量,而是借此表达一点心意,他也欣然。最后的一次生日,画了一幅繁枝,求简不得,只有多打圈圈了。他说:“这是冬心啊。”他总是这样鼓励我。话又说回来了,这天整个下午没有其他客人,他将那幅梅花完成后也就停下来了。相对谈天,直到下楼晚饭。平常吃饭,是不招待酒的,今天意外,不特要八嫂拿白兰地给我喝,并且还要八嫂调制的果子酒,他也要喝,他甚赞美那果子酒好吃,于是我同他对饮了一杯。当时显得十分高兴,作画的疲劳也没有了,不觉的话也多起来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他毕竟老了,看他作画的情形,便令人伤感。犹忆1948年大概在春夏之交,我陪他去北沟故宫博物院,博物院的同人对这位大师来临,皆大欢喜,庄慕陵兄更加高兴与忙碌。而大千看画的神速,也使我吃惊,每一幅作品刚一解开,随即卷起,只一过目而已,事后我问他何以如此之快,他说这些名迹,原是熟悉的,这次来看,如同访问老友一样。当然也有在我心目中某一幅某些地方有些模糊了,再来证实一下。
晚饭后,他对故宫朋友说,每人送一幅画。当场挥洒,不到子夜,一气画了近二十幅,虽皆是小幅,而不暇构思,着墨成趣,且边运笔边说话,时又杂以诙谐,当时的豪情,已非今日所能想象。所幸他兴致好并不颓唐,今晚看我吃酒,他也要吃酒,犹是少年人的心情,没想到这样不同寻常的兴致,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晚餐。数日后,我去医院,仅能在加护病房见了一面,虽然一息尚存,相对已成隔世,生命便是这样的无情。
摩耶精舍与庄慕陵兄的洞天山堂,相距不过一华里,若没有小山坡及树木遮掩,两家的屋顶都可以看见的。慕陵初闻大千要卜居于外双溪,异常高兴,多年友好,难得结邻,如陶公与素心友“乐与数晨夕”,也是晚年快事。大千住进了摩耶精舍,慕陵送给大千一尊大石,不是案头清供,而是放在庭园里的,好像是“反经石”之类,重有两百来斤呢。
可悲的,他们两人相聚时间并不多,因为慕陵精神开始衰惫,终至一病不起。他们最后的相晤,还是在荣民医院里,大千原是常出入于医院的,慕陵却一去不返了。
我去外双溪时,若是先到慕陵家,那一定在摩耶精舍晚饭。若是由摩耶精舍到洞天山堂,慕陵一定要我留下同他吃酒。其实酒甚不利他的病体,而且他也不能饮了,可是饭桌前还得放一杯掺了白开水的酒,他这杯淡酒,也不是为了我,却因结习难除,表示一点酒人的倔强,听他家人说,日常吃饭就是这样的。后来病情加重,已不能起床,我到楼上卧房看他时,他还要若侠夫人下楼拿杯酒来,有时若侠夫人不在,他要我下楼自己找酒。我们平常都没有饭前酒的习惯,而慕陵要我这样的,或许以为他既没有精神谈话,让我一人枯坐着,不如喝杯酒。当我一杯在手,对着卧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间,却也没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
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
溥心畬先生的画首次在北平展出时,极为轰动,凡爱好此道者,皆为之欢喜赞叹。北宋风格沉寂了几三百年,而当时习见的多是四王面目,大都甜熟无新意,有似当时流行的桐城派古文,只有躯壳,了无生趣。心畬挟其天才学力,独振颓风,能使观者有一种新的感受。
他的润笔在北平琉璃厂肆固然是居第一位,而后门大街小书画店,也偶有他的作品出现,其价值自不同于厂肆。据说这都是他家的佣人流出来的,因为他的恭王府距后门大街甚近,佣人们与后门的店商,难免都有往来的。一次吾友常维钧兄在这家店里看到一小捆心畬写的对联,维钧选了两副,米襄阳的笔意,极佳。等我去时,剩下的只有成亲王体了,我买了两副,定价不高,每副两元。所有题款却非溥儒,也不是心畬或西山逸士,而是“仲衡”两字,下钤“省心堂”小印。“仲衡”是他早年的字,后因京剧有一名演员叫“郭仲衡”的,他就不用了。
后来我又在那家店里,收了一幅山水小品,旧高丽纸,元人笔意,萧疏有致,维钧看了也以为是一幅好画。不意两三天后,我在那家店里发现了同样的一幅,为之奇怪,我买的难道是赝品么?于是我请袁珏生先生鉴定,珏生名励准,前清翰林,名收藏家,所收古墨尤知名海内。此老当时在辅仁大学美术系讲授“书画题跋”,我将画带到教员休息室,他一看就说是心畬的真迹,并说心畬喜欢一张稿子画上两三次,这样的事,当他在台时也证实了。以现在观念看来,如此“拷贝”有什么价值?我想,他大概以笔墨为主,构图并不重要。如倪云林的画,并看不出什么高山峻岭,又如古人作品往往题曰仿曰临,却不减其流传的价值。虽然如此,心畬的精品,没有不可以看出他的匠心的。至于他自以为游戏之作如《西游记》图等,意趣横逸,想象力之高,则是前无古人的。
当时我还收了一幅仕女图,像是红叶题诗之类。另一幅友人名之为归隐图,一高士在驴背上断流而渡,一琴童岸上看着发抖,神情毕现。这一小品,曾经给他看过,他笑着说:“境界还好,笔弱些。”
我与心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平他的恭王府,恭王府的海棠最为知名,当时由吾友启元白兄陪我们几个朋友去的。王府庭院深沉,气派甚大,触目却有些古老荒凉。主人在花前清茶招待,他因我在辅仁大学与美术科主任溥雪先生相熟的关系,谈起话来甚为亲切。雪斋是心畬从兄,这两位旧王孙,同负画苑盛名,兄清癯而弟丰腴,皆白皙疏眉,头发漆光,身材都不算高。
心畬渡海来台,我们始相见于台大外文系英千里兄的办公室,道途辗转,不惯海行,颇有风尘之色。我陪他参观中文图书馆,甚是高兴,以为不意台湾孤悬海外,居然还有这么多藏书。我告诉他这些书都是福州龚家乌氏山房的收藏,早年台湾帝大买来的,他笑着说:“这不失为楚弓楚得。”后来他便时向我借书。
约在甲子春夏之交,大千兄在日本带给我一本他画的册页,甚精。他听说了,急于要看,因告诉目寒兄,后日同在某家宴会,务必带去。届时我带去了,他坐方桌前,正为一群人写字。看我来了,就放下笔,欣然将册子接去,边看边赞赏。翻到最后空页,拿起笔来便题,不曾构思,便成妙文:
凝阴覆合,云行雨施,神龙隐见,不知为龙抑为云也。东坡泛舟赤壁,赋水与月,不知其为水月为东坡也。大千诗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与诗,是耶?非耶?谁得而知之耶?
寥寥六十来字,超脱浑成,极切合大千气度。尤妙者,所谓“是耶非耶”语气,好像是受大千的题语而触发了灵感,因大千是册最后画的是他日本侍儿山田女史的像,题云:
画成既题署,侍儿谓尚余一页,兴已阑,手亦倦,无暇构思,即对影为此,是耶?非耶?静农何从而知之耶?
是耶?非耶?已无从起心畬而问之矣。我曾与大千谈到心畬的捷才,他也佩服,因说昔年同在日本时,他新照了一像,心畬看了,就立刻题了一诗:
滔滔四海风尘日,天地难容一大千;恰似少陵天宝际,作诗空忆李青莲。
这样真情流露。感慨万端,不特看出他两人的交情,并且透露了他两人以不同的格调高视艺坛的气概。我想他这种感情,必是久蓄胸中,一旦触机而发,绝非偶然。可悲的,大千投老归来,心畬竟先返道山。今则两人俱归于寂灭,余写此回忆,虽平昔琐屑,实深怀旧之感。
(摘自《台静农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版,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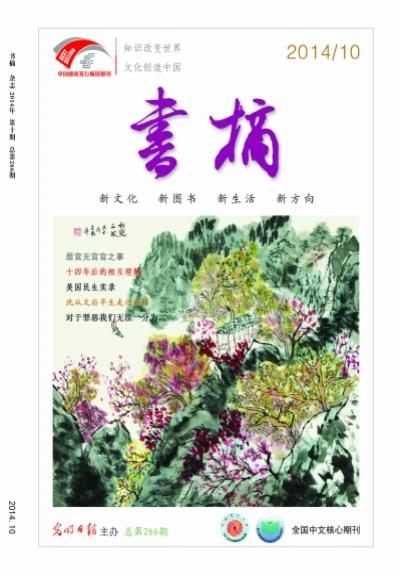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