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人政治”,托克维尔的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能马上会被人想起,自前年该书因一位政治要人的点赞而声名烜赫以来,书中描述的“作家干政”现象,也引来无数关注。
把政治当文学玩,托克维尔以为这是法国才有的现象,因为同期的英国就全不是这个样子,在那里,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也就是说,思想、理论与实践是相互结合、彼此检验、共同促进的。托克维尔当然不会想到,在他说完这些话半世纪后,与欧洲相隔遥远的东方,一个国家的一位海军将领,对另一个国家的一位海军将领说了一段与他意思相仿的话语:“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
这是1894年,天朝上国大清被东亚新强日本打败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给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致了一封劝降书,直陈中国之败乃在“文艺”。大清上下,有没有人听懂伊东佑亨在说什么呢?
政治的“文学”或“文艺”化误国,误在何处?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战国策派”,对此有深刻省察。
抗日战争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一些教授为主体组成的“战国策派”,对国家危亡有切肤之痛。他们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强国对强国的决斗、强国对弱国的并吞”的残酷现实,强烈希望国人振作猛醒,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
“战国策派”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此提倡从事实而非从道德出发的世界观,“国际政治是‘非道德’(amoral,不是‘不道德’immoral),一切幼稚的善恶观念必须打破”,“大政治是以事实做根据的:国际既不能避免战争,我们唯有以武力维护安全;国际既没有公理、法律、道德,我们的算盘只有国家和利害”。
令“战国策派”忧心不已的,是尚武精神在中国的没落。林同济、雷海宗都曾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主导阶层——“士”的精神品格,两千年间有很大变化,经历了由大夫士到士大夫的演变过程。这是两种极为不同的人群,林同济说,西周到春秋前期的士,是爵禄世袭的,是有战斗训练的,是有专司的职业的,也就是说,是贵族的、武德的、技术的。但到孔子之世,这一阶层就已走入末运了,再经过战国时代的剧变,到了秦汉,中国的社会政治,已变为大一统皇权类型,也就是“大夫士”之一物渐次变为文人化、官僚化,而形成两千年来“士大夫”的结构了。雷海宗说,“士君子”是封建时代对士族阶层的尊称,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次的荣誉职务,在这种风气下,君子锻炼出了毅然不屈、慷慨悲愤、光明磊落的人格。但到战国以后,这种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逐渐消失,出现文武对立,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半流于粗暴无状”,而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传统。
与大夫士相比,士大夫的性格特点、理想追求,完全变样。概而言之,是两点:一为官僚化,陈独秀说,把中国士大夫的骨肉烧成灰,里面都可以发现“做官发财”四个大字。二为文人化,不再学习和懂得射御之事,成为专事苦读诗书之徒。也就是说,“大夫士是贵族武士,士大夫是文人官僚”。由此又派生出士大夫阶层的以下特点:
一是重宦术而非技术。大夫士是会做事的,通晓各种社会事务,而士大夫是从战国游说之士而来,鼓唇摇舌只为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所谓“宦游”即“游于官”而非如大夫士那样“游于艺”也。“由封建的士到当今的士,便是由技术到宦术,便是由做事到做官。做事是生产,是‘创造’。做官是消费,虚耗,是‘反创造’。中国之整个政治之所以糟糕,整个文化之所以僵化,关键就在这里,始则政府人员,继则社会人士,上上下下,都不想做事,只想做官,不晓得做事,只晓得做官”。
二是重书本而非实践。“中国的书本头脑是一种整个的宇宙观——一种文字迷的宇宙观……他不能直接念及现实,他失去直接看到现实的本能。所以论到治河水利,历代文人的建议,几于千篇一律,总脱不出大禹治水行所无事那一套”,“中国政治上最大的毛病,就是这种文字迷的假信。西方人办事,言论只是实行的起点;中国人办事,言论乃是一切的终点”。这种书本主义、只说不做的习病,“在官场中发达特甚。我们有个专有名词,就是‘做官样文章’”。
三是重道德而非利害。士大夫阶层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文治而非武功的世界,文是王道,武是霸道,“力之一事,自他们看去,不但在道德上是‘坏’与‘恶’,并且在实际上是‘无效’和‘无用’的”,这种“德化第一”主义,在林同济看来,“无容讳的成为一种弱者的自慰语,无力者的自催眠”,大难临头时还在念念叨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现实利害面前不免沦入苍白可笑,“敌至城下,亦竟或诵经赋诗而图存。数千年不讲国防,一旦失去东四省用瞠目不解其理,不解为什么此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森严世界里,竟会有人来犯天下不韪以破我行政土地的完整。惊愕之余,乃仍在那里梦想欲借公论以克暴力,喊正义以动邻国”。
这些特点决定了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并无应付变局的能力。林同济把这种现象,称作“文人政治”。官僚化、文人化的士大夫阶层,不仅没有血性、缺乏尚武精神,在该担当时不敢担当,而且习惯于以道德论世,对经世致用一窍不通,对如何解决国家难题没有办法,这使他们在该担当时不能担当。雷海宗说秦汉以降,中国的智识阶级即士大夫们大部流于文弱无耻,无事时奔忙于“鸡虫之争”,大难来时则“惊得都作鸟兽散”,乃是典型的伪君子面貌,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
社会中坚阶层的特质决定国家性格,也决定国家命运。“战国策派”认为上千年来中国伪君子遍布,结果是国内文弱之气蔓延,宋明最后都不抵外敌入侵而国破政亡。在国家危难之际,士大夫阶层不仅不识大体,沉迷于党争而不管国家死活,还丧失原则和立场,动辄卖身倚靠。雷海宗总结士大夫阶层误国祸国的方式有三:一是结党误国。典型如东汉末的党祸、宋代的新旧党争、明末的结党,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二是清谈,逃避现实。魏晋时代,胡人已把凉州、并州、幽州大部殖民化,内政与民生也到了山穷水尽之时,负政治责任的人与很多在野的人仍在谈玄。三是做汉奸。刘豫、张邦昌、洪承畴都是进士出身,投身他人时,毫不为耻。
“战国策派”对中国传统及士大夫群体的批判,今天看来有些过激,未必全然合乎历史事实,但总体来说又是有针对性,因此又是有建设意义的。
做事难,并非难在事难办,而是难在一人办事、十人掣肘,另外还有百人在边上说风凉话,等着看你出洋相。干得多不如干得少,干得少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挑刺的。中国之所缺,正在于以实心“做事”者少;中国之所滥,正在于以虚言“做人”者多。雪珥(《李鸿章政改笔记》一书的作者)前些年辗转于文字场与生意场之间,现已完全放弃生意而倾心于晚清改革史研究,对晚清时弊及其由来后继多有深刻洞察。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发展前行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学性浪漫想象与现实政治可行性混沌不分,普遍性地急功近利,期盼一夜暴富、一举成名,不耐烦裱糊的慢工细活,以为推倒重来,换上某一“主义”之蓝图,必能造就摩天大楼。于是,墙倒众人推,人人皆成拆房之专家,你方拆毕我登场。结果,中国经常性面对的局面,是制造一个“主义”,生产一个理论,忽悠一个愿景,什么都可以许诺,就是不能说如何实现。人人迷信所谓“主义”,以为万能灵丹,其结局必然是来回折腾,徒耗国力民力。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托克维尔的法国,“战国策派”的中国,在这一点上多有相通,那就是对社会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偏好抽象原则和高上理念,一味沉浸于说出来的话是不是“美好”、“正义”,在道德上是不是“高尚”,而不去追究所说一旦付诸实践,到底可不可行,行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托克维尔认为这是法国人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政治毕竟不同于文学,后者可以天马行空、越虚构越优美,但政治是要看结果的,不从技术环节考虑利害得失,那越美妙的思想和理论,操作起来就可能越是祸害无穷。现实是,中法这两个国家,近世以来所遭之难,也确比其他大国为多。这恐怕不能一味归于“外国欺压”吧,国家内部精英群体的状态和表现,也干系重大啊。这种缺失与弊端,就中国而言,直到今天仍然时有表现。
(摘自《读书》2014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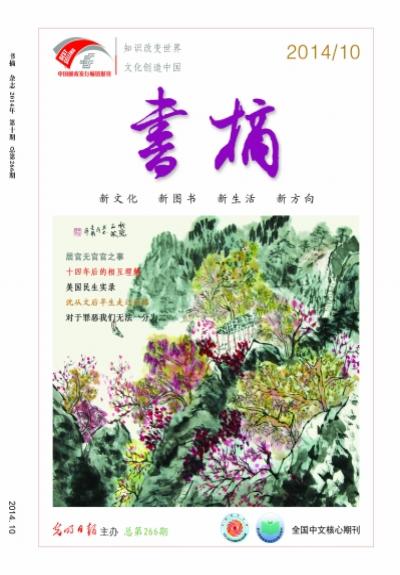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