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自然的花草树木如何在寂静中生长;
看日月星辰如何在寂静中移动……
我们需要寂静,以碰触灵魂。
——特蕾莎修女
“人类终有一天必须极力对抗噪音,如同对抗霍乱与瘟疫一样。”这是诺贝尔奖得主暨细菌学家罗伯特·柯赫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警语。历经一个世纪后,这一天已经比先前近得多。今日,宁静就像濒临绝灭的物种。城市、近郊、乡村,甚至最偏远、辽阔的国家公园,都避免不了人类噪音的入侵,而在洲际之间往返的喷射机,也使得北极无法幸免。人类的历史已经走到一个重要的时刻:如果我们要解决全球的环境危机,就必须永远改变现今的生活方式。我们比以往更需要爱护大地,而寂静正是我们与大地交流的重要管道。
寂静其实是一种声音,也是许多、许多种声音。我听过的寂静,就多得无法计数。草原狼对着夜空长嚎的月光之歌,是一种寂静;而它们伴侣的回应,也是一种寂静。寂静是落雪的低语,等雪融后又会化成令人惊讶的雷鬼节奏,琤琤瑽瑽地让人想闻声起舞。寂静是传授花粉的昆虫拍扑翅膀时带起的柔和曲调,当它们为了躲避一时微风小心翼翼在松枝间穿梭时,虫鸣与松林的叹息交织成一片,可以整天都在你耳边回响。寂静也是一群飞掠而过的栗背山雀和红胸?,啁啁啾啾、拍拍扑扑的声音,惹得人好奇不已。
我聆听世界的声音,这也是我身为声音生态学家热爱从事的工作。除了南极洲还没去过以外,我在各大洲都录过音。这些录音被用于许多地方,从电玩游戏、博物馆展览,到自然风格的唱片、电影音乐和教育产品。我录制声音已超过二十五年,各种自然环境都尝试过,我的声音图书馆藏有多达三千GB的声音,包括蝴蝶鼓动翅膀的声音,瀑布如雷的轰隆声,子弹列车如喷射机般呼啸而过的声音,一片漂浮的叶子细微的声响,鸟儿充满热情的鸣啭,还有草原幼狼低柔的咕咕声等等。我热爱聆听,胜于说话。聆听是一种无言的过程,可接收到最真实的印象。
尽管我录制各种声音,但专长是那些静谧的声音。这种声音非常细微,人耳几乎听不到,但只要学会仔细聆听,也不是完全无法掌握,而我正是个会仔细聆听的人。
我很高兴来到田纳西州,享受自科罗拉多以来第一次遇见的山脉,也很高兴展开拖延许久的追寻。我的旧福斯小巴就像我的田纳西猎犬一样,嗅闻出些许的和平与宁静。我真的等不及要下车!等不及让双脚亲吻大地,跟随约翰·缪尔的脚步穿越美国,或许能踏上他先前走过的地面,聆听他笔下清凉山溪所发出的“大自然的最丰富言语”,这是缪尔在一八六七年写的话。
自从我小心慎重地开始阅读缪尔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著作之后,他就一直是我迫切渴求的精神导师。缪尔显然是利用当时现有的技术记录自然声音的专家,而他的聆听功力以及捕捉大自然里多种交响乐曲的本事,令我震惊。我贪婪地阅读他的《发现荒野八书》,同时有系统地把每个有关自然声音的描述输入可搜寻的数据库,然后分析他的观点,希望找出他最喜爱的主题及经常聆听的地点。我决心弥补他的文字及我的了解之间的差距,于是开始实际追随他的步履。我“在四月一日左右”到约塞米蒂,留着胡须,甚至尝试他在荒野里吃的素食,尽我最大的努力体会他的精神,跟他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自然聆听者。他把山谷与河流描述成乐器,把自然之声形容为音乐,有时还会搭配地震重新排列由大花岗圆石所构成的音符。缪尔打开了我的耳朵,让我能把自然当成音乐聆听。
空气是翅膀留下的音乐。万物都在音乐中舞动,谱曲。老鼠、蜥蜴和蚱蜢一起在土洛克的沙蒂上欢唱,与晨星共鸣。
缪尔最常描述的声音是水。他是这样描述海拔两千四百二十五英尺高的约塞米蒂瀑布:
这高贵的瀑布拥有山谷里最丰富和强大的声音,它的音调变化万千,有时像风自活橡树光滑叶片间吹过时带起的尖嘶声和沙沙声,有时像松林里温柔细致、令人安宁的声音,有时又像是在山巅危崖间冲撞怒吼的狂风与猛雷。有时硕大的水块会在危崖表面与两块突岩上的空气相遇,在冲撞与爆裂下发出不断回响的轰隆低音,如果情况理想,五六英里外就听得到,一块突岩在我们脚下,另一块在它上方大约两百英尺处。这些如彗星般巨大的水流在高水位时会持续不断出现,而爆破般的低沉音调则是狂悍地时断时续,这是因为除非受到风的影响,否则大多数沉重的水流会从悬崖表面激射而出,所以会飞越过突岩,直冲而下,但在其他时候则会撞击突岩,轰然爆发。偶尔整个瀑布都会摆离危崖表面,然后突然间又整个冲上去,有时则会如钟摆般左右摇晃,造成变化万千的形式与声响。
缪尔首次聆听水声,是在田纳西州蒙哥马利市外的清凉山溪畔。据我所知,自一八六七年起,就没人曾刻意到那里像缪尔一样专心聆听,或同时在内心回荡着缪尔的话语。于是我决心找到那条溪,追踪它的声音。
隔天早上,在美丽日出的橘色光芒下,我察觉到空气中有一股熟悉、辛辣的草香,就像……就像我小时候在荒僻林地漫游时闻到的落叶味。
大约在诺克斯维尔市外三十八英里处,我从六十三号州道出口离开,却发现自己来到一块商业区:几乎每个主要山谷都有一条道路通过,交通声会在丘陵间回响。我知道我在横渡水牛河时错过了原本应该转弯的岔路,于是打了U形回转,转到诺玛路上。
诺玛路逐渐变成石子路,比较危险的路面已铺上柏油,总宽度单是运煤大卡车走起来都很勉强,更别说多了在反向“车道”上行驶的我的这辆老福斯。看到一个写着“昆布兰步道”的路牌时,我就知道自己开过头了。好吧,现在我得到河里冷静一下,冲掉身上的尘土。新河的河道宽大,流速缓慢,高大雄伟的树墙围着池底的岩石,形成美妙的自然露天剧场。我潜入较深的水池,观察昆虫把这条河流当高速公路般使用的情形,偶尔会有觅食鲈鱼飞溅的水花形成的涟漪,同时也听得到卡车声在枝叶茂盛的峡谷间回响。我在河岸的小圆石之间看到闪着虹光的小石油坑。
把身上的水滴干后,我仔细研究地形图,看接下来该往哪里走:沿着朝东方的侧谷往上开到蒙哥马利分岔口,往栖息耳泉的方向走。沿路一个写着“野生动物管理区”的路标,让我多了点信心。
这个受到保护的侧谷延伸出数个小凹谷,形成天然的露天小剧场,四周环绕着橡木、山胡桃和枫树。山谷中央有一条小山溪,一定是它!就算它不是缪尔笔下清凉的田纳西山溪,肯定也跟它同出一源。
我把车停在高地,以免引擎冷却时“噼啪、咔嗒”的声音妨碍我聆听。我扛着录音设备,徒步走下布满尘土的路面,朝山溪的呼唤声走去。我从突出的树叶间瞥到水池和各种各样的石头反射着最后的阳光。走了几分钟,一条美丽的小溪出现在眼前,我刚要到水里架设设备,一只画眉鸟就发出竖琴般的歌声,仿佛在给予这一刻最后的祝福。我立即停步不动,深怕惊走这只跟知更鸟差不多大小、天性害羞的小鸟,然后悄悄把三脚架架在浅浅的溪水里,按下录音钮。
然而,我的计划还未能实现。一辆美国国家煤矿公司的卡车开进来,停在离我大约一百码的上游处,像口渴的大象般开始吸水。原来这里是道路洒水车取水的地方。这个口渴的怪兽让小山谷充满刺耳的机械声。我的音量计读数猛升到七十一加权分贝——这种事竟然发生在野生动物管理区,简直不可思议!
我放弃任何录音的想法,走过去跟卡车驾驶员说话,他衬衫上的名牌写着“蓝帝”。他告诉我,他一次取四千加仑的水,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然后别人会接手继续做十二小时,以便减少路上的灰尘,这些水也用来补充煤矿场的水池。
“没有水,就没有煤。”他边说边打量我的衣服:汗湿的褐色T恤、晒白的卡其猎人背心、帆布短裤和Teva牌户外运动鞋。“你在这里做什么?UPS?”蓝帝肯定以为我是UPS快递员,身上穿的是适合高地的制服。
我告诉他,我想录制鸟的声音。
他告诉我,每次补充水大约要十五分钟,他一个晚上要跑七到十二趟。这次的水是要送去补充煤矿场里快干掉的水池。“他们没有水,就不能处理煤。小竖坑,一周一两次没什么用。这条溪的水位通常在八九月以前不会这么低。”我把这视为意外的录音消息,因为这应该比较符合缪尔在九月十二日造访时的情况。
噪音加上他的口音,让我无法立即了解他的意思,经常会落后一句。现在我才听懂他刚才在问我是不是要拍摄飞来这条溪的鸟。
“不是,我来听约翰·缪尔一八六〇年代在他日志里写到的声音,有点像是在做历史旅行。”
“这样啊。”
“那么,”我问,“国家煤矿场离这里有多远?”
“大概三点五英里,顶多四英里。”
这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完全行不通,因为就算我能趁蓝帝换班的短暂空当录音,在那段空当里也会有另一种噪音:人类为取得能源而钻入地底深层的嗡嗡声。
“你知道蒙哥马利怎么走吗?”
“就在这里,就是这里。这条溪就叫蒙哥马利溪。这个桥架下的小溪,叫作罗奇溪,很漂亮的溪。到这里为止都很漂亮。”
我们看到水溢出卡车顶。“我加满了,”蓝帝说,跑过去关掉帮浦。
“哔——哔——哔——哔”,他按喇叭警告我,他要倒车,接着就掉头开回矿场。
我按照蓝帝的建议,沿罗奇溪往山谷上方走,假想自己正在追随缪尔的脚步。走在溪水里,我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不断变化。没有两颗岩石是一样的。任何一道水流都不同。每走一步都是一个新的组合,新的音符。在不同的时代,例如缪尔的时代,我有可能沉迷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但是在国家煤矿公司第十一号矿场自远方传来的噪音下,我几乎无法心平静气地聆听。缪尔在离我此刻位置很近的地方,于日志里写道:“在大自然中,以山溪的言语最为丰富。”如果他得负责写维基百科里有关生态学的条目内容,以今天的情况,他会怎么写呢?
我倒是知道缪尔写了下面这一段话:“心灵的感官肯定比身体的感官优越得多!”我希望他是对的,因为我们未来得靠来自心灵感官输入的野生情报,度过下一个千禧年。
我得在星光出现前走出这里,因为单靠星光,无法安全走过这些滑溜的岩石。在回到我的老福斯旁,等待茶水煮开时,我从缪尔一八八八年七月写给他太太露依的信里汲取勇气:“晨星仍一齐歌唱,而这个尚未成形一半的世界,每天都愈见美丽。”
没错,这也是我心里的想法。这世界正处于生成之中,它“尚未成形一半”。在噪音污染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现在正是我们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
(摘自《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商务印书馆2014年4月版,定价:6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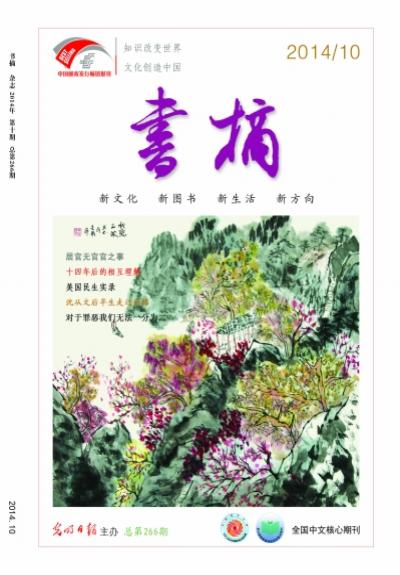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