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时间,好莱坞都是资本主义的符号之一,罪名是以梦幻麻醉人民。现而今好莱坞仍被描述为“梦工厂”。做梦要有相宜的氛围,所以最好在电影院里,封闭在黑暗之中,只余银幕上的世界,与现实全不搭界。大约是入梦的难度越来越大,现在的观众对观影环境的要求与时俱进,声音画面的高保真之外,对座位的舒适也有要求。只有小孩不讲究这些。我那一代人儿时就更不在意,我小时最起劲的是看露天电影。
在城市里,放露天电影的往往是那些有大院有操场或大草坪的大单位,届时各出口就有人把着不让随意进出,不过这要比没票混进电影院容易得多,会翻墙就行。摸不准具体的放映地点也没关系,路上的人大多都在往那儿去。放电影的地方照例人声鼎沸,再大的影院也容纳不了这些人。大呼小叫此起彼伏,有占了位子喊熟人快来的,也有一群人同来而走散了在高声寻人的。人群中有一张桌子崛起,上面是放映机、电影拷贝外加放映员的热水瓶大茶缸。差不多都是在这位置,有一竿子竖起,上有一瓦数很大的电灯泡,入座、散场,就指着它照明。这里当然没有对号入座一说,都是自带凳子,扛椅子过来的极少,太沉。凳子有高低,自有维持秩序的指定矮凳靠前,高凳排后。为抢占有利地形,自然要提前入场,往往半小时之前,看电影的氛围已开始酝酿。为座位起争执也是这氛围的组成部分,闹到大打出手也是常事。观众是现成的,放电影之前先来一场全武行的围观,也算有时代特色的一种暖场吧。
要到那大灯泡灭了,人声才渐次低下去,四周黑下来,并不是全封闭的黑,天好的时候,头顶上明月皎皎,星光烂漫。左近的三两点灯火则总是不灭的。还就要好天,月黑风高就很不保险,风大了吹得银幕如同满帆,图像整个变形;星月潜踪了,保不定来上一场雨。期待了很久的一场电影,看了一半让雨搅了局的,也不是没有。即使老天爷赏脸,中间的停顿还是必须,因为往往只有一部放映机,换片子的当儿,那盏灯又复亮起,电影也被分成了上半场下半场。若正当节骨眼上,唿哨声、不满的倒彩声立马响成一片。
现在想来,这样的环境里想要全情投入,似乎不大容易。然而也就将就着看了,到紧张或动情处还真安静,电影的声音之外唯余放映机的轧轧声。我每在此时意识到头顶上的那道光柱,光柱里的内容随季节变化各各不同:夏天是飞虫,冬天是众人口中哈出的热气,下小雨时则是透明的雨丝。有一样是不分天候季节的,即是烟民嘴里喷出的烟雾。
露天电影的最后一幕是散场,我对“天下大乱”一词最具体生动的感受即产生于此时。大呼小叫声又起,比开场前加倍,大人在找不安于席、跑没了影的小孩,有人在寻丢失的东西,叫喊里杂着愤愤的詈骂和威胁语,无非是回家怎样收拾之类。也有找着了当下就施以惩罚的,于是必有小儿号啕大哭之声。空场上不可能像电影散场时的大放光明,赖有很多人都备着照路的电筒,一时间全都点亮,无数缭乱的光柱中是幢幢的人影,精力过剩的顽童恶作剧地四处乱照,少不得有被晃了眼的,当然就又有高声的喝斥:“照!照什么照?!”
不知露天电影在城里是到何时成为过去的,我印象中到上世纪90年代还有。不过已不是单位组织,大多是在公园一类的地方,属游园的余兴节目,招徕游客的手段,而非观影的主流形式了。最后一次看露天电影好像是1991年的事,中山陵音乐台,在报纸中缝里看了消息去的,纯粹是怀旧性质。放《简·爱》,偌大的场子,稀稀拉拉坐了几十个人,气氛全无,我看了十几分钟就撤了。
走进电影院
据说原先南京最上档次的电影院是大华,1949年以前叫大戏院,后来是否就以放电影为主,改称电影院,我不知道。那时的影院与剧场界线模糊,似乎都是多功能,放电影之外时常开会,文艺演出。开会、演出要有台上、台下,而电影院都是有“台”的,银幕架在舞台之上。直到80年代,还常有一些单位借电影院开年终总结大会之类,开完会后,正好因势利导,招待一场电影。现在新起的影院则是地道的影院,再无舞台一说了。
小时没怎么去过“大华”,印象中最豪华的影院是“曙光”。很长时间里,“曙光”是南京城唯一一家有宽银幕的影院,其他影院放宽银幕电影都有些勉强,难怪它一度以“宽银幕影院”相号召。过去的影院不像现在,银幕无遮无拦,通常都有一层帷幕遮掩着,要待乐声响起,幕布才徐徐拉开,把看电影这事搞得挺隆重。“曙光”是紫红色的丝绒帷幕,拉开后里面还有一层薄纱,缓缓向两边移动之际,影像已透过薄纱影影绰绰在银幕上出现。
我于此时常不期然地想起“撩起神秘的面纱”或“温情脉脉的面纱”之类。只是那时放的电影既不“神秘”也不“温情”,都是剑拔弩张的“斗争”气氛,上面的人横眉立目,好像随时准备喊口号。有段时间,放片之前放幻灯片,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等等,仍然是幕布徐徐拉开,制作极粗陋的幻灯片叠映在丝绒、薄纱上,很不协调——放映的内容变了,放映的方式还是照老规矩。
那时的片子极少是宽银幕的,我们第一次见识宽银幕电影,好像还是拜朝鲜之赐,大概就是《卖花姑娘》。我对所谓“苦戏”没兴趣,不过宽银幕电影总得新鲜一把吧?影院里能让人新鲜一回的几近于无,家家影院都闹饥荒,颠来倒去就那些片子,记得《创业》我就看了不下三遍。饶是如此,影院的上座率与今相比却好得多,有打着受教育旗号的单位包场撑着之外,亦因日子过得实在单调。
“文革”结束后是电影院的黄金时期。只要是故事片,不拘是解禁的还是新拍的,一概大受欢迎。当场票几乎买不到,曙光前面偌大一片空场上,总有许多人在等退票,倘是热门的片子就更不得了。所谓热门,现在的人难以想象,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买预售票的人可以排成上百米的长龙。此所以许多与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也大放电影,比如体育馆。有一阵,放电影似乎成了五台山体育馆的主业,一侧看台架起银幕,观众坐在另一侧隔着球场遥看。
看电影而频频鼓掌,好像也是那时特有的情形,也可见上世纪80年代初大家高涨的情绪。《甲午风云》里邓大人出现,大鼓其掌,这是在欢呼邓小平复出,也就罢了。高潮处鼓掌,有出彩的对白,也鼓掌。彼时尚无“恶搞”一说,都是投入式的鼓掌,学生场气氛就更热烈。有次大概是南大的包场,满电影院都是大学生,看印度片《大篷车》,结尾处男主人公暴揍恶霸,大鞭子一鞭鞭下去,抽得血肉模糊,居然也掌声一片。
惜乎好景不长。80年代后期,已是盛景难再,到90年代,电影院好日子就到头了。“曙光”也露出下世的光景,门庭若市一变而为门可罗雀,搞出通宵电影,大概就是不得已的救市之策。三四场电影一起放,青菜萝卜搭着卖,捆绑销售的性质。起初颇有市场,大概是新鲜,算起来票价也便宜。渐渐就不行,去看的多是谈恋爱的——夜里没地方,影院也算是个去处。看得哈欠连天,看一阵睡一阵的也大有人在,清晨散场时,出来的人一个个蓬头垢面,面无人色。
电影的遭冷落,一大原因是录像机的出现。电影片源太少,限制太多,各种渠道进来的录像带则是花样繁多。于是电影院纷纷附设录像厅,大放投影电视。一时间,附庸蔚为大国,看录像倒成影院的主业了。那以后则有游戏机的入侵,“曙光”一楼的大厅、二楼的空地似乎都被游戏机占据,一进去就震天价响;再进到放映厅里,又安静下来,观众席上没多少人。
我最后一次进“曙光”之前,大概已有半年时间没看电影了。那天下午是到对面的书店买了书,想久不看电影了,一时兴起,就买了张票进去。看的是什么已忘了,只记得冷清得很,楼下只零零落落坐了十几个人,多是成双作对,卿卿我我,对银幕上发生的事似也不怎么关心。
因那场电影看得败兴,以后很长时间,几乎绝迹于影院。也不知过了几时,忽一日,又从那一带走过,发现“曙光”已拆了,一地的瓦砾。
旧时美人
我所说的“旧时”特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时间里“美女”、“美人”这样的字眼其实不大出现,出现了也不是褒义,因为有“封资修”的嫌疑。然而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口里不说,心里却有,只是美的概念因人而异之外,还有时代烙印。那个时代大家心目中的美人,有些特别。
任何时代,影星都兼职大众情人,革命年代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自50年代起,共和国的审美趣味中也有一种乡村导向。不拘背景是不是农村,女主角身上大都透出乡野的美。规定得劳动人民唱主角,工农兵当中,工人、当兵的大都有农村的背景,倡导这样的美,也是无怪其然。
《柳堡的故事》里的二妹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的孔淑贞,《刘三姐》里的黄婉秋,《阿诗玛》里的杨丽坤……一概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
与“土”相对的是“洋”,洋气的影星也不是没有,但大多只能附着在那些反派或可疑的角色身上,其中最“洋”者,乃为女特务。电影中的女特务在我这样的观众心目中唤起的绝对是一种暧昧的情绪,选来演这类角色的,通常长相、装扮、神情都较城市化,王晓棠,还有个叫师伟的,就是。既为美女蛇,其毒可知,其貌美亦可知,而且女特务之“特”,也常见于其一身妖气,不管着美式军服还是其他显身段的便装,带些诱惑性是一定的,因此“洋气”有时也通于妖气。偏偏不少人就被这妖气所惑,《孤胆英雄》里王晓棠演的女特务最后被击毙,我就暗自怅然久之。由银幕造型的诱导,很多人有意无意间都把“洋气”和女特务联在一起。初一时班上有个同学的妈妈很好看,高个子,瘦长脸,穿衣有些讲究,头发有点卷曲,也不知是自来卷还是稍稍烫过,我的一个哥们儿有次就悄悄对我说,某某他妈像个特务。说时神情诡秘,回想起来,其中也许还掺着恋慕的意思吧。
尽管女特务勾魂,毕竟是坏人,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恋慕,是对自己甚至也不能承认的。我那时的梦中情人在“土”、“洋”之间。其身份应该叫革命青年,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早春二月》里的陶岚,《大浪淘沙》中的谢辉。扮相、衣着,不像二妹子们那么“土”,却也不像女特务那样“洋”到近于“妖”。
其实《早春二月》、《大浪淘沙》这样的电影在当时是不够主流的,前两个女主演的长相也不主流,却还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那样的美,与今天的“美人”标准,也早已不相干了。我不知道现在再到电影里去看“革命美人”,会是什么反应。
(摘自《旧时勾当:提前怀旧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4月版,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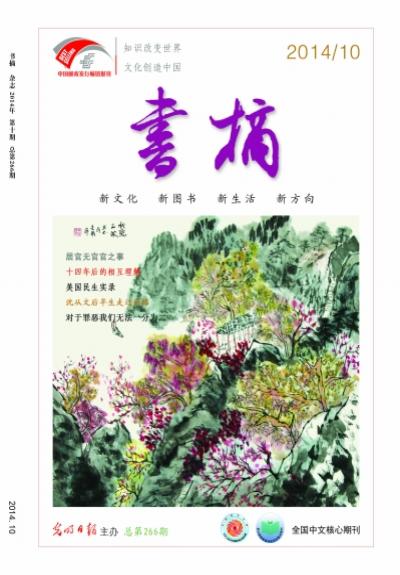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