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庄是西北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荒寒闭塞,没有通电,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吃水靠接天雨。年轻人纷纷选择进城打工,老幼孤寡艰难留守。为了切实解决农村群众的居住问题,县委、县政府下达了关于危房改造的通知。
一大早,老村长就在高音喇叭上通知开会,“家家必须来一个人,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利益,是好事。”络绎不绝,到十点钟,一共来了五十几号人。老村长说:“除了念书的娃娃,在村里的人来了三分之二了,危房危窑改造哩,你说指望他们能做个啥么?”老村长把文件递给我,是县委、县政府关于危房危窑改造的通知。
老村长把村部两间房子的会议室门打开,张六给给一笑说:“老黄瓜,开会议室做啥,你还想坐在台上耍排场啊,准备没准备都得讲两句是不?蹴到院里说说算毬了,窑里阴得。”大家都靠着墙蹴下去,老村长说:“文件你给念念。”
我清清嗓子开始念:“危房危窑改造是关注民生情怀的德政工程,是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工程,为了确保农村危窑危房改造工作顺利开展,县上成立了由县政府主管副县长任组长,经发、住建、财政……”
张六插话说:“念这些做啥?白话么,没用,你挑着拣着往下念。”
“为了切实解决农村群众的居住问题,按照《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要求,我县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与乡镇干部,对全县农村危窑危房进行了详细普查……”
老周说:“这也不用念,你再往下看。”
张六说:“你就念国家给补多少钱。”
“在资金补助上,低保户、五保户建房标准每户补助一万三千元,其他户建房标准每户补助七千元,C级危房建房标准每户补助五千元。对新建的实行‘1+2’(每户补助一万元,每人补助二千元),改造的实行‘5+1+5’(每户补助五千元,每人补助一千元,每孔窑房补助五百元)的补助政策。同时,为减少困难群众建房负担,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以‘自建、援建、帮建’的方式,发动亲帮亲、邻帮邻,投工投劳……”
老顾插话说:“‘自建、援建、帮建’的方式,发动亲帮亲、邻帮邻,投工投劳,这就是坐在办公室想出来的么,现在人死了都抬不出去,就凭这些老胳膊老腿,扛得起个檩条,还是上得了一根椽子?”
老村长说:“让念完再说。”
我觉得有一段还需要念一下:“坚持‘政策支持、政府引导、农户自愿、便于发展、综合配套’的原则,在建设住房的同时,综合配套了水窖、圈棚、温棚、沼气池,配备了太阳能,新修道路,绿化村庄……”
老周说:“这些不要念了,虚头巴脑的念那做甚?!”
我又挑了段继续念:“家庭人口少于三人的不超四十平方米,三人以上的不超六十平方米,需提供:(1)户口本及户主身份证复印件,并带原件核实。属民政低保、残疾、五保户的,需提供残疾证、农村五保供养证、低保金领取证的复印件,并带原件核实;(2)和改造前的危房照片一张;(3)……”
下面开始不安分,就像调皮的学生娃,喊嘁喳喳的。
老村长说: “一个个喔毬德行,好事么,当公家害你们哩?前些日子镇上组织我们去看过改造的房子,红砖红瓦,水泥砂浆,松松梁,三七墙、上圈梁,质量好得很,节能炕、太阳灶、沼气池,洋气着哩。”
老曹说:“没说不是好事,房子咱不能说亏心话,盖得漂亮结实,我亲家家就危改了,抗八级地震哩,住几辈子人没麻达,可不符合实际么,房子再漂亮结实得有人住,没人住这钱不是白瞎了。娃娃们打工小年前后回来,人七日(正月初七)不过就风风火火走了,房子盖得再好一年能住几天?有些娃一连几年都不回来一回。这些娃心都高了,日子瞎瞎好好都不会回来了,娃不回来,我们这一茬人没了,谁回来住,不白瞎了?”
“就是么,我那些娃几年没回来了,说你们好着呢么,回去做啥?你听这话,非得我病了死了才回来?前些天又捎来话了,今年的年让我们到城里过,我给骂了,你那鸟笼子里能过个啥年?!”八老汉在鞋底上磕着烟锅,“狗日的还骂我不会算账,说他们弟兄姊妹几家二十几口人,一来回花销得多少?别的不说,光花在车轱辘上的钱有多少?你们两个一来回能花销几个?有花在车轱辘上的钱你们吃了喝了穿了不是得了?唉,气归气,理却是个理,算账的事么。”
老周说:“干部,你看看有没有说自己盖了房公家给补助的?”
我摇摇头。
老许说:“椽子、砖瓦、水泥准备下多少年了,要不是娃没回来的心思,我新房子早盖起来了,还等危改?现在木头风吹日晒的都爆口子了,公家要盖房,能不能把我备的这些料卖给公家?”
老村长说:“尽想美事,危改啥都是统一的。”
我说:“你们不住呀,危改后你们住进去多敞亮。”
“我们能住几年?”老拓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土都壅到脖子上了,腿一蹬手一摊走了,到时房子又搬不走,想卖谁要?现在这地方我们住到死没啥麻达。”
张六说:“你看看有没有说在别的地方买房给补钱的?”
我说:“文件上说的是危房危窑改造,不是买房补助。”
老村长说:“啧啧啧,把钱补到城里买房,做梦娶丫头,想得美死咧,给你个舌头你还上肚子哩。”
我哧地笑了,老村长也笑了。
张六说:“咋不能这么想,人家城里人买房子国家不是给补助呢么。”
老周说:“驴拉屎在墙上蹭沟子哩,把你想得洋气的,跟城里人比?”
张六踢了老周一脚说:“你个瞎[尸][从],跟我抬杠?我说得不对?你让干部说,我1987年就进城打工了,2009年回来,二十多年,儿子打工也眼看二十年了,我们父子打工加起来四十多年,不在城里吃,城里屙?挣下钱不花在城里?没给城里上税?咋就成不了个城里人?城里的政策咋就不能享受?我弟的儿子闰生,还不是大学生,兵当得好,转业到城里了,才五六年时间,就分了一套房子。要说在城里的贡献,我父子不比他大?!交钱的时候两口子合起来光那啥金来着……”
黄婶正在纳鞋,头都不抬地说:“味精。”
张六啧啧地说:“你就是猪,光记着吃,难怪像个麻包。”
老周跟了一句:“肉厚了棉,像棉花包子,软和。”
黄婶扑老周来了,老周跳起来边跑边嘿嘿地笑,说:“是你男人说的,不信他回来你问他。”
杏花婶说:“炒肉放点味精就是提味么。”
一婆婆说:“鸡精更提味哩。”
张六一拍大腿说:“对,对,是积金,公积金。”
婆婆说:“不对,鸡精不分公母。”
杏花婶说:“应该分吧,羯羊肉就比母羊肉好吃。”
老村长嘿嘿笑了半天,说,“都回家做饭去,知道个毬!”
老周回来了,给给一笑说:“可不就知道个毬,耍了一辈子的东西么。”
人群哈哈、嘿嘿地笑了,几个女人说:“这些老叫驴(公驴)啊。”
黄婶拿胡基丢老周说:“你要长个尾巴的,打到驴群里都辨不出来。”
老周说:“你肯定认得出来,老黄不比我像驴。”
张六说:“两口子光公积金提出来二十几万,一套房交的连十万都不到,你说哪里说理去?”
老周说:“就是么,城里人有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没咱农民工的份儿么。去年把家里打折了一遍,凑够了首付,去买房,人家要担保,要工资证明,没人担保,干活的老板又不给出工资证明,在银行跟人家求爷爷告奶奶地说了半天,人家一听是农民工,连话都不多说一句。干部,你说么。”
杏花婶说:“啧啧啧,当国家给你补座金山银山哩,就想着到城里买房子。”
老周说:“问题是你要危改,国家补了,还得自己拿钱,再说就是把房子盖起来,不买几样子摆设能住进去?一户下来没十来万出不来么。”
“干部,你们制定政策时想过没?矛盾着哩,说打工是铁杆庄稼,鼓励大家进城打工,人都进城打工了,又把钱投到这里让改造房屋,你说矛盾不矛盾?就说我们张家沟,四十二户,二百多口人,现在家里有人的就七户了,再说门长年累月锁着,晚上孤得都吓人哩!”
张六说:“你是耍笔杆子的么,写个东西,把钱补到城里让娃买房子去,我们都把名签上递上去,危改是好事,可要切合实际么。现在你看得明白么,儿子不回来,孙子就更不回来了,我们这一辈人下场(去世)了,这村子就荒了。”
老村长说:“别嚼牙碴了,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狗看星星——望(妄)想,把名都报了,明年开春就动弹给你们盖宫殿哩。”
八老汉说:“娃在城里买房子逼得人眼里滴血哩,哪有钱往这里花?我不用考虑了。”老顾说:“我也不用考虑。”张六说:“我也不用考虑了。”老村长说:“这么好的政策,一个个福烧的。”
老许说:“政策不能说不好,可没好到地方上么。”
老村长说:“憨子婆娘你家呢?”
赵婶说:“我得跟老汉儿子商量一下,又不是白盖,自己拿不少哩。”
老顾说:“你还用商量,一龇牙,男人钻老鼠洞哩,家里啥事他说了算过?”
赵婶说:“都不要谝嘴,现在谁不是儿女当家,儿子大了,老子罢了。人家都想当城里人,把钱花到这里行么?”
老村长说:“说正经话,回去都跟儿女们商量商量,这么好的政策。”
会就这么散了,女人们都走了,老曹起身要走,张六说:“急着回去吃奶呀?”
“人家给儿子扒光阴哩。”老周说着也走了。
大家也都陆续散了。
老村长说:“你看么,就这么个现状,在城里买房子,难着哩,多少年了,在城里买了房的也就五六户,都漂着呢。买了房子的也是四处拉债,日子紧成啥了,回村子上来借钱。”
又说,“广播上说,全国城镇化率超过52%,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又说另一个数据也不容忽视,2010年中国户籍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为34.17%,这就是说两亿多无城市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不能享有和户籍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均等化方面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想在城里落下去,没有这些,难着哩,国家要解决这些人落下去的问题,也难着哩,这还不住地往城里跑哩。”
是啊,三十年了,城市还没有做好接受他们的准备,可他们的家——农村却已经萧条衰败了。
(摘自《上庄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版,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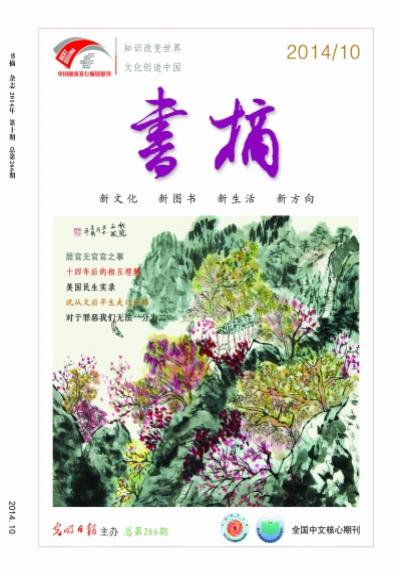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