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皇明名臣记》写到宋濂,有这样一个细节:洪武九年六月,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位侍从学士说:“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他把首席秘书宋濂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为了表示恩宠,希望宋家“世世与国同休”,要他的儿子、孙子都出来做官。一向谨小慎微的宋濂再三推辞,朱元璋亲自任命其长孙宋慎为殿廷仪礼司序班,次子宋璲为中书舍人。宋氏祖孙三代同时在朝廷为官,同僚羡慕为无上荣耀,宋濂感激涕零,常常告诫子孙:“上德犹天地也,将何以为报?独有诚敬忠勤,略可以自效万一耳。”他万万没有料到,正是这一恩宠,带来了杀身之祸。“布衣天子”与“草莱侍从”之间的纠葛,不足为外人道也,人们所知甚少,却很有探究的价值。
宋濂,字景濂,早先居住于金华之潜溪,后迁居浦江青萝山。自幼好学,记忆超群,写诗歌往往有奇语,被誉为神童。稍长,师从儒者吴莱,又对大儒柳贯、黄溍执弟子礼,柳、黄二公却以朋友之礼相待,顿时名声大振,正如万历《金华府志》所说“以文章家名海内”。
金华义乌人王袆,与宋濂有同乡之谊,又同为《元史》总裁。朱元璋认为宋、王二人各有所长,对王袆说:“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宋濂死后,王袆写《宋太史传》,对他赞颂备至:“吾观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气殆前无古人。”王袆对宋濂的描摹栩栩如生:
景濂状貌丰厚,美须髯,然目短视,寻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雪边月下,蝇头之字可读也。性疏旷,不喜事检束,宾客不至,则累日不整冠帻。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间,索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乐。世俗生产作业之事,皆不暇顾。而笃于伦品,处父子兄弟夫妇间,尽其道。与人交往任真无钧距,视人世百为变眩捭阖,漫若不知,知之亦弗与较,纵为人所卖不复恤,而人亦无忍欺之者。用是,咸称为有德之君子。
王袆笔下的宋濂,既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悠游林下品位甚高的名士,又是天真无邪的谦谦君子。
作为皇帝身边的侍从,宋濂十分谨慎检点,有所陈说,毫不文饰隐蔽,坦诚而透明。一天,朱元璋突然问他昨日饮酒否?座客是谁?吃了什么?他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了大笑:昨日朕派人侦视,果然如你所说,没有欺骗我。从此更加信任他的诚实,他却愈发谨小慎微。朱元璋要他臧否廷臣,他列举了一些“善者”,而绝口不提“否者”,解释道:“善者与臣友,故知之;否者纵有,臣不知也。”说得滴水不漏。
作为首席秘书,经常在皇帝身边,知道很多朝廷机密,他却守口如瓶,从不向外泄露。郑晓《皇明名臣记》说:“上喜公善谏,公深密不泄禁中语,有奏,辄焚稿。尝书‘温树’二字室中,或问朝廷事,指二字不对。”对于这样规规矩矩的幕僚,朱元璋是很满意的,当着朝廷众臣赞誉宋濂:“古之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其诚所谓君子乎?匪止君子,抑可谓之贤矣。”
朱元璋驾驭群臣很有手法,即使对于文坛盟主宋濂,也要他在诗文方面甘拜下风。焦竑《玉堂丛语》记录了一则轶闻: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时,朱元璋宴请大臣,宋濂不胜酒力,酩酊大醉。朱元璋竟然要与他比试酒后写诗的功力,自己一气呵成一首“楚辞”:
西风飒飒兮金张,会儒臣兮举觞。
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洋洋。
为斯悦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
玉海盈而馨透,浮琼斝兮银浆。
宋先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
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
一向自诩“专攻文墨”的宋先生,酒醉以后头昏眼花,“下笔字不成行列”,歪歪扭扭写了一首五韵。朱元璋特地叫人抄写这两首诗,送给宋先生收藏,对他说:“卿藏之以示子孙,非惟见朕宠爱卿,亦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也。”其实是在嘲讽他的“文墨”不过尔尔。宋先生也自叹不如:“帝为文或不喜书,召臣濂坐榻下,终日之间,入经出史,衮衮千余言……上圣神天纵,行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诚所谓天之文哉!”
退休之后,他愈加谨言慎行,布衣蔬食,如同贫士一般,埋首读书著述,两耳不闻窗外事。同乡弟子郑楷在《宋公濂行状》中写道:“先生惟刻意为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时去书不观。及致政归青萝山,辟一室曰‘静轩’,终日闭户纂述,人不见其面。戒子孙毋至城市……或谈及时事,辄引去不与语。”邓元锡《皇明书》说他晚年“究心于性命之极,视外物往来泊如不相干。尝曰:‘古人之学,欲心正身修,而见诸行事,今俯仰无愧而已,繁辞复说无谓也。’”他自以为俯仰无愧,闭门读书,不问时事,当然是想避开是非,远离政治。然而政治并没有放过他。
洪武十三年春节期间,朱元璋突然以“擅权植党”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并且宣布取消丞相及其办事机构中书省,然后大张旗鼓整肃“胡党”,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以“胡党”罪被杀,随即株连大批僚属党羽。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宋濂的孙子宋慎为“胡党”牵连,于次年冬处死;次子宋璲也株连而死;他自己也被带上枷锁押解到南京论死。
受到宋濂多年教育,对师父尊崇备至的太子朱标,得到消息,大惊失色,流着眼泪向父皇求情:愚笨如我只有一位师父,请陛下哀怜,不要处死。朱元璋大发雷霆:等你做天子时再哀怜吧!太子听了惊恐不已,跑到金水桥投水自沉。朱元璋听到消息,连忙命令内侍速救,救不起来,统统处死。太子救起后,他喜怒参半地骂道:痴儿,我杀人与你有何相干!太子哭着说:师当刑,儿何忍不死?
一向宽厚仁慈的马皇后异乎寻常的冷静,对皇帝的处置表示异议。张岱《石匮书》记录了这一细节:“宋学士濂常授太子经,以诖误置重辟,后闻,为素食。帝还宫问故,后曰:‘宋先生当刑,祈天宥之耳。’因泣下曰:‘民间延一塾师训子弟,尚始终不忘。宋先生授太子诸王经甚劬,今奈何杀之?况宋先生致仕在家,又何与京师事也?’乃得贷。”
朱元璋刚愎自用,却惧内,太子以死相谏,马皇后站在太子一边,振振有词地劝谏,迫使他打消了立即处死宋濂的念头,改为流放四川茂州(今四川北川、汶川一带)。这种流放并非自由行,而是作为罪犯在兵丁押解下长途跋涉,不论行路还是坐下歇脚,都不能打开枷锁。这样的侮辱与折磨,对于年逾七旬的老者而言,等于要置他于死地。果然,还没有到达茂州,宋濂就在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命呜呼。
宋濂死于夔州是没有疑义的,至于如何死法,却是有疑问的。何乔远《名山藏》说他是自尽的:“至夔,宿野寺,侘傺语曰:‘闻之佛书报应以类,今爽濂也。’其夕,投缳死。”谈迁《国榷》的说法相类似:“至夔州,宿僧舍,叹曰:‘佛书报应以类,何爽也。’夕自经。”多年侍从生涯,备受宠信,居然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从高峰落入低谷,他看作“报应”,与其苟延残喘,不如自我了断,一了百了。谈迁感叹道:“悲哉,仕宦真畏途也。”他的自尽,可以看作对自己侍从生涯的无言否定,令后人百味杂陈。
被太祖高皇帝推崇为“君子”、“贤者”、“纯臣”的宋先生,“不能获于正寝”,方孝孺是耿耿于怀的,却难以直言,在祭文中含蓄地说:“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被誉为“读书种子”的方先生笔底带着感情,为何这样一位正人君子,不能寿终正寝,不能庇荫子孙?
这当然与朱元璋“以重典驭臣下”的治国理念有关。当初他应聘前往南京,献给朱元璋的方略,就是“劝不嗜杀人”。然而太祖高皇帝一生,始终“嗜杀人”,正如吴晗所说:“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甚而至于,连自己表彰为“君臣道合”的“草莱侍从”,劝他“不嗜杀人”的宋濂,也要杀,实在是莫大的讽刺。其中缘由颇堪寻味。
宋先生退休时,朱元璋送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诗:“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他回应了两句:“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此后果然每年到南京朝见一次,还经常写信给太子,以师父的身份给予指点。焦竑《玉堂丛语》认为,宋氏之祸,“乃讳迹焉”,隐喻宋濂没有遵守“此后迹应稀”的旨意,招致大祸。
焦竑《熙朝名臣实录》为宋先生立传,文末引用李贽的评论,很有意思。由于宋濂学问道德名扬海外,日本国使节为了表示敬仰,专程向他请求墨宝并赠送礼品,谨小慎微的宋先生婉言拒绝。朱元璋得知后问他:“何以不受乞文之馈?”宋先生回答:“天朝侍从,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国体。”李贽就此评论:
予观上之曲宴公,尝叹曰:“纯臣哉尔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爱。”呜呼危哉斯叹,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告老而归,仍请岁岁入朝,欲以醉学士而奉鱼水,此其意不过为子孙宗族世世光宠计耳。爱孙之念太殷也!孙慎怙势作威,坐法自累,则公实累之矣,且并累公,则亦公之自累,非孙慎能累公也。使既归而即杜门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隶于籍,孙辈亦何由而犯法乎?盖公徒知温室之树不可对,而不知杀身之祸固隐于鱼水,而不在温树也。
人称“异端之尤”的李贽,读史阅世见解独特,发他人所未发。他认为太祖高皇帝一声叹息:“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爱”,是提醒,也是警告,向他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宋先生却浑然不觉,退休之后,仍然请求岁岁入朝,“欲以醉学士而奉鱼水”(此处“鱼水”一词比喻君臣相得),实在是过于天真。宋濂一向以“温树”相标榜,对朝廷机密守口如瓶,李贽讥讽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杀身之祸固隐于鱼水,而不在温树也”。至于他所说的退休之后,应该杜门不出,不让儿孙逗留官场,可保晚年平安,则未必然。按照这种逻辑,倘要彻底保平安,他当初就不应该出山,充当什么侍从学士,那么“隐于鱼水”的杀身之祸便无从谈起了。
晚明时的学者型官僚朱国祯说,宋濂晚年似乎有所参悟:“末年引疾,实拂圣心,若有意避远,并子孙亦杜仕籍,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可惜为时已晚,果然“天威一振,全族皆沉”。
(摘自《明代文人的命运》,中华书局2013年8月版,定价:32.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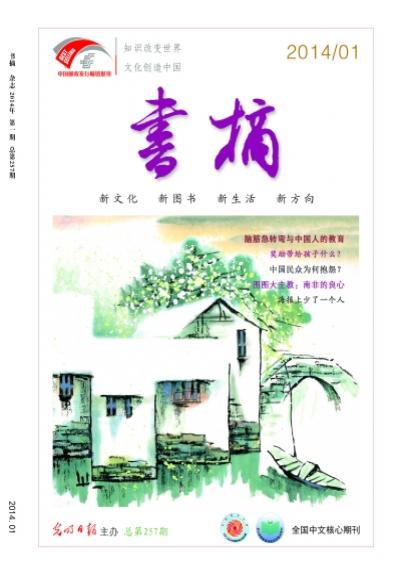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