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1978年秋,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
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
看来世界上的事还真难讲,当年的批判斗争热火朝天,泰山压顶,雄辩滔滔,深文周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是把好端端的作品打成反动宣传。突然,一下子全不算了,不费吹灰之力,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哪怕是小道理,所有的子弹炮火同伤痕遗迹,全部烟消云散。世界上的事怎么会这样虎头蛇尾,有头无尾,历史怎么会走得这样匆忙粗糙呢?
我突然想到,也许虎头蛇尾是世界诸事的规律,许多战争是这样,许多创作也是这样——如《红楼梦》,创世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
文坛一瞥话清明
1979年6月14日,我与芳双双回京。
我回到北京,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中国的“专业作家”与外文中的专业作家含义不同,恰恰相反,在外国,专业作家是指以写作为职业,靠版税生存的人,在中国,是指被“养起来”写作的人。
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意见不一。管桦,杨沫,都对浩然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然。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然一花独秀,尤其是浩然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归来”的我等(包括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
我也不想站队。我明确宣示过,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我愿意把这些个想法提交给广大的读者,提交给历史。从个人经历来说,新时期以来,在我回忆的这个时期,我是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的。
还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干。就是不与人搞口舌之争。至今如此,有误解,有歧义,有恶意,有胡说八道,我都是笑一笑。笑一笑是一宝,这是我的体会。我宁可再不写一个字,宁可转业卖糖葫芦,决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第四次文代会
1979年10月30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我看到那些老文艺家,坐着轮椅,扶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了台上发言,说上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仿佛“文革”中整死的文艺家的冤魂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啦。
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例如柯岩、白桦,还有刘宾雁的讲话,全场轰动。他们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词祝贺。人们对他讲的“不要横加干涉”欣喜若狂,掌声如雷。
但我的印象不尽相同。我是主席团成员,姓氏笔画又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我近距离地感染到了也领会到了小平同志的庄严、正规、权威,他的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的神态、举止和语气。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他牢牢地掌握着局势和权力,他的姿态和论断绝无令文人们想入非非之余地。
我希望保持适当的清醒,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
34年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除了大的社会变动的投影与有关政策的宣示以外,这样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会竟然没有什么文艺的内容可资记忆。
吉凶祸福的测不准原理
1982年初夏,有友人告诉我,在今秋将召开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有可能成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对此我深为震动不安。
我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十二大,看到候补委员中有王蒙的名字。
人,机缘,历史一直在互相调适,一直会出现错位与误植,一直会出现你改变了我与我改变了你,你改变不了我与我改变不了你的情景。我称此为人生的“测不准原理”。
“现代派”风波
想不到的是,十二大后等着我的是关于“现代派”的风波。时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充任法语译员的高行健先生写了一本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其实是一部通俗的小册子,谈到所谓西方现代小说里时间空间的处理,心理描写与意识流等。李陀、刘心武、冯骥才三人各写了一封给高行健的信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表达对此书的兴趣。我因上海的《小说界》催稿甚急,写了一篇小文,介绍并称许了高行健的书。
想不到的是这成了一件事,似乎是异己的现代派思潮向中国发起了袭击。胡乔木更看重的则是甘肃出版的一本《现代文艺思潮》,尤其是该杂志上发表了东北诗人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崛起的诗群》,被认为是颠覆性的。
《文艺报》的一批骨干,面对现代派之说如临大敌。
此次的现代派风波,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我一个下马威的色调。
好在胡乔木对我是既忠告又保护。他肯定:“你走得不远”,我想他看重的是我的作品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少共情结。我的“此致布礼”大大帮助了我在猛批现代派的风浪中矗立不倒。
乔公在1983年春节期间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我和我爱人到他家小坐,极大的友好情节一传出去,《文艺报》的某些人长叹一声,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便只好放过了王某。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后来夏衍写了文章,巴金老也发表了看法,都不赞成那样如临大敌地批现代派。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更加不安。
《文艺报》的同志收获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与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民间文学研究会;理论组组长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结果。
中央委员会
我自1982年秋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前后参加中委活动十年。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我一方面感到一些拘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存惊叹,党可真有两下子,天南海北,党政军企,身经百战的虎将,运筹帷幄的官员,各有绝门的专家,各色头面人物,土的土,洋的洋,文的文,武的武,汉满蒙回藏苗瑶……堪称网罗殆尽,硬使几百万几千万各不相同的人物拧成一股绳,使成一股劲,团结起方方面面,管理住东西南北,步调基本一致,朝令大体夕改,说贯彻就贯彻,说制止就制止,说转弯就转弯,办成一件大事又一件大事,错误也没有少犯,犯完了改过来再干,仍然是说嘛算嘛,指东绝不打西……
清明的心弦
1983年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讲了不要搞精神污染的问题。时隔30年,我现在写到这段历史,写到我在反精神污染时撰写的散文诗《清明的心弦》的时候仍然自问:什么叫清明?我其实完全没有弄清明,我不明不白了。
这一段时间文艺界确是常常被内部通报。新的领导方法并不是放任自流,自由世界,而是改理论思想的纠偏为力图严密的管理,不争论,不炒作,不咋呼,不动声色,堪说是不吭气地管住管严,天下太平,令“有害信息”无法出笼,一出笼也先挨上一棒子,再一棒子;个案处理,不搞左右之类的概括,以行政性具体措施性管理取代意识形态的唇枪舌剑,对待创作者尤其是名人放宽尺寸,团结帮助,以礼相待,而对于发行者经营者编辑者各级各单位大小领导干部严格约束,以行政性奖惩取代理论观点性激战,主要是运用行政权力而不是话语权威来管……这些,都是后话,而此时已露端倪。
有过这么一次作代会
1984年年底到1985年年初,开了一个跨年度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我当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说来话长,居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有说是闹翻了天的,有说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赞扬,有的愤恨。
开幕式上,宣读各领导人贺词贺信的时候,胡乔木的声音受到冷落,周扬的名字轰动全场。有人发起了致周扬的慰问信,会场上悬挂着这样的大信,许多人去签名。我没有签。
会议的主题是创作自由,但创作自由不是喊出来的,它是一个逐步实践、落实与拓展的过程。然而同行诸兄诸公是没有人注意什么“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创作自由”的。认为文人同行能“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婴儿。
四次作代会的结果是好几个重要的作家诗人落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他们都是作协副主席的候选人,而且名字都印到了选票上,本应无疑问地选上的。曹禺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当选为剧协主席了。而其他几个人的落选就与舆论、与各种窃窃私语有关。
有一位领导很生动地形容这种文艺头面人物的内斗:从上海“左联”时期就斗,到了延安,斗得更厉害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仍然继续斗。直到“文革”,全完蛋了,消停了些。“文革”一结束,又斗起来……最后两边的人都逝世了,一看,两边的悼词,并无不同,都是优秀的文艺战士,都是杰出贡献,都是巨大损失,谁也没比谁谁多斗出个一两一钱来……
极“左”只能消解
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使我得到了一大启发,极“左”是没有出路的,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以“文革”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政策是没有出路的,极“左”与极右是互为依据的,极右同样是只能头破血流,祸国殃民。但对“左”不要搞什么大批特批,大批特批的方法与举措本身就是极“左”的产物。
我的体会,极“左”只能消解。生活是消解极“左”的,市场是消解极“左”的,经济运转本身就是消解极“左”的,执政党的地位是消解极“左”的,小说诗歌散文影片电视剧相声大鼓都是消解极“左”的……同时克服与消解极右。
我相当反感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中烈士出得太少的各类暗示。“左联”五烈士,雨花台的枪声,郁达夫的被害,王实味掉了脑袋,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丁陈集团,成千上百的作家划成“右派”,“文革”中《红岩》作者之一的坠楼,傅雷的全家自杀,郭小川在黎明到来时死去……你为什么那样嗜血?
中国总是这么绝门。查阅资料,外国讲人文精神,是讲脱离神学的钳制,承认世俗与人,而中国讲的是脱离物欲的引诱,走向伟大的理想精神,甚至视世俗为罪恶。同样叫人文精神,外国强调的是人,人的而不是神的。我国强调的恰恰相反,我们强调的是原文中并不存在的文与精神,而不甚在意于人。绝了。
明年我将衰老
《花城》2013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短篇《明年我将衰老》。
2013年,我就要79岁了,而按照过去的民间习惯,我的“虚岁”业已80,从1953年我动笔写《青春万岁》算起,我从事文学写作已长达60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65年。感谢上苍,从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个寿数。
2013年对于我是重要的,这一年,怀念着也苦想着瑞芳、万念俱灰的我在友人的关心下结识了《光明日报》的资深知名记者,被称为美丽秀雅的单三娅女士,我们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她是我的安慰,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我必须承认,瑞芳给了我太多的温暖与支撑,我习惯了,我只会,我也必须爱一个女人,守着一个女人,永远通连着一个这样的人。我完全没有可能独自生活下去。三娅的到来是我的救助,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我感谢三娅,我仍然是九命七羊,我永远纪念着过往的60年、65年、80年,我期待着仍然奋斗着未来。当然,如我的小说的题目,明年我将衰老,而在尚未特别衰老之际,我要说的是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摘自《王蒙八十自述》,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33.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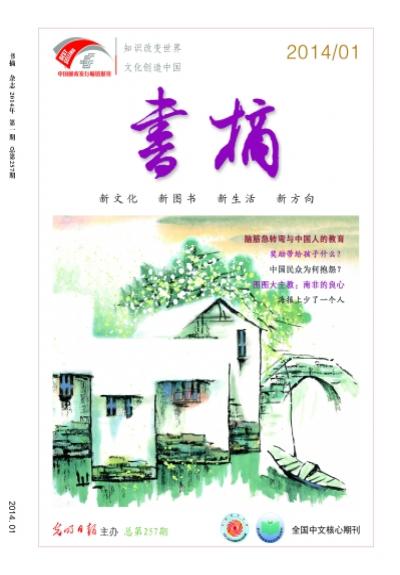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