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人民日报》下面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的“不容易”,并说,这样写的话,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和谐首先要民众安定,而要民众安定首先要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看不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难道我们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利去指责我们民众的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心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您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还要做这么多的活动,但是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是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还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而艰辛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不经你同意,不经法院判决,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不经我同意拆毁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照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合法并且是经我同意拆的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我同意的非法拆毁,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上可能腐败,但是只要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不依法立案和依法判决。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就是不给你立案和依法判决,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会在议会提出质询,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待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
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尽管这样,我还是坚持问:“假若议员就是不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家哪一天拆掉呢?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么项目就让农民成为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和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的一个纪录片,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天啊,还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要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想要民众不抱怨,你要让民众对你理解,你首先应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的最后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无理要求。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需要改变。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运动。
第四,要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的“不抱怨运动”。
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我认为,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国家制度的认同。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实力。
(摘自《父亲的江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35.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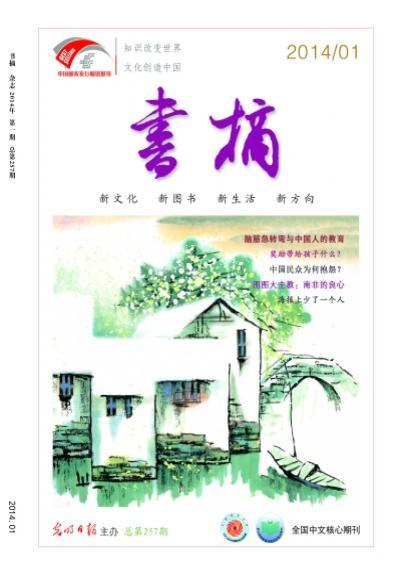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