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许多事情,难有“是非”可言。比如饮食。
尽管中国古人说过“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之类的大话,但现实之中,南人之口与北人之口,中国人之口与东洋人之口与西洋人之口,所“嗜”之 味,往往毫不相干。有的时候,此地之“非”,恰为彼地之“是”,很难达成一致。
中国南方的田间地头长着一种草,叶卵状,茎白色,大名蕺莱,古称岑草,别名折耳根。说起来,这蕺菜也是大有名头。当年越王勾践吃了败仗,被迫到吴王夫差宫中打工。为早日脱离苦海,勾践使出绝顶功夫,在夫差生病时主动申请尝其粪便,以确定病情,好让大王早日康复。这一手果然灵验,夫差痊愈后,很快便让勾践回国享福去了。不过,勾践也因此落下了病根,口臭。这下便有些麻烦。一国之君,满嘴喷着臭气,下达的指示再冠冕堂皇,也少点正经味儿。幸亏大臣范蠡想出个高招,“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乱其气”。大家都吃点蕺菜,要臭就臭到一块儿,省得让老大一人难堪。
蕺菜的最大特色其实并不是臭,是腥。其味道与松花蛋、臭豆腐、韭菜、大蒜之流绝不相同,而是有着一股强烈的鱼腥气。吃食之中,非鱼而腥者,似乎唯此一家,因而蕺莱也叫鱼腥草。这种味道,一般人起初很难消受,因此,吴越之地,除了当年的勾践,似乎再没有什么人把蕺莱当正经东西,相反,还授予了它种种“美名”,什么猪鼻吼、狗帖耳、臭草、臭嗟草、臭臊草、臭腥草……听听这些谥号,即可明了其地位如何。
不过,在巴蜀之地,这味道奇怪的蕺菜却被奉若上宾,有着上亿之众的铁杆追“腥”族。四川人如果提起折耳根,便会眼睛发亮眉毛上扬,视其为天下绝味。不少人长年不可离此君,凉拌、烧肉、炖汤,变着花样招呼。四川的烹饪学家熊四智先生还将蕺莱列入四川野蔌八珍,可见其地位之尊崇。邓小平1986年春节回四川时,据说就曾指名要吃折耳根,因不到时令,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一些。现在四川已经把折耳根当菜种,有的县一种就是上万亩,再不愁没的吃。范蠡知悉此事,准得目瞪口呆。噫吁!国人口味之差别甚矣。
中外对于美食的认定,更是各吹各的号。法国有一名菜,叫鞑靼牛排。几年前和一批记者到空中客车公司采访,在巴黎餐馆吃饭时,不知是谁点了这道菜,及至“牛排”上桌,众人却只是大眼瞪小眼,无人再肯出头认领。盖因盘中仅生牛肉馅儿一团,生鸡蛋一只,外带说不出名堂的树叶草籽儿几样,实在过于生猛。最后,还是本人当了敢死队,将生鸡蛋嗑入生肉馅,加上七七八八的调料,把这道大餐送进了肚子。味道还不错。
前一段,在北京见到一位在中国待了十几年的法国女士时,顺便聊起了“鞑靼牛排”。她登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连说“好吃好吃”,还说小时候在法国时,上肉铺买牛肉馅,回家路上边走边吃,到家时只剩了一半。据说,丹麦也有和“鞑靼牛排”相似的菜肴,名为“魔鬼的太阳”,而且还是国菜。中国人碰上这等丹麦国菜,多数可能是只见魔鬼不见太阳了。 饮食之“无是非”或“多是非”,与一国一地的环境物产、文化习俗乃至意识形态都有些关系。在小国寡民时代,人们固执己见倒也无关大碍,因为无须与外部“搭界”,尽可关起门来成一统,按照自己的喜好吃饭喝汤。如今,人们要外出办事,要旅游观光,要渡洋考察,于是,己之”是”与他之“是”,难免发生碰撞。如果仍一味固执,不知变通,倒霉的是自己的肚子。
要想肚子不受委屈,就不能坐井观天,盲目是己而非人。不管是折耳根还是“鞑靼牛排”,最好先拿来品尝品尝,对胃口的留下来,不合适的 一边儿去,这起码于健康有好处。饮食内外,都不妨来点儿五湖四海。
折耳根如今北京超市也经常见得到,有兴趣者不妨买些尝尝,只要挺过最初的鱼腥气,便会觉得它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吃折耳根,以凉拌味道最好,可以保持其原味儿。
(摘自《食之白话》,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29.8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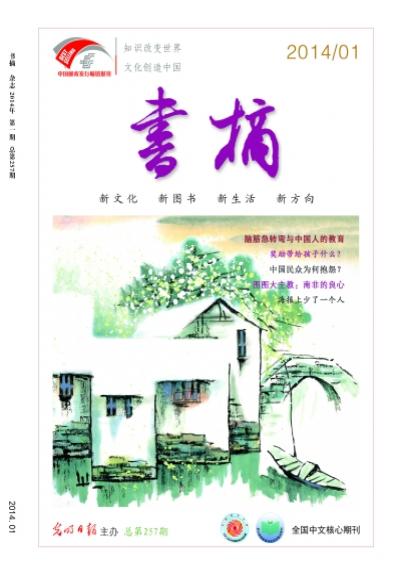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