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里的小巷古朴幽深,条石路面清清凉凉;
吊脚楼临河而居,细脚伶仃站在水里;
乌篷船上艄公的号子唤醒黎明,送去黄昏……
它叫凤凰。
湘西,雨巷
千年的景致里,最美也是藏得最深的事物,我认为不是沱江,不是吊脚楼,而是那青灰色屋檐下迂回曲折、综横交错的青石小巷。夏天时光脚踩上去冰凉冰凉的,屋檐下有红灯笼垂挂下来,两旁是木板房屋的人家,这样的小巷,总叫人情不自禁要把它想象成戴望舒笔下雨巷的样子。
若是天下了点雨,恰好将屋顶和地面淋湿,路面微微发亮,在黄昏时灯笼的光晕里,一个人撑了伞,闲闲地走过,小巷里,只听得一个人的脚步,心里隐隐约约地期待着一次美丽的邂逅……
抵达凤凰的那天下午,恰好大雨,我在朋友早已安排好的宾馆里休息,宾馆的阳台类似长廊,连通在一起,和江边所有建筑一样,屋檐垂挂着一溜红灯笼。阳台下就是一条青石小径,一头通往城郊的沈从文墓地,一头通往古城的闹市区。这是8月,凤凰的旅游旺季,无数的游客和人力三轮车从我阳台下经过。对面是苍翠的山脉,雪峰山的一部分,因下雨的缘故,山间弥漫着白色水雾,沉沉的久久不散。沱江就在我与对山之间奔腾,大雨漫天而下,江面上密密麻麻都是被雨水砸起的小水泡。
我下了楼沿着小巷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个晚上,看着红灯笼一盏盏亮起来;江边的酒吧响起疯狂的鼓点;小饭店门口悬挂着香喷喷的湘西腊肉和烤黄的鸡鸭,热火朝天的样子,服务生满堂穿梭;有店铺在当街表演姜糖制作,伙计把姜糖拉得长长的,调试它的硬度,旁边是围观的人群,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很多人聚集往码头边放河灯,无数的河灯被放下去,随波逐流,禁不住小小浪花的席卷,最后大抵沉入黑暗的河水;一些招牌亮在旅馆和酒吧的门口,暧昧地招徕着顾客,似乎人世间最浪漫的艳遇、最激情的故事都在这些吊脚楼式的家庭旅馆里上演……窄窄的小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磕头碰脑的像是夏夜黑地里的蚊子一样密。
扎染、印染、银器铺、绣花工艺品,五光十色的店铺,光影里斜斜乱飞的雨丝,撑伞的、不撑伞的游人,喧闹的世界,热闹非凡的雨巷……
全然不是我想象中寂寞清冷的样子。
全然不是戴望舒笔下那般人流稀疏的模样。
经过北门城墙时,墙洞里一支卖唱的乐队突然一齐发声:
……
我多想回到家乡
再回到她的身旁
看她的温柔善良
来抚慰我的心伤
……
忧伤的旋律瞬间把我击中。
这是繁华的闹市。跟我原来的期望隔了十万八千里。
奇怪的是我依旧喜欢。
在那层层叠叠青砖的屋瓦下,卧着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故居,民国总理熊希龄的故居,当代知名画家黄永玉的画室,和一些当地著名的祠堂,这些都是供人瞻仰的景点,是远离了人间烟火的风景,没了温度。
那晚,徜徉良久,在小巷的尽头,我意外见到了梦中出现过千百次的景象: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小巷的青石路面被洗得发亮,路两旁的人家大抵已经关门闭户,红灯笼依旧点着,游人因为夜深而变得稀疏,整条小巷,寂静而清冷。
不知哪里飘来蔡琴低沉的歌声:
……
寂寞的长巷,而今斜月清照
冷落的秋千,而今迎风轻摇
……
我呆立在雨巷中,突然因这灯火阑珊时的感动,迟迟无法挪步。
沱江边的车夫
我努力想从眼前这车夫身上寻找沈从文当年回湘西时,那一路帮他将行李从沅陵挑至凤凰的挑夫的影子。
这是一个年近三十的车夫,不高、黑,着一袭颇具热带风情的衣裤,花里胡哨的。他的上身和脸一样,呈方块状;两腿短小,显得发育不良。在当面和他说话之时,看着他大国字脸上连成一片的络腮胡,我有好几次忍不住偷着乐。
他飞快地拉着我们在沿江窄窄的石板路上飞奔,不时跟对面来的人力三轮车用凤凰土话嚷嚷着大声招呼,不时回头跟我们介绍沿途景物,同时没忘了在会车时将行人吆喝到一旁:
“车来咧——让一让,让一让啊——”
嗓门儿粗哑。如果不看他本人,你会以为这嗓门儿的主人至少年届不惑了。然而他车龄并不长,大约在凤凰开始大规模开发的2001年起,他就从事了这个行当,他的嗓音和沱江边所有车夫一样。
沈从文墓地我已经去过,可我还是想去,一是喜欢听涛山依山傍水的清幽,二是这里有个村人用的小码头,从此地可以乘坐本地人的小船泛舟沱江。车夫听说我们还想游沱江,立刻来了兴致,执意要为我们介绍渡船。为着他可以从中拿点介绍费,我也没有拒绝。这个拉了6年车的车夫,用一辆车,拉活了一个家。他的那双手,还将继续拉下去;他的双腿,还将继续丈量着这熟悉的青石路——生命中又有多少个6年呢?
我们在墓地耽搁了不少时间,下得山来,花衣服立刻迎了上去,原来他一直在等着我们。
他憨厚的笑着,太阳将他的脸晒得又黑又黄,他搓着大手跟我们介绍旁边的船夫。那船夫看上去比他稍年长,一样的黑。似乎是为了价钱的缘故,两人在小声的商议。因是本地土话,我没有听懂,但是看得出来,花衣服在为我们斡旋,争取了一个我想要的合适价格。那一刻,我心底有些感动。
想起车停中途的时候,他为我们算的账:每天拉客10趟,每月3000元,遇到抠门的主顾或者旅游的淡季,还不到这个数。这笔看似不低的收入中要上缴一部分给旅游局,大部分维持家用恰好,还小有盈余,但旅游业的疯长同时刺激了本地消费,比省城还高的物价,想必他的日子过得十分节俭。
但他却有很多计划和憧憬,他不断对我们絮叨,沿江这一带一定会不断发展,现在的远郊以后一定会繁华热闹起来,那时,大约他也可以将车拉的更远吧。
这沱江的车夫,生存始终是唯一的信念:只是这么简单、安宁地生存着——黄昏回家时有满院的烟火等着他,白天有车可拉,孩子听话肯读书,长大了不要和自己做一样的事情。
他们围在老城门的城墙根下,一边等客,一边闲唠嗑。他们大多是壮年的男人,少数女人偶尔顶替家中男人来拉上一两趟,但绝不久留;她们更愿意去码头卖河灯或拉客,为自家或相熟的渡船介绍生意。
夕阳悄悄地挪移,晒着城墙根的青苔和小草,几十年过去了,几百年过去了,青苔依旧,荒草依旧,古城里的男人活得依旧:那么卑微,那么自在,那么滋润,那么轻易就满足。
那个花衣服的车夫夹杂其中,他的孩子还小,离读大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有理由梦想更多,可他的梦和旁的车夫比起来,并无不同。
(摘自《清晨,在陌生的地方醒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26.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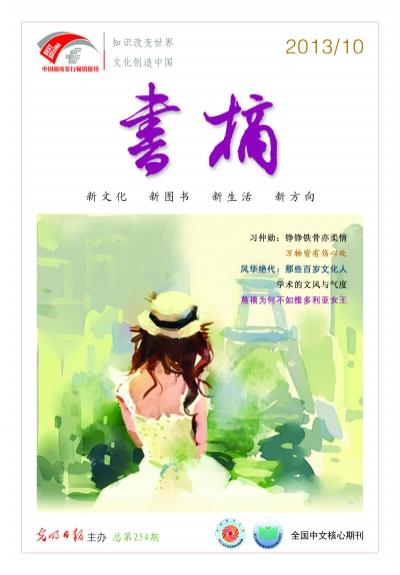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