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市政府会议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其间,《文汇报》记者唐海因发问蒋介石令其大怒而名震一时,以至若干年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参加开国大典的唐海的手说:“唐海,唐朝的海,久远得很哪!”(张煦棠《唐海之海》,刊《文汇报》2005年2月25日“笔会”)
“唐海发问蒋介石”已成为文汇报史,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的“传奇”。曾听不止一位老报人说起此事,但重点都落在唐的无畏和蒋的恼怒,至于唐与蒋如何一问一答短兵相接,似乎已在“传奇”之外,因而也就语焉不详了。
后来读到《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撰写的《风雨文汇:一九三八——一九四七》(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版),其中有《唐海向蒋介石的提问》(以下简称“《提问》”)一文:
……招待会快到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礼貌性地问:“还有问题的话,再谈三五分钟。”
唐海站起来说:“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蒋主席的‘四项诺言’也规定要释放政治犯,不知政府何时可以释放?”
蒋介石脸色马上沉了下来,很生气地回答:“政治犯已经释放。你说还有哪个没有释放,你开名单来!”
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一片肃静,不少人的目光注视着唐海。
唐海又站起来说:“到现在为止,只释放了一个廖承志。”
没等到蒋介石再回答,御用报纸的负责人马上以一般性的问题,冲淡会场的紧张气氛。不久,记者招待会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
据郑重说,这是“40年后,1986年春天,我在太原路唐海居住的一幢花园洋房里访问唐海的时候,听他谈这段往事”的;又说,“访问唐海之后,我翻阅旧报……”如此说来,《提问》中的“这段往事”既有当事人的回忆,又有相应的史料依托,该是较为可信的。但细加推敲,唐与蒋的一问一答却不无有疑处:
一、蒋介石刚刚在协商会开幕讲话中宣布“四项诺言”(即“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普选”及“政治犯释放”),记者会上有人就“释放政治犯”提问,当算不上是“突然袭击”,蒋及其幕僚该是有预判和应对之策的,为何蒋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很生气”呢?
二、抗战胜利后,蒋已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世界风云人物,且身为最高领导,他对“释放政治犯”这一重大事项的实施进程应该是随时掌握的。面对“何时释放政治犯”这样的问题,蒋完全可以“正在实施”之类的官话搪塞,很难想象他会冒着被当众揭穿的风险,说出“政治犯已经释放”这种低级谎言;更难想象他会不计后果地说:“还有哪个没有释放,你开名单来!”——这无疑是愚蠢至极地给了对方一个“探头球”:只要对方给出一个未释放的政治犯的名字,譬如叶挺,岂不就给了蒋一记巨响的耳光?
查阅旧报可知,“根据有关部门通知,招待会新闻必须采用”(《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1938—1998)》,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编,2005年。以下简称“《大事记》”。)的中央社稿是这样报道的:
问十一:政治犯何时可以释放?
答:政治协商会议对于释放政治犯一点已有决议,政府对此早经宣布,现已实行。
值得注意的是,唐海“直接参加编写”,“取材于《文汇报》版面内容、文书档案,同时参考《文汇报》老报人和知情者的回忆”的《大事记》,对此也只是说:“此问题为本报记者唐海所提,中央社报道事实有出入。”至于事实真相,却未见“老报人和知情者”片言只语的回忆。
三、唐以“只释放了一个廖承志”对答蒋的“你开名单来”,似乎也有些“答非所问”——对于“探头球”,一个敏锐的记者通常是不会放弃“迎头痛击”的。
此外,《提问》一文还有若干错漏及令人不解之处——
《提问》说:唐海当时系《文汇报》负责采访政治新闻的记者,兼职南京《大刚报》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是拿着《文汇报》经理严宝礼的请帖出席记者会的。记者会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找《文汇报》负责人严宝礼谈话。徐铸成陪严宝礼一起去见张道藩。张对严、徐施加了压力,提出了责问。张道藩回到南京后,找了当时唐海兼职的《大刚报》社长毛健吾,对毛健吾下达命令,立刻开除唐海并且说要逮捕法办。毛健吾专程赶来上海,对唐海说:‘你闯了大祸,得罪了蒋主席。’……这样,唐海就被《大刚报》解雇了。”
这段叙述多有令人不解处:张道藩找严宝礼谈话,为何时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要陪同前往,且一同受到张的施压、责问?张“对严、徐施加了压力,提出了责问”,为何最后却只是命令《大刚报》开除唐海的兼职?张说要将唐海“逮捕法办”,为何唐海此后仍能以“本报记者”的身份在《文汇报》上不断露面?
《提问》说:记者会“第二天《文汇报》又刊登与众不同的社评《所望蒋主席者!》文中几处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删去,以至上下文接不起来,有的地方留下空白开了天窗”。
这段叙述似乎意在说明,《文汇报》在记者会后强化了自己的立场,而国民党则加强了对《文汇报》的新闻检查。但翻检旧报却发现,《所望蒋主席者!》(旧报原题为“所望于蒋主席者!”)刊于记者会召开当日,即13日出版的《文汇报》上,也即记者会前。可见此文之“开天窗”,与唐海发问蒋介石无关。
也不知是当事人唐海记忆有误,还是作者郑重翻阅旧报时疏漏,以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简称“主委”)身份主持记者会的张道藩,被《提问》说成是“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据查,张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长还是抗战时期的事了。
但《提问》依据的毕竟是当事人的第一手史料,因此错漏归错漏,有疑归有疑,我终究还是只能“存疑”于心。
近日翻书,偶遇《新民晚报》老报人张之江口述实录(董纯蕾、唐洁《对话张之江:有没有这样一种沉醉》,见李清川主编《相遇历史——老报人访谈录》,文汇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我心中的“存疑”于是有了柳暗花明处。
这位当年经由唐海介绍加盟上海《新民报·晚刊》的老记者回忆说——
我和唐海的初次见面是1946年的初春,在蒋介石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我当时是一家小报馆的记者,唐海是《文汇报》的记者,还兼任《大刚报》的主任记者。我们两人当初并不认得。记者招待会现场,唐海坐在我前面没几步路。提问时间里,开始都是外国记者的场面。最后,蒋介石问:还有没有中国记者要提问?但跟着提问的,也是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这时候,唐海举手了:“请问委员长,您在重庆政协做的四项承诺,什么时候兑现?”蒋介石当时就拉下了脸:“当然是要兑现的。你说说看,我哪项没有兑现?”唐海还想继续问:“譬如说,张学良的问题……”但被身边的徐铸成制止了。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趁机赶紧宣布散会。
同是当事人的第一手史料,张之江与唐海的回忆却大有出入,孰是孰非的确很难判断。所幸张的回忆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另一位当事人徐铸成。
徐铸成晚年著有多部回忆录,既然他当时在场,我想,对如此重要的事件他定然会有记录。
果然,徐铸成写于1984年的回忆《我采访蒋介石》(徐铸成《风雨故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中有此记录: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是在1946年初,他从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在上海露面。有一天,在三马路市府(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旧址)大客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当时还在《大公报》任总编辑。他讲些什么,记者们提出什么问题,我现在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文汇报》年轻记者唐海曾发问:“现在全国团结建国,请问主席,张学良将军何时可以释放。”我侧目看蒋的脸色立时煞白,怒容满面,后立的戴笠、唐纵等都两目射出凶光。招待会就此收场。
张与徐的“张学良说”虽叙述上略有出入,但足以互证,且较之唐的“廖承志说”,“张学良将军何时可以释放”显然是令蒋恼怒的问题。
检阅旧报可知,自协商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奋激陈辞,要求政府释放张学良及杨虎城。并谓:蒋主席曾允诺释放一切政治犯”之后,虽然当局一再强调“所有事实均明示张、杨二人不应归于政治犯之列”,但仍受到来自中共及民盟等方面的不断施压,国民党内部对此显然也产生了分歧。二月初,《大公报》报道说,“政府将于数日内释放政治犯,总数约三万名。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及杨虎城亦在其列。”记者会前一天,法新社报道说:“盛传张学良将获释”……
外有压力,内有分歧,“盛传张学良将获释”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从张学良终究未能获释看,蒋当时正处于两难之境——释放张、杨由中共代表率先提出,且与“释放政治犯”挂钩,已令蒋处于尴尬境地,无论释放与否,蒋在政治上都已“失分”——而此时唐海竟发问“张学良将军何时可以释放”,就大有“逼宫”的意味,也就无怪乎“蒋的脸色立时煞白,怒容满面”了。
如果蒋的确说过“你开名单来!” 那很可能是蒋被“逼宫”之后说的“气话”:“你要我释放谁我就得释放谁,那干脆你开名单来!”而这“气话”当是冲着中共而去的,因为唐海的发问,与周恩来在协商会上的“奋激陈辞”一脉相承,很难让蒋介石相信唐海不是共产党。徐铸成的回忆可以佐证这一点:
当晚,《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兄邀我同去见张道藩,请其代为解释。张还一再说:“唐海不是共产党,你们能担保么?”
现在来看,唐海当时虽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其发问的确有中共“背景”。他的直接领导、《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孟秋江就是中共党员。而据唐海回忆,记者会前一天,他“已经想好要提的问题,向采访部主任孟秋江汇报。孟秋江帮助他策划要把释放政治犯作为重点问题提出……”(《提问》)
唐的发问激怒了蒋,严宝礼深感事态严重,于是当晚邀徐铸成一同“去见张道藩,请其代为解释”。不难看出,这是严宝礼想借助徐铸成的影响力向张道藩“求情”,并请张出面斡旋,以设法减轻当局对《文汇报》的处罚。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严、徐此次拜会张,的确产生了作用,《文汇报》因此“毫发未损”,且保住了唐海。当局只是让《大刚报》解雇了唐海的兼职“以儆效尤”。徐铸成的这段回忆解答了《提问》中的诸多不可解之处,更为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会次日出版的《文汇报》也呈现了“解释”的姿态:头版头条按规定照登中央社的《招待中外记者席上蒋主席谈当前问题》,配发中央社侧记《招待记者会上空气融洽自由》,以及《欢迎大会今举行 下午三时在跑马厅 参加者将达十五万》等蒋在沪活动的新闻,同时在第二版刊载了唐海采写的新闻特写《蒋主席莅沪第三日几个新闻性的镜头》,其中的记者会“花絮”,对蒋的描述也相当正面——
主席头发已略带灰白,但是精神极好。走路的时候,步伐轻快,常常露笑容。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很快,双手常常交叉地放在胸前,夫人和主席讲话的时候,用上海话,在下扶梯时,关照主席“当心跌跤”。
……
有关“唐海发问蒋介石”的回忆,从上述分析看,当是“张学良将军何时可以释放”更为可信。但令人不解的是,《提问》披露的唐海回忆,竟与亲历者徐铸成、张之江的回忆迥然有异,何以如此,显然还有待进一步考据,故本文只能算是抛砖引玉的“小考”。
2013年7月29日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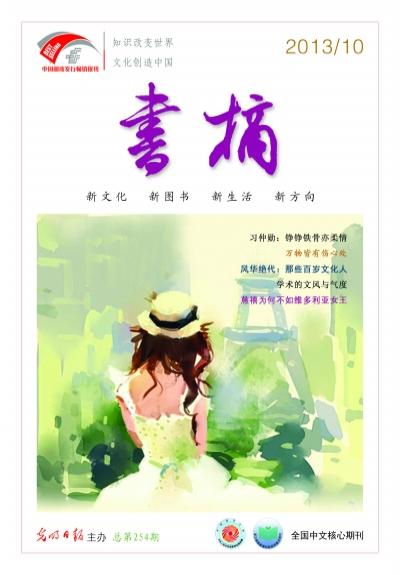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