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刚刚开始,中国正式进入毛泽东时代。这个天才的战略家,率领共产党和军队,成功地结束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紧接着,继续以运动战的方式,推进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三五反运动,把广大工农群众按照新的方式组织起来,凝聚为新国家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严厉打击地方的乡绅势力、资本家、所有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此外,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名为“洗澡”。至1956年,随着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一个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
1949年后,向有“自由职业者”之称的作家诗人转变为“单位人”,随着职业问题的解决,开始为组织所规约。与此同时,出版业成为国家统一管理的专业。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逐步升级,直至酿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但是,在文艺界,不但没有人对钦点“思想犯”的做法提出批评,而且大批知名人士都成了积极的追随者。经过以“双百”口号为标志的短暂的和平间隙,至1957年,毛泽东再度发起规模宏大的整风运动。据统计,55万“右派分子”陷身逆境。从此,文艺界再也没有异议的声音,只有大唱高调,直至“文化大革命”汹涌来临。
在中国,无论在诗歌界还是整个知识界,郭沫若都是领军人物。他在建国后任政务院副总理,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他的诗歌取向,无疑具有示范性作用。
很早以前,郭沫若就表白说自己是“有些左倾病的人”,他要做“革命时代的前茅”。1920年,那时他放声大叫:“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天狗》)后来这种叛逆精神不见了,一度吞下去的太阳,这时却变做了膜拜的对象。在古代诗歌中,太阳是君主的象征,新民歌恢复并刷新了这一传统意象的特定含义,郭沫若从中取得灵感,多次将毛泽东比作太阳,反复加以赞颂。如此借象取喻在国外也有,像苏联就很突出。但是,严肃的诗人是反对的。如因反对土耳其政府而长期留在苏联的希克梅特,在1951年就这样表示说:“我十分尊敬斯大林同志,但我不能读那些把他比作太阳的诗,这不仅是坏诗,也是坏的感情。”郭沫若起愿做“喇叭”,自始至终是一个紧跟“形势”的诗人;文艺整风中,带头写过一篇表态文章,叫《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明确否定自我,并劝告广大文化界人士接受思想改造。《新华颂》是他建国后出版的第一个诗集,所编全是《集体力量的结晶》、《鸭绿江》、《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之类,开了新型“应制诗”的先河。“双百”方针出台以后,接着出版诗集《百花齐放》,极力把“反右”以后的季节装扮成春天。大跃进时期,他到张家口地区跑了一趟,一气写下组诗《遍地皆诗写不赢》,计数十首,热烈赞美当时的过火做法和浮夸风气;还同周扬一起,合编了一本《红旗歌谣》,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提供范本。直至“文革”届临,郭沫若仍写诗不辍。初期,他写了《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文革”》、《大民主》、《毛主席去安源》、《庆祝“九大”开幕》等,歌颂“文革”,歌颂暴力,歌颂伟大红旗以至炙手可热的旗手江青,后期又写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等。但他颇有自知之明,自述道:“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郭沫若1949年以后写诗上千首,从他生前选编的《沫若诗词选》看,所收278首诗词,新诗仅48首;其中,五十年代39首,六十年代仅9首。形式的复古倒退,是与内容的单调空虚相适应的。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同为诗人的宗白华说他是“在朝的达官贵人”,“有他身不由己、逢场作戏的苦衷”。他的幼子郭世英因参与组织X社而被打成“反革命”,于“文革”初期坠楼身亡。在此期间,他一面用毛笔工整地抄写儿子遗下的日记,寄托内心的哀思,一面照例接见外宾,填写歌颂“文革”的诗词。
相当一批诗人,如陈梦家、戴望舒、孙大雨等,建国后随即沉寂下来。如果不甘沉寂,就必须追随主流,改变诗风。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十四行诗》运用西方形式表现东方情调,诗艺精湛,影响颇大。此时,他改以通俗的语言演绎民间故事,编写土改翻身的新传说;如果拿《韩波砍柴》与过去的《蚕马》、《帷幔》等比较,面目迥然不同。臧克家本以描叙农村苦难和锻炼辞句著称,现在也不能不放弃他的特长。三十年代与何其芳、卞之琳齐名的李广田,1957年整风期间,写了一首诗,名叫《一棵树》:“我受大地和太阳的哺育,/我在风里雨里锻炼自己的身体。/……还要把根扎下去,扎到最深处,/也要把枝叶伸出去,伸向太阳去。/……我必须每年落一些叶,/也必须不断地脱一些皮。/……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休止,/因为我自己并不属于我自己。”可以说,这样的“表态诗”是有代表性的。诗人坦言“我自己并不属于我自己”,忠实地描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裸裎了知识分子与现行体制的某种契合关系。苏联及东欧文学史中有一个词叫“多数派”,中国多数派的诗,就是这样的诗:单调、直露、粗糙、假嗓子,缺少人性的润泽。
艾青早年留学法国,归国后从事进步的美术活动,后来投奔延安。他是一个把西方的观念同中国的土地亲密地揉合到一起的诗人,一个深沉的、自由奔放而又略带忧郁气质的诗人,一个具有大师潜质的诗人。然而,他并没有在人们的期待中长成大树;却也如他后来写到的盆景那样,由于离开了大旷野,而无法逃避“铁丝的缠绕和刀剪的折磨”,逃避园艺师的设计。建国以后,写了相当一批国外题材的诗,虽然不出反帝、和平与友谊的主题,却因为越出规限太死的工农兵题材的框架,艺术上便有了较多的可伸缩的余地。还有一些类似咏物诗、哲理诗的短制,都与所谓的“重大题材”无关,明显地含有个人的寓意。诗人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像《下雪的早晨》这样透明得几乎没有内容的诗,是当时整个诗坛所没有的。看得出来,艾青在努力维护自我,维护作品中的诗性意义;可是,这种维护并非通过自由的抗争,而是靠逃避和保留实现的。他过去诗中的那份汪洋和涌动不见了,神秘不见了,忧郁不见了,而在他的心弦上却落满了尘土和忧伤。
艾青是一个有自由感的诗人。他不像一些现代诗人标榜的那样唯在纸上自由地栖居,作为一个歌手,他要和大堰河的儿女们一道摆脱枷锁,争取地面的自由和幸福。一个真正的热爱自由的人,必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不可能对大众的社会斗争无动于衷乃至拒绝参与。自由的蛊惑是无法抗拒的。不同的只是,即使在大众中间,他仍然一如从前般地保持他的个体性,保持属于个人的尊严与自由。在延安,艾青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题目就叫《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这是一篇呼吁书,也可以看作是个人声明,其中说:“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强调的是:“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文章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后,随即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文一起遭到批判。1959年,事隔十多年以后,毛泽东发动《文艺报》进行再批判。为此,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主动放弃了自由写作这一唯一的特权。只是,个性和艺术信仰的存在,使他的放弃并不彻底;也即是说,他是一面妥协,一面挣扎着坚持的。于是,在这个优秀的诗人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时而写得好,时而写得坏,在大量平庸的文字里,时而出现奇异的光芒。这正是诗人的残存的自由感的作用,如若不然,他将整个地为时代所覆盖。
1979年版的《艾青诗选》收入诗人在“反右”前夕写的两个寓言:《画鸟的猎人》和《养花人的梦》,其实也可以读作两首讽喻诗。从隐喻性内容到散文化写法,在他的作品中还是比较特异的。他写猎人教人打猎,不是打会飞的鸟,而是在硬纸上画鸟来打,最后发展到先朝纸上打,打完了再在有孔的地方画上鸟,打几个孔,就画几只鸟。阶级斗争扩大化,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真正的敌人发展到假想敌,人为地制造目标,先定罪名,后到罪状,寓言揭示了这种斗争的荒诞性。另一则写的养花人,在一个院子里种上几百棵月季花,呈现着一种“单调的热闹”。一天晚上,他忽然梦见许多花走进院子,都愁眉泪睫地看着他,各自诉说自己的寂寞,一致表示希望得到主人的理解,说:“得到专宠的有福了,我们被遗忘已经很久,在幸运者的背后,有着数不尽的怨言呢。”养花人醒后,对自己的“偏爱”有所省觉,也觉得世界确乎被弄得太狭窄了。为了使院子成为“众芳之国”,他觉得,必须尊重花的自由意志和开放的权利。“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吧。”著名的“双百”方针刚刚出台,知识界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这时,艾青通过寓言的形式进行呼吁和解构,应该是勇敢的。
然而,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大群的知识者成为“右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艾青们陷落社会的底层,喉咙塞满沙泥,再也无法歌唱。对于中国诗坛来说,这是一种不幸呢,还是一种幸运?人才固然遭到蹂躏,但是噪音也随着他们的失宠而大大减少;在苦难的生活中,他们倒是有希望酝酿另一种歌声,不驯的歌声。主流诗歌是没有个性的诗歌,统一的诗歌。即使有个别诗人试图玩弄花样,也仅仅局限在修辞学方面,因为连文体形式也都贴上阶级的标签,没有哪一个主题不是经过严格筛定的。这样的诗歌注定是刻板的、粗俗的、肤浅的、浮夸的、虚伪的,甚至是堕落的。频繁的运动和燥热的气候培养了一种粗暴的官方文体,诗歌的直接性被利用为直接打击,从批判胡风集团和“反右”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诗歌是如何瓦解经验语言而使用概念语言,行使语言暴力的。另一种堕落,就是利用诗歌的抒情性进行谄媚,其实是政治投机。在大地沉寂时,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的颂歌是如何的美好动听,响遏行云。
比较一下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诗坛,不会是多余的事。
涅瓦河上阿芙乐尔舰的炮声虽然已经停歇,但是,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仍然回响着炸弹的轰鸣。战争、饥饿、传染病、仇恨与痛苦的情绪到处蔓延。一夜之间,知识界发现自己被抛弃到社会的最底层。正如十月革命的领袖人物托洛茨基形容说的:“大批诗人和小说家都觉得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为这块正在走向灭亡的土地举行葬礼。”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是被镇压,被“捕狼的猎犬”活活害死的。勃洛克以憧憬革命的《十二个》闻名于世,却在惨淡的命运中辞世;叶赛宁也是在恫吓、压制、“社会审判”下自杀的;茨维塔耶娃自杀时简直走投无路,贫困到极点,连一个洗碗工也不让做。受到批判和迫害的诗人为数更多,还有众多的流亡者。
勃洛克在普希金逝世84周年的讲演《诗人的使命》中说:“对于诗人而言,要使和谐获得自由,‘安宁与自由’是必要的。但是,安宁和自由还是被剥夺了。剥夺的不是外部的安宁,而是创作的宁静;剥夺的不是孩子的自由,不是自由化的自由,而是创作的意志自由、神圣的自由。因而,诗人死了,因为他呼吸不到任何空气了,生活失去了意义。”诗人之死不单是历史现象,也是现实的情形,勃洛克很快就对革命失望了,抑郁代替了热情,并因此严重毁坏了他的健康。他不再为苏维埃官僚制度辩护。对于整整一代苏联诗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在“时代”的范畴和他们的道德与艺术的尊严之间双重性格地生存下去?他们其实只是希望“自由呼吸”,写作一种无羁的、非说教的、不受政党支配而仅仅忠诚于灵感和所有词语的诗歌。然而,在一个统一思想和音调的时代,只要坚持个人的方式就是对抗。俄国知识分子普遍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因此能够从根本上认同一种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并始终不渝地用心灵守护它。
中国新诗恰恰缺乏这样一个诗与人相结合的伟大传统。就连屈原、杜甫的声音,在历代诗人群体中也是十分微弱的。至于新文学传统,其灵魂,即五四精神,由于本土资源的匮乏,很快地,便在接连的冲击之下趋于断裂。
(摘自《中国新诗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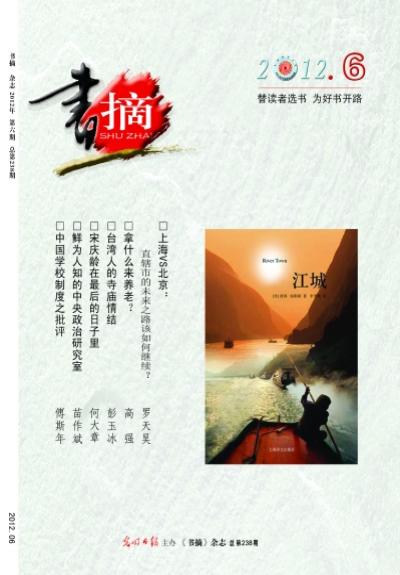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