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因它不像中宣部那样是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又不像《红旗》杂志社那样,每半月要出版一期党刊;加之当时的政研室不像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常有关于领导人的报道,所以在社会上鲜为人知。但政研室是中央的一块理论阵地,是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平级的直属中央领导的一个单位。为不使这个机构的历史湮没无闻,这里仅就笔者所知,作些介绍。
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政研室
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在延安成立了政治研究室。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年夏天,党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设十几个研究室,把训练干部的任务全部移交中央党校。一个多月后又改成了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张闻天,增加范文澜为副院长。不久,从中央研究院抽调了三十多位同志,到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
延安整风的一项思想准备工作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汇编党的文献,政研室的一些同志参加了一部分工作,主要是选语录、做核对、跑印厂等技术性工作。文献都由毛泽东最后审定。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头找人谈话,进行整风前的思想工作。就政研室方面,毛泽东找了陈伯达、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然和邓力群五位一起去谈。讲了两个来钟头。
陈伯达曾对其子陈晓农说:1941年以后,由我负责,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邓力群、张仲实、周太和、田家英都是我从马列学院挑去的,马洪是我漏下的。当时我是研究室主任兼政治问题组组长,邓力群是经济问题组组长,张仲实是国际问题组组长。七大以后,政治研究室改由洛甫(张闻天)负责。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柴沫、史敬棠,也曾在延安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解放战争时,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政研室停办。
1955年重建政研室,直接为毛泽东服务
1954年,毛泽东指定陈伯达、田家英和胡乔木去杭州起草宪法。在起草工作告一段落时,毛泽东指名要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筹备成立新的政治研究室。1955年,中央重建政治研究室,地址在北京市万寿路13号,是个新建的大院,即现在的万寿路西街7号院,中组部万寿庄宾馆。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理论研究班子,主任是陈伯达,他的办公室和毛泽东的办公室并列着,但是毛泽东没有来过。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日常工作由胡绳主持,汪浩为办公室负责人。工作人员来自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
政研室设有哲学组(组长关锋)、经济组(组长陈真)、历史组(组长黎澍)。此外还有个三人的党建组、两人的国际组。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针对整风鸣放的形势,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署名“中央政治研究室”,耐人寻味。6月12日,此文印发党内。毛泽东在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又将署名改为“毛泽东”,时间定为1957年5月15日。此文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1977年4月第一次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辞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红旗》杂志创刊后,政研室为《红旗》撰稿,宣传中央精神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红旗》杂志的创立是以政研室为组织和人员准备的,它的首任总编辑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政研室两位副主任胡绳和田家英都是《红旗》编委。《红旗》杂志创刊社址定在沙滩大院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便从万寿路迁到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楼办公。这时政研室设立三个组。原哲学组改名为思想界动态组,该组和逻辑组由胡绳分管,历史组由田家英分管。
1959年,中宣部、《红旗》和政研室三家联合,举办了座谈会,星期五召开,两周一次,每次一个主题。主持会议的是康生、陈伯达、周扬、胡乔木。具体做组织工作的有马仲扬、史敬棠、李洪林、丁伟志。作会议记录的是丁伟志、王忍之。参加会的是专家、学者和教授,名单报送胡绳和田家英批准。《红旗》杂志的业务组长和中宣部的理论处负责同志都是参与者。在这样的会上,人们可以对学术理论问题自由发表意见,思想比较活跃,有人称之为“神仙会”,以至有的与会者多年后都怀念它。可惜好景不长,庐山会议一开,人们就不敢讲真话了。
胡绳在《红旗》上开辟了“思想文化评论”专栏,署名“施东向”,即思想界动向之意,许多文章是由胡绳指导一些青年人写作并经他定稿刊出的。因经常出现,质量较高,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后来“施东向”变成以胡绳为首的有关作者的共同笔名。其成员大都是政研室的,有王忍之、丁伟志、李洪林、马仲扬、郑惠等。
1958年秋季创刊的《思想界动态》,是根据中央要求编辑的内刊,是向中央委员以上(或经特别批准的)领导同志反映各界思想情况的党内刊物(半月刊),发放范围虽然不大,但因层次很高,故受到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思想界动态》组是1958年8月成立的,首任组长是关锋。这年底,关锋调任《红旗》杂志社编委,由马仲扬接任思想界动态组组长。这个组是政研室内最大的一个组,有二十余人。核心成员有马仲扬、李洪林、史敬棠、丁伟志。编辑工作主要由李洪林负责。
1961年春夏,经田家英推荐,柴沫调到政研室任秘书长。政研室内机构再次进行调整,把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撤销,改编为工业组、农业组、编辑组。柴沫来后政研室的主要任务是搞调查研究。如1961年6月,柴沫带队到天津搞工厂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有王忍之等参加。
搞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1962年2月底,毛泽东决定由田家英再率调查组,到湖南他的家乡一带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
调查组到武汉待命时,毛泽东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
在韶山短暂观摩后,调查组兵分三路展开工作。去大坪大队(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的一组,在调查时,社员们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他们认为,恢复农村经济的有效办法,只能是以户为单位分别承包和管理少量田地的生产。他们说的“分田到户”,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田家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大坪分别召开了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调查组全体会。不仅在当地开展深入调查,还派人去安徽无为考察“包产到户”的状况。
田家英将湖南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在北京的刘少奇。陈云称赞了报告,说写得“观点鲜明”;刘少奇认真看了炭子冲的报告,认为很好。毛泽东对此却很冷淡。回北京后,田家英布置政研室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去对“包产到户”呼声最低的东北和山西,查看对“包产到户”有何反响。柴沫向政研室同志传达说,据田家英透露的信息,看来中央已经原则上定下来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现在的问题只是考虑波及面的大小,所以要我们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
1962年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中苏论战背景下,政研室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
1963年前后,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中共方面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于1964年春决定将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进行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研究。其任务是“两史四论一中心”,即编纂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关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艺学的理论研究;中心是研究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院长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副院长胡乔木,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周扬,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实际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副院长胡绳,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他们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内的红秀才和中央的笔杆子。秘书长柴沫,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
马列主义研究院组建后,开始是租用海淀区西颐宾馆北馆作为办公处所,后来迁往中央党校,已离开沙滩大院,其发生的事已不属于政研室的范围,本当不论。但研究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散了,并从其中留下一部分人重组中央政治研究室,又迁回沙滩大院。不仅如此,陈伯达倒台后,中央在沙滩大院举办了“批陈整风”学习班,参加者不仅有政研室的全体成员,还有原研究院的全体成员。学习班揭批的问题,包括研究院存在期间发生的事。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学习班的历史背景,下面简要介绍研究院的一些情况。
陈伯达严厉批评柴沫,发泄对田家英的不满
研究院成立后,按照陈伯达的旨意,工作人员都下去,先是在北京通县农村搞“四清”,然后又在北京天津两地的一些工厂搞“四清”。1966年6月,陈伯达一声令下,工作人员统统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陈伯达从延安时期起,长期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很善于领会毛泽东的心意,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件常由他起草。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思想越来越“左”,陈伯达积极配合。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和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都是陈伯达主笔。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也涉及了田家英。在会议期间,陈伯达三次跑到研究院讲话,严厉地抨击了周扬、胡绳、田家英等人,而重点是批评柴沫,指责柴沫不听他的话,走田家英的门子,搞秘书长专政。说柴沫缺乏革命原则性,在同田家英的关系上犯了严重错误。
田家英从1948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文化大革命”前已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因工作关系,和政研室秘书长柴沫、中办主任杨尚昆有较多往来。陈伯达与田家英平日矛盾很深,见毛泽东、林彪要打倒彭、罗、陆、杨,涉及田家英,于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并通过批柴沫发泄对田家英的不满。于是,一些人纷纷向柴沫开火。对柴沫的错误无限上纲,一下子把柴沫定成“黑线人物”,敌我矛盾。不久,对柴沫采取了隔离措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威逼下,柴沫感到绝望而自杀。
1967年3月17日,陈伯达来研究院接见全体工作人员,并讲话。不知谁将陈伯达讲话的记录整理外传,闯了大祸。3月26日,陈伯达又来院召开大会,在会上说:“我在会上也声明过不要记录,现在不但记了,还散发到旁的地方,而且记得不准确,有很大的严重错误……这算什么马列主义研究院呢?一点纪律都没有。搞了两年了,一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都没有。我打算向中央建议,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关门。”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内中必有隐情。笔者晚年和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成为邻居,在闲聊中王文耀说,“在一次会上,江青质问陈伯达:你管的单位就那么干净,一点问题没有?康生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那当然咯。弄得陈伯达很紧张。他唯恐江青、康生插手研究院,当天晚上就给毛主席打报告,要求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没想到主席看后就同意了,在报告上画了圈。”
研究院撤销后,有的人分到《解放军报》社和总政,有的去了《红旗》杂志社,有的回到了5月新恢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
晚年陈伯达小心翼翼,唯恐被江青等人抓住辫子进行报复
恢复后的政研室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政研室除主任陈伯达外,没有副主任和秘书长,也没有别的官员。工作上的事,史敬棠在管,他的职务仅是秘书。史敬棠,在延安时期就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毛主席处工作,是位高干。秘书曾向陈伯达建议,是否给史敬棠一个行政职务,如副主任什么的。陈说,“不用,不用,就叫秘书。”
陈伯达当时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并无多少实权。江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中央文革开会实际是江青说了算。陈伯达每次开会必须到,但只是挂名而已。陈伯达在1967年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曾一度想自杀。特别是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被否定后,陈伯达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抓住辫子进行报复。这时的《红旗》杂志,虽然他名义上是总编辑,但实权已被姚文元抓去。他唯一可控制的阵地就只剩政研室了。他怕弄出个官来,被江青一伙拉过去,于是连官也不敢设了。
陈伯达倒台,政研室被撤销
1970年八九月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大讲设国家主席和称毛主席是“天才”。陈伯达从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了一些称天才的语录,以证明“天才”之说有依据。加上叶群、吴法宪等人的煽动,打乱了会议布置。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停止各组讨论。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说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欺骗了不少同志”。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并不无夸张地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意见》最后号召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九届二中全会由此改变议程,转为批判陈伯达。9月6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从此,陈伯达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12月22日,政研室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内容是中央成立组织宣传组,撤销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政研室人员的安置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管。
陈伯达出问题后,有人向中央告状,认为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运动不彻底,有许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未挖出来就解散了,陈伯达包庇了坏人。为此,上面从北京卫戍区派来15名军代表,进驻沙滩大院。结果挖了两年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个也没有挖出来,最后不了了之。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军代表撤出沙滩大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历史才最后划上句号。
(摘自《北京沙滩大院百年风云录》,红旗出版社2012年3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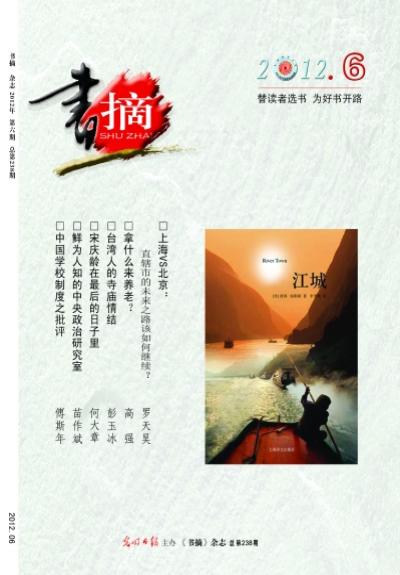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