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为了寻找出路,我离开插队的农村投奔在青海的父亲。青海的记忆很像一首唐诗——“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青海岁月我没人可说。如果用颜色来形容青海的日子,不是红色也不是黑色,那也不是黄,是一种灰白,苍茫高远的色调,想起来就忧伤不已。
我在青海总共住了五百八十六天,占我已有生命的二十七分之一。我记得刚到青海的第一天,就发现父亲的褥子底下全是书,少说也有三四十本,都是很新很新的书。这使我想起以前父亲回北京出差,经常给农场图书馆采购图书。我翻查了青海日记,才发现我过去说的“我在青海只读了两本书(《虹南作战史》与《红与黑》)”是不确实的,虽然只读了有限的书,但是不只这两本。现将有记载的书名及看书的日期抄在下面。
《艳阳天》(1972年8月21日)、《不光荣的权力》(1972年9月3日)、《印度对华战争》(1972年9月8日)、《在人间》(1972年10月2日)、棋书(书名失记)(1972年11月9日)、《中国通史》(1972年11月20日)、《从寂寞中走出来》(1973年2月17日)、《人民画报》(1973年2月23日)、《张居正大传》(1973年3月3日)、《回忆与思考》(1973年3月4日)、《新体育》杂志(1973年3月12日)、《金光大道》(1973年3月22日)、《国外科技动态》(1973年3月28日)、《红楼梦讨论集》(1973年4月3日)、《艳阳天》(1973年4月28日)、《巴金散文》(1973年5月7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73年5月17至19日)、《戈丹》(1973年6月7日至18 日)、《红色保险箱》(1973年6月27日)、《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1973年7月15日)、《朱可夫回忆录》(1973年8月4日)、《水浒》(1973年11月3 日)、《没有号码的房间》(1974年1月8日)、《约翰逊回忆录》(1974年2月10日)、《红与黑》(1974年2月12日:每天看一段)
在青海,我也一样得干活,干的都是下死力气的活,在没有路的荒野中辟出路来。青海的风很大很硬,夜风把帐篷吹倒了,我们也懒得再搭起来,素性把帐篷当作又一床被子,天亮了再说。青海的空气很干燥,缺蔬菜,没水果,嘴唇没几天就裂开了口子,感到很委屈。往砖窑里背砖坯——我认为这是最具屈辱性质的苦力形象——背一趟八分钱(当时正是一张邮票的价值)。还有一个活,挖八十公分见方的直上直下的洞,两米半深,挖一个五毛钱,不是松软的黄土啊,很难挖的,两个人一天未见得能挖成一个。1972年9月11日日记:“晴,太阳还没起来,每个人就必须去打柴禾了。临时工的命在某些人看来就不是命。整个上午就是抬石头,肩头至今还疼呢,总算弄出个模子来了。又添了个人。一共是九员。帐篷,暗绿色的帐篷,走到你的里面的傍晚是经过了多么漫长的白日啊。”
上面说的书都是没活干的闲时看的,可知在青海还是没活干的时候多,也就是说挣钱很难。只有《虹南作战史》和《不光荣的权力》是在工地看的,在第五册日记中查到:“1973年8月30日。这两天把那一段路干完又前进了五十公尺,开始觉得累了。《虹南作战史》还算有点意思.”2005年5月28日我在新购《虹南作战史》扉页上写了一段话:“今日购此书于潘家园旧书摊,同游书友皆嘲笑吾档次低,他们哪里知道这书三十年前曾经帮我排遣夜晚的孤寂。”在第四册日记查到:“1972年9月3日。阴。很早就起来砌石头。上午干活的时候,爸爸乘王师傅的车路过工地,此时此地见到家人,心情又是一样。在炎热的北京夏天说的话活生生的出现了。时间又是无情又是奇妙。下午他们去前面返工,我们几个在跟前干。往后的日子见人心,渐渐艰辛了。近日看了澳大利亚的《不光荣的权力》,还是一本不错的书。”《不光荣的权力》是澳大利亚作家弗兰克·哈代的作品,不是写《德伯家的苔丝》的那个哈代。
近年,得益于网络的兴起,可以很方便地将这些曾经看过的书,仅是出于怀旧之目的,一本一本找回来。只有一本例外,《没有号码的房间》迄今未能搜求到手。这本苏联的书有一个情节我至今记得。一个地下谍报人员邂逅一个姑娘,两人相恋了,就在某一次约会前,谍报人员被捕了,而姑娘尚不知情,谍报人员在牢房里想着失约后姑娘的痛苦。这些曾经在青海慰藉过我孤闷心情的书,只有《红与黑》这一本被我带回了北京,当时从西宁至北京的火车要开整整两天两夜,我没有和邻座说过一句话,一直在看于连和德瑞那的故事,直到火车进了北京站。
在北京呆了两个月我又回到原先插队的农村。在北京我告诉过表哥关于于连被砍头的那段有个问题困扰我,表哥回答不了我。过了许多许多年,知青作家叶辛在一次演说中间接解答了我的困惑:“我也不是特意地挑剔他(司汤达),只是想指出这点来说明他在作品中潜存的浪漫成分.越浪漫,就是他任由自己的兴致来描绘,他愿意笔下的人物应该如此,即使明天要上断头台,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要当近似国务院总理秘书的女儿,另一个是如此高贵的德瑞那夫人)还在爱着他。但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他的浪漫笔法,在最后一章里,他不愿意描写断头的残忍过程,他觉得这么美好的人物不能写这一过程来加以形象的破坏。他就写了玛特尔小姐在第二天去看他了,看到时,身为男人的福格都不愿意去注视,她就是要注视着他。之后她把他的头颅摆在尸身上面,还要亲吻他。不但如此,当她坐着马车送他到墓地时,还把他的头颅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我就不明白,一个人的头颅被砍下来后,有血和脑浆等,如果是现实主义作家必定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了爱情一切都不顾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作家应该写到这一笔。可丝毫都没有描绘过。好像这个头颅是雕出来的一样,放在手里很舒服地带到墓地上。这一小小的情节也能说明司汤达作为一名作家,他毕竟生活在法兰西浪漫主义的上升时期,他的小说中也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面。”同样是上世纪70年代书荒岁月的过来人,叶辛当年的读书水平就高于一般人。
(摘自《书呆温梦录》,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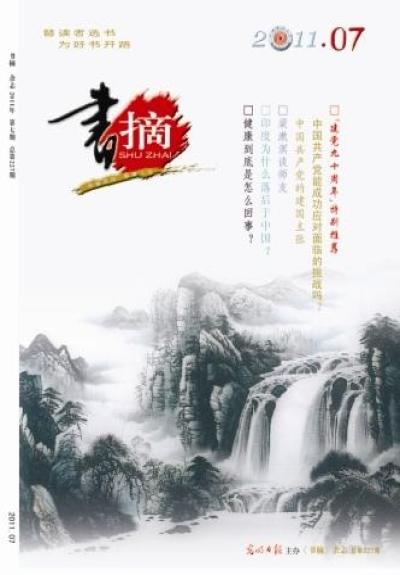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