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我从湖南零陵到衡阳,在热闹的市中心找到我要投奔的目的地:生活书店衡阳分店。
黑底白字的招牌上,“生活书店”,四个标准体的大字是我早已熟悉的。几年前,我在苏州附近吴江县同里镇一家米行里当学徒的时候,我是生活书店五万个邮购户中的一户,又是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大众生活》等几本杂志的长期订户。日军占领我的家乡,逃到上海以后,我多次到福州路生活书店门市部去浏览图书,曾经对佩戴店徽的工作人员投射过羡慕的目光。如今我要把一位地下党员胡大年写的一封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递给书店经理黄宝亢。
我是因为长沙大火而失掉组织关系的。我和党小组长王之屏在大火前一天逃出长沙时,根本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落脚,也不知道我的入党介绍人陈世德将去哪里,不可能带着组织关系逃难。
一路流亡,走走停停,到了零陵,王之屏遇到熟人交通银行秘密党员胡大年,决定停留下来,委托胡大年替我们找寻长沙的党组织恢复组织关系。几个月之后,胡大年给我这封信,要我去衡阳解决组织关系。
我和黄宝亢已经不是初次见面。几个月前,他和赵海青带着几十大包图书,到零陵来开设零陵支店时已经认识了。他们到零陵时,只带书,没有现金。先是摆地摊卖书,有了收入,买了一些竹子、茅草,和着泥巴,雇人修了一间茅草房,书店就开张。我原本是生活书店的老读者,一见“生活书店”这几个字就满怀热情环绕着书摊转。等到书店开张,我帮着搬书、上架、卖书、开发票,跟这两名同乡人交了朋友。这一次黄宝亢看过胡大年的信后毫不犹豫地留我参加书店工作。
衡阳分店只是一间宽不过六七米,进深不过十一二米的单开间门面。店堂中间放一张长条书桌,靠近马路这一头摆放新书,过路的读者一探头就能看到今天来了什么新书。这张书桌上陈列一摞摞有高有低的书,全是比较重要的,越是重要的学术著作,或是文学名著,越要多放几本,造成鹤立鸡群的架势,吸引读者的眼球。
衡阳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时候出版一本杂志《衡阳青年》。当几名三青团员拿着他们的团刊来寄销时,因当时的衡阳分店力求以商业性作掩护,我找不到可以拒绝的理由,只好收下来。等他们走后,我用别的杂志盖在上面。过了三个月,三期杂志只卖掉一本,从此不再来了。
生活书店的门市部一开始就有“好书皆备,备书皆好”的宗旨。衡阳分店经销的是抗日的、进步的书刊,以政治时事读物、社会科学和文艺书为主,有少数应用技术书籍。战时的造货和运输都十分困难,使得本版书品种不全,售缺后往往补不上。外版书中,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书比较多,还有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署名莫师古翻译的(在上海翻印的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中文版。莫师古是莫斯科的谐音)《国家与革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左派”幼稚病》等等。
当地一位姓向(或项)的朋友使用五洲书报社名义翻印莫斯科中文版《论政党》、《列宁主义初步》也拿来寄销。生活书店出版的《救亡文丛》是一套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论著,有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潘汉年的《全面抗战论》、李公朴的《民众动员论》、胡愈之的《抗战与外交》等等,在当年曾经畅销一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光明书局在上海印的书也有一些,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夜》,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没有业务往来,更不用说广益书局之类的书了。开明版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高尔基的《母亲》是青年读者喜爱的书,可是多次开出添货单,一本也没有发来,可能是战时造货和运输上的困难。
整个门市部除收银柜处有一张凳子外,没有第二个可以放放屁股的地方。所以在营业时间是不可能坐下来休息的。
衡阳分店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店堂后面是书库,四周靠墙是书架,中间的一张桌子是我做轧销的地方,又是吃饭的桌子。那时不管有多少人吃饭,每个人都是端着饭碗,环绕着桌子,站着吃饭。这是战时生活的一景。(1940年我到桂林《救亡日报》工作,报社的工作人员,包括主笔夏衍,也是端着饭碗一起站着吃饭。)
衡阳经过几次大轰炸之后,市民们一早起床见是晴天,便急匆匆吃罢早饭,涌到城外去。当时把这种行动叫做“跑警报”。“跑警报”要跑到城外丘陵地带,找一个“三面好”(可以躲避从三个方向飞来的弹片的死角)的地方,晒几个小时的太阳,下午回城,三点开门营业。有一次日本飞机把城内有巨大的红十字标志的伤兵医院给炸了,衡阳分店距离伤兵医院不远,黄宝亢决定疏散书库里的存货,在城外村子里租了一间房子。又把一些过期杂志与多余的滞销书退给发货店西南区管理处。
把我调到门市部,我很乐意投入这个书的海洋。过去许多年只能在图书目录上见到的书,现在随手可以触摸。战时的衡阳,上门的读者零 零落落,有充分的时间让我翻阅新书的前言、后记,熟悉作者、译者。一名作者写过几本书,一本书有几个译名,都是一名门市工作者应该知道的。
门市部的书有二千来个品种,一名门市工作人员,只要勤奋工作,经常整理书架,要记住书架上有哪些重要著作,记住书名、作者、定价是毫不困难的。熟悉了书和作者,又是经常留意文化界动态的工作人员,才有和读者交朋友的资格。接二连三上门的读者一般都是读书人,他们读的书比当年衡阳分店的几名小青年(包括我在内)多得多,跟这样的读者谈天说地交朋友,可以增长知识,又可以拉住读者。
生活书店深受读者的爱戴。有的老读者逃难到衡阳,偶然间看到生活书店的招牌,必定要进来看看。他们会像面对一名老朋友那样倾诉他们这两年来的苦难历程。那年头在大后方流行这样一句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种落难在异乡的感情,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见到。
当年衡阳分店的读者大体上有三类人:从东北、华北、江浙一带逃难来的,其中多数是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少数是缺衣少食的老弱妇幼;其次是军人,有当地驻军,有从前线下来休整的,也有在伤兵医院治疗的;再有就是本地的湖南老乡。
这一年,我写过一篇《平凡的一天——衡店门市剪影》,发表在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內部刊物《店务通讯》上,这篇小东西给当年的衡阳分店留下一个剪影。
写入《平凡的一天》的是门市工作的形形色色,然而不是全部。因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有些事是不能写成文字印出来的。例如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他们逃出沦陷后的上海,决心投奔延安,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一说延安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他们只相信生活书店。我看着他们的模样,相信他们是热血青年,我就带他们去到城外一个村庄里找到十八路集团军驻衡阳办事处。又有一天,几个年轻军官要买茅盾、巴金、张天翼的小说,东北口音,是流亡青年。我问起前线的情形,这一下打开他们的话匣子了。他们异口同声咒骂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说他们几个是凭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参军,却是投错了地方,现在想退出不容易了,等等。
读书人偷书,当年也是有的。有一天吃过晚饭,我回到门市部,发现书架上的《希腊神话》少了一部。此书上下两厚册,黄书脊,是在上海印的,比在重庆、桂林用土纸印的书整洁、挺拔,特别可爱,一共有两部。我查了发票存根,又问了门市部的同事,没有卖过,显然是被偷了。我注视着门市部的几位读者,发现一名青年的胳臂很不自然,我悄悄地跟着他跨出店门,走过几个店面后,他从衣服里面抽出两本书来,正是《希腊神话》。
我把他带回书店,为避免引人注意,又带进书库,追查过去被偷的书。最后他答应回家去把过去偷的书全部归还。我跟着他走到一片日机轰炸后留下来的瓦砾场,在分不清街道和住宅的黑暗中,他叫我留步。他是一名从江浙一带逃难到衡阳住在一个亲戚家里的失学青年。我同情他的处境。等了一回,他递给我一摞书。其中一半以上,如巴金的《家》、《灭亡》,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文学名著》等,不是衡阳分店丢的。这一摞书告诉我,这个青年的确如他自己说的是一个爱好文学的穷学生。
我进衡阳分店时,店里有两名中共党员。经理黄宝亢,门市部一名小青年李道生。我到书店的第二天,黄宝亢带我到郊区一个村庄,找到负责中共衡阳地区文化支部工作的李华揖同志,替我接上组织关系。此后,又增加一名女同事欧阳晶(欧阳文彬)。我们几个地下党员就在李华揖居住在乡村的砖瓦房里秘密过组织生活。
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通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制造平江惨案,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活动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有一天李华揖到书店找我,传达上级指示:在新形势下停止小组活动,采用单线联系。凡是已经半公开的党员都要转移,他和李道生要去延安。李道生是本地人,李华揖的侄子,是一个活跃分子,我刚接上组织关系,他就要带我到郊外村子里去探望徐特立老人,十八路集团军驻衡办事处的地址也是他告诉我的,所以他非走不可。我留下来坚持工作,因为我到衡阳不久,并未引人注意。此时,黃宝亢因肺结核病吐血不止,已离店休养,欧阳晶已去桂林,在书店里只有我一名党员了。
几天之后,另一位年轻同事陈风九悄悄告诉我,他要去延安。当时国民党为了阻止大后方的青年涌向革命圣地,在去延安的路上到处设卡捕人,所以陈风九只能偷偷地告别书店。
李华揖临别时给我一个暗号,约摸过了半个来月,一个小个子的中年男子拿着一本卷着的《世界知识》杂志来到书店,在书架前来来回回浏览书籍。这是李华揖布置的接头暗号。我用惯常招呼读者的模样帮他找书,悄悄地通报我的姓名,他约我第二天跑警报的时候在城门洞见面。每天跑警报时,关心战事的人路过城门洞,通常会停下来看看墙上的《大刚报》。用这样的形式见面,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见我来到转身就走,我跟着他混在跑警报的人流里,在广阔的田野上,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由他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八路军的战绩等等。我遵守秘密工作的准则,从来不问他的姓名、住址。他也不过问我在书店的工作。有一次,他布置我在指定的日子到耒阳,找到某军文工团的一位团员,告诉她:“舅舅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了。”说完这句话我就告辞。不必猜测,也不应该探问,我至今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意思。
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之一是对进步文化出版业的压制与对进步书刊的封杀。继1939年3月封闭浙江天目山的生活书店营业处之后,接二连三将西安、南郑、天水、沅陵、金华、吉安、赣州、宜昌、丽水、本溪、曲江、南平等地生活书店的分支机构一一封闭或勒令停业。工作人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驱逐出境。邮局里增加了邮检人员,从此,衡阳分店寄往外地包括本省的或是外省江西、浙江等地读者的邮包全部被没收。
幸好,我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歌咏队唱歌时认识了邮政局的两名职工,他们既是爱国的流亡青年,又是书店的读者。在他们的帮助下,选在邮检人员出外吃饭的时候送去邮包,立即封入邮袋,由此逃脱这一罪恶的黑手。
可是,衡阳分店没有这样的幸运,继本省的沅陵、常德分店之后,在1940年2月5曰下午七点左右,一群衡阳警备司令部的武装人员端着枪冲进书店,大呼“不许动!”后面跟着警察和衡阳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人员。他们冲到后面的书库,又冲进厨房,冲到楼上,几名便衣在书架上搜查禁书。搜到深夜,作为罪证被拿走的有一对在白色的枕套上绣着红色镰刀斧头的枕头。整个衡阳分店11名职工,包括接替黄宝亢的经理金伟民,烧饭师傅,还有从吉安、沅陵、曲江等地逃到衡阳来的职工全部被捕。
我因为收拾收银柜里的现金,最后一个离开书店。我在跨上囚车的一刹那,回头看到几名警察正在门上贴封条。悬挂在头顶上的这把中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来了。
(摘自《出版生涯七十年》,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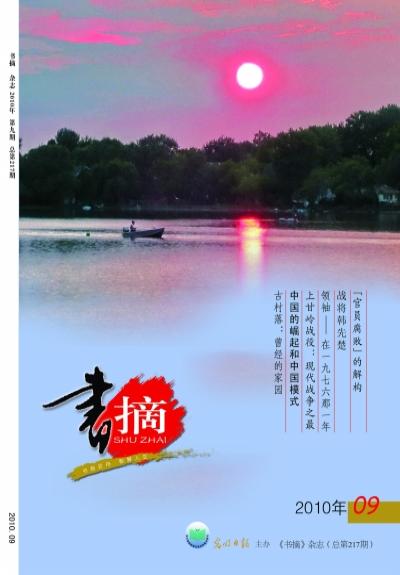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