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钓鱼台220号,高大结实的铁门,高大的院墙上拉着铁丝网。进门一条水泥路将院落一分为二,左边为四幢二层楼,右边为菜地。南边紧靠院墙两个篮球场大小的一块地,是1号楼韩先楚家的菜地。葱、蒜、茄子、辣椒、黄瓜、丝瓜,应有尽有,田埂上还长着一些黄花菜。
1997年和1998年两年,韩家的这块地是最荒的。秋天,种着玉米的一畦田里,玉米一人高,那草高处没膝深。
韩先楚在世时,正好相反。
每天清晨,韩先楚起床就下地了,去他的菜地。那一畦畦各种蔬菜,从播种、耕耘到收获,他筹划,他侍弄,他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不许有一棵杂草。横是横,竖是竖,他侍弄它们就像操练军队,一畦畦小苗就像一个个绿色的方队。他知道第一朵茄子、辣椒花是什么时候开的,知道一条条大小不一的黄瓜、丝瓜都长在什么地方,他看着它们就像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最激动的是第一次收获的时候,最幸福的是把它们送人的时候:吃吧,吃吧,没有化肥,没有农药,从里到外都是绿色的。
有人说:不光别人,就是他自己,到头来才发现,一代名将原来还是个农民。
是吗?
韩先楚由兰州军区司令升任军委常委不久,即负责全军人事安排。
如今的东钓鱼台220号院,那路灯有的没有灯罩,有的连灯泡都没了,冷冷清清。正对着大铁门的那条胡同,路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下雨积水不说,还挺脏的。有时一些建筑垃圾也堆放在那里,占去近半个路面。不知当年是个什么模样,但上世纪80年代初进出东钓鱼台220号的车辆,大都是奔1号楼韩先楚家的,则是肯定无疑的。连多少年见面招呼都难得打的人,这时也登门拜访来了,一口一个“韩常委”,叫得热情而又亲切。负责全军人事安排,意味着多少人的命运,也就是乌纱帽,抓在“韩常委”的手里,怎能不让那些惯于跑官、要官的人心动而奔波忙碌呢?而这种职务与分工本身,又说明上边对他这位“韩常委”,是多么地信赖而又器重呀!
他却有些不习惯,不适应,甚至不识抬举。
在谈到某一职务时,有人提出一个人选,韩先楚有些不快。一是这个人选不合适,二是这个人选不是提名者的亲属吗?他知道自己不是个“政治家”,就竭力在心头命令自己克制,但脸上却把什么都写出来了。
人家却像毫无知觉,不愠不火,愈发和蔼而又亲近起来:老韩,你再想想,你有什么人也是可以考虑的嘛。
韩先楚终于拍起了桌子。
不久,他就去人大常委会了。
他不想去人大,干脆直接回家算了。陈云劝他还是去吧,这才去当了个副委员长。
一个一辈子干实事的人,那感觉就像辆疾驰的汽车,突然被人拉了急刹车。
他忽然悟到,他这种人,原本就不是当京官的料。
想来,他也是有“野心”的。第一仗打下来不久当了排长,就想当连长。当排长背长枪,当连长挎驳壳枪,枪把上再拴块红绸子,那是什么气派?后来,特别是到东北后,那一次次战前的“方案之争”,实在让他伤透脑筋。那可不是挎支驳壳枪再拴块红绸子了,那是直接关系到战斗、战役的胜负呀!那时就想什么时候我说了就算,没了这些唇枪舌剑的,多好呀!1947年秋季攻势后好多了,他当了3纵司令,成了一方天地中的“1号首长”了。可海南岛战役呢?作为下级,作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要想说服领导按自己的意见行事,那实在就是天底下最难办的事情之一了。可从长白山到海南岛,直接、间接领导,除了林彪,有谁没被他“不”过?正因为如此,尽管他这个“好战分子”不招一些人喜欢,却也非用他不可,因为用他打仗放心。战争毕竟是非常实际的。而和平时期,会当官的人有的是,谁会喜欢一个不听摆弄、总爱说“不”的人呢?1953年回国不久就读书,毕业就主动请缨去了有仗打的福建前线。他再爱说“不”,也毕竟是一方诸侯,天高皇帝远。如果他这个副总参谋长就留在北京,这个天生就是带兵打仗的人,是不是早就一巴掌把自己拍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放牛娃到将军,他知道带兵打仗是来不得半点虚妄的,也知道百姓大众是说大实话的。可人家那种举“贤”不避亲,不也是大实话吗?
更令他莫名其妙,又无限惆怅的,是一个戎马一生的将军,怎么一下子就去了人大?这与他的人生轨迹,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
战争年代,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指挥所、前指。和平时期,福州16年,一有风吹草动,不管什么时候,他准在作战室里。1979年初,在南疆自卫还击战的日子里,他就在兰州军区作战室里,对着地图,遥望南天。
“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而今,再也没有作战室了,再也不会有作战参谋把他从睡梦中摇醒,不管半夜三更,还是风雨交加,披上衣服就往作战室奔了。
窗外,硕大的泡桐树叶子打着旋儿飘落着。他打开箱子,把那套上将军礼服取出来展开,凝视着那对肩章和上面的三颗金星。自1965年取消军衔后,每年秋天,他都要把它们翻出来,放在室内窗前晾晒一下。
他希望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时,能穿着这套上将军礼服,去见马克思、毛泽东、吴焕先,以及那些知名的、不知名的、战争年代牺牲的和后来病逝的战友。他还说过,死后要葬在父母身边。可这一切,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曾想解甲归田一样,是可能的吗?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特别是9号文件后逼他检查“路线错误”时,也曾想到毛泽东的这段话,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而今再想,甚至不用想,就通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俯仰无愧,这就是了。
无私与刚毅,原本就是他的性格和生命的一部分。
读中学的,读小学的,孩子们放学回家,或是星期天、寒暑假,家里、院子里、操场上玩得那个开心哪。韩先楚羡慕得摇头叹气:你们真是快活死了,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开心哪?
一个大军区司令,是难得有8小时之外以及星期天、节假日的。他总是显得那样从容不迫,是因为他的脑子一直都不闲着,对任何事情都有个一、二、三,乃至四、五、六。
在朝鲜时兴起跳舞。那时什么都学苏军,跳舞好像也是。在山洞、坑道里跳,环境好点,就找间大房子,用布把窗户蒙上,点起汽灯就跳。文工团的女同志称之为“执行任务”,大家共同的称谓叫“夜行军”——一个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军人随手拈来的生动形象的比喻。这支堪称世界上最善于夜行军的军队,一些人一来上这种“夜行军”,那瘾头才大呢,四步、三步,有机会就跳,乐此不疲。志愿军总部,一个是彭德怀不跳,再就是韩先楚难得一跳。“好战分子”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喜欢打篮球。他是到延安才见到篮球的,见到就爱上了它。在东北,战争间隙,驻地附近有球场,有时就情不自禁要忙里抽暇组织一场球赛,他自然是要上场的。虽然只有一只手管用,却是久经锻炼,比一般人的右手格外粗壮有力,加上身段灵活,带球、传球、投篮,什么也不耽误,而且命中率颇高。
还爱打猎、钓鱼。患病疗养,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武汉东湖宾馆。一是他是“九头鸟”,二是那里是打猎、垂钓的天然去处。宾馆那只大花猫都习惯了,一听到枪响就往外跑,有鸟吃了。钓鱼,把鱼钩甩进水里,岸边一坐,就凝神等待、感觉去吧。那种大鱼咬钩时的冲撞涌动,通过线杆像电流般传感到心头,冲撞得他心花怒放。那种快感和激动,是只有战争年代一个十拿九稳的歼敌方案成熟了、如愿以偿了,才能与之媲美的。
最喜欢的还是土地,是侍弄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使人们得以生存的庄稼和蔬菜。
从福州到兰州,再到北京西山和东钓鱼台220号,他家都有块菜地,主持福建工作后,他家还养了只猪,并要求军区领导都要养猪。住在马鞍山腰,有这个条件。猪肉当然可以吃,粪肥除了自家菜地用点,大都送给附近生产队。将军楼配个猪圈,虽然不雅,却很实际,一举多利。
年纪大了,篮球早就不能打了,打猎也不大行了,钓鱼坐上两个小时,身子骨也不像过去那样好使唤了。看电视,“新闻联播”雷打不动,每天必看的;再一个是“动物世界”,到时候就坐到电视机前了。不爱看电视剧,他觉得那剧中人,怎么还不如“动物世界”里的猴子、大象有人情味儿?而几十年始终如一,而且愈来愈有魅力的,就是那片菜地,是那些翠生生、绿油油的茄子、辣椒、黄瓜、丝瓜。
不过,比起墙上、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就铺到地上的那些军用地图来,这一切就都不在话下了。
在地里侍弄菜,吃饭了,喊一声,他站起来,拍打拍打手就回来了。顶多回一声,待我把这点弄完了。若在房间里看地图,喊几声也难听得到回音,有时干脆就听不到别人喊他。有时戴着老花镜,有时拿着放大镜,就那么看呀看呀,在屋子里转呀转呀。有时一看就是半天,有时还要锁上门,锁不锁门都不许人打扰他。
不了解他的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解他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却也不免在心头嘀咕:还看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银山动地来。”站到地图前,一看到那些指纹似的等高线,呼吸就有些急促,周身的热血就一阵阵沸腾起来。那泥泞路上的跋涉,那冰冷堑壕中的据守,那枪林弹雨中的攻击,那血与火的岁月,历历在目,声声在耳,像刚刚发生的一样。
从大别山到陕北,从长白山到海南岛,再到朝鲜,又从福州到兰州,末了,那目光有时就又停在了大别山南麓那个叫“红安”的地方。
最后一次回红安,闵永进、陈尊友几个儿时伙伴,说他们想去北京看看皇帝的金銮殿。不用说,他也知道他们会这么想的。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还有什么比金銮殿还至高无上的地方?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城看的第一个地方不就是故宫吗?但他永远也说不出闵永进那样的话:看了皇帝上朝的地方,这辈子值了。
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乡苏维埃土地委员。这个职务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农民为什么造反、革命?不就是为了土地吗?他扛枪打仗去了,不再是扶犁肩锄的农民了。但他若不曾是个农民,就不会走到哪里,都在房前屋后种菜。而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人和将军。
许世友在南京时,住的是当年孙科的房子。孙科是何等人物,那是何等房子,“许老板”却把一些花草刨掉,种上玉米、蔬菜。“许老板”也爱花草,他来兰州时,“许老板”说那地方荒凉,特意送他五盆花。可“许老板”也是农民出身,像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看到土地,首先想到的是土地可以种庄稼、打粮食。可这就能改变他那军人的本性吗?
当年,战友们经常唠起革命胜利后干什么,绝大多数都说回家种地。已经挎上了拴块红绸子的驳壳枪的韩先楚,也这样说。可当上营长不久就变卦了,拍拍那支驳壳枪的枪套: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1966年12月,中央给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发来电报,“增补韩先楚同志为福建省委书记”。想了几天,他连着给周恩来、林彪、陶铸打电话,问这项任命主席知道不知道,若是主席不知道,他就准备推掉,请中央另行选人、派人。不是因为动乱年代,今天上台,明天打倒,而是这项任命实在是赶鸭子上架,他根本就不是干地方、抓经济、搞运动的料。末了,他说我服从中央、主席的指示,但是一旦省委比较主动,形势缓和后,我还是要做军队、抓战备工作。
有人渴望在军中,是为了军人的特权、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不便说出、也不需要说出口的原因。韩先楚把军人作为自己追求的唯一目标,并愿永远服务其中,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军人这个职业是一种能够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而他也天生就是来干这个的。
1985年春,已经调去国防大学的韩先楚的秘书杨旭华,来东钓鱼台220号看望老首长。军队刚刚换装,杨旭华头戴大盖帽,身着没有军衔的85式制服。正在菜地里忙活儿的韩先楚,开头竟没认出来。
他在地头的水龙头下洗了手,擦干了,瞅着,又摸摸衣服质地:好精神!
又道:有军衔就更好了。
杨旭华告诉他:团以上干部都是毛料。
韩先楚笑笑:我是没毛了。
又像是自言自语:如果我能授衔,现在该是什么了? (摘自《战将韩先楚》,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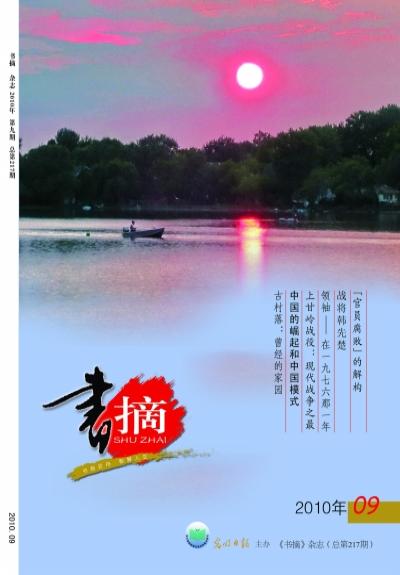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