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朋友跟着我进茶馆,看那么多女人闲坐在那里,或聊天,或不聊天。不聊天的,有的看报纸杂志,有的端个小镜子看自己。又是夏天,女人多是吊带、短裙,白花花的腿和肩。朋友于是被惊了一下,小声问我,这些女人都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都有。老板、干部、白领、教师、画家、歌手、开铺子的、卖衣服的、编报纸的……还有一些我这样的,写字的。
成都女人,甭管干什么的,如果有空有闲的话,都喜欢泡茶馆。
在其他很多城市,茶馆这个有点男性化倾向的公共场合,一般来说女人是不好频繁露面的。在很多北方城市,老太太除外,很难想象所谓的正经女人会三五成群地经常去泡茶馆。
但在成都就是这样,泡茶馆的习惯几乎涉及各个层次不同领域的女人,这跟被称为美食之都的这个城市在餐饮上全民共享的风俗是一脉相承的。
成都女人泡茶馆的习惯由来已久了。在成都籍美国学者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中,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考证说,1906年,成都第一家带有商业性演出的茶园——可园,成为首先允许女客进入的茶馆,之后,几家大茶园比如悦来茶园、鹤鸣茶园等,都开始接受女宾进入。之后,几乎所有的茶园都开始接女宾。刚开始,女宾要从另一个门进出,座位也和男宾隔开,但不久这一方式就失效了,很快就出现了男女杂坐共同喝茶观戏的局面。成都竹枝词一贯杂咏新鲜风物,有赞此景的诗曰:“社交男女要公开,才把平权博得来。若问社交何处所,维新茶馆大家挨。”另外,还有诗云:“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
鲜活佻达的市井气味,卫道者历来是要掩鼻的。成都女人进入茶馆的过程,中间也经历了不少波折。官方时不时会出台一些禁止令,比如可园接纳女宾后不久,曾经被禁过;1913年,官方颁布过《取缔戏园女座规则》(成都的戏园和茶园从来是合二为一的);而当时所谓的一些精英文人们也竭力抨击这一“伤风败俗”的现象,指责“女宾嬉笑撩拨男宾,秩序大乱”,还有一则说法很有趣,说是妇女们对“改良新戏,文明新戏,全不爱听。哪个园子有淫戏,哪个园子多上女座……《翠屏山》偷和尚,《关王庙》解衣拥抱,《珍珠衫》乘醉诱奸的时候,女座眼也直,男座眼也斜。一边喝彩,一边回顾”。一众“社会精英”为此现象忧虑良久,不得解脱。
成都女人会在20世纪初那个封闭守旧的大环境中流连于茶园这种公共场所,其实与这个城市的女人历来的气质有关。成都女人,大胆、放松、娇俏和刁蛮集于一身。她们很早就开始出入公共场所,市场、寺庙、节日集会等,都是她们乐于出入的社交场所。这一点,在李劫人先生的著名小说《死水微澜》里也可一观:邓幺姑和罗歪嘴之间的感情萌动就是过节时在成都街头发生的。那是20世纪初清末的故事。学者伊莎贝尔·贝德在19世纪末进入成都时,惊奇地看到“高大健康的大脚女人,穿着长边外套,头上扎着玫瑰花……她们站在门口同朋友——有男有女——聊天,颇有几分英国妇女的闲适和自由”。后来有学者分析说,贝德所看到的,可能是满族女人,而非汉族女人。但不论怎样,这种无拘无束自由浪漫的天性,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已经植根于成都女人的血脉之中了。
我问那位外地朋友,女人泡茶馆怎么样?看得惯吗?那位仁兄笑得合不拢嘴,说太看得惯了!那倒是,茶让他享了清福,四周的女人让他享了眼福。有必要多说一句的是:成都,是个美女如云的城市。
(摘自《半如童话,半如陷阱》,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2月版,定价: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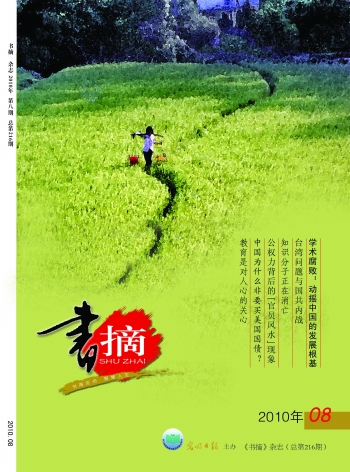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