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泗原先生见过很多面,衣着朴素,看上去很干瘦,愁容满面,虽是长者,却不多见言笑。享誉学界,后来也有人以国学大师头衔相赠,与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相比,这位王泗原还算不上大名鼎鼎。他是祖父的老部下,也是祖父最信任的人,有人甚至把他戏称为叶圣陶的左臂右膀,年龄要比我伯父还大,应该是比吕叔湘先生略小,如果活着,差不多也有一百岁了。
王泗原送父亲的书,居然称“至诚”兄,这让人觉得很搞笑,父亲也觉得太过客气,毕竟他要比父亲年长许多岁,而且学问太高太深,而且他是那样的严肃,因为严肃和不苟言笑,要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很多。说老实话,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王泗原出生于哪一年,上网去搜索,没想到宣传条目不少,吹捧文章也有好多篇,出生年月还真一时找不到。
上世纪80年代,祖父病重住院,院方规定每周只有三个下午可以探视,王泗原关心祖父的病情,又不愿违背医院规定,便改成每天去家里咨询,向轮流陪同祖父的家属打听情况。照例是问昨晚睡得如何,体温可好,胃口是否开了,然后说一声这很好,也不喝一口茶,就心满意足地走了。大家都觉得这老头十分古怪,天天都如此,其实打一个电话就行,可是谁也不敢这么提醒,有些话一说就俗了。说给祖父听,祖父也很感慨,只能用“真是个古人”来评价。
我考上大学,祖父很认真地说,我们老开明的人,是看不上什么大学生的。这话伯父说过,父亲也说过,让我觉得很奇怪,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明白什么意思。祖父不是大学生,伯父和父亲也不是,狭隘地想,因为他们不是,所以难免有吃不着葡萄的心理。后来明白不是这样,对于老一代人来说,不上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譬如祖父就是因为要养家糊口,没钱上大学,伯父因为高考时患猩红热耽误了,父亲上了大专没几天就去革命。按照我的傻想法,大学之门进总比不进好,有无学问,与上大学并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世上有文凭的人多,大学生研究生如过江之鲫,真有学问的人太少,以学历和文凭取人,看走眼是经常。
其实执著于文科的人,完全可以在家自学。王泗原倒是考上过大学,因为家贫,很快退学,他的学问功力,一方面得以家传,一方面全靠自习。说到学问好,祖父经常称赞与自己相熟悉的两位,一位是吕叔湘,另一位就是王泗原。坦白地说,我最后没有走上做学问的道路,既与喜欢写小说有关,也与那些有学问的人太有学问有关,活生生地是被吓住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去做学问,这两位实在是太认真太厉害,认真得让人没办法效仿,厉害得可望而不可及。学问是人做的,然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
王泗原出身名门,世代书香,祖父王邦玺是进士,写一手很好的字,与湘人名流王先谦同科,曾任国子监司业及光绪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也绕不明白这“司业”和“行走”究竟是多大的一个官,反正是在皇帝身边,侍候着天下第一号人物,有很多可以说的掌故。王泗原偶尔也会透露一些,譬如关于老佛爷慈禧,与外面传的就不太一样,听上去更像一位邻居老太太,我父亲生前常说,王泗原要是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事都写出来,会非常有意思,可惜他并不太喜欢向人家卖弄这些破烂。家道中落是乱世的必然,王泗原的祖父得罪了李鸿章,然后就是被贬,告老还乡。老人家讲经学,在王泗原出生时已过世,因此对王的影响并不太大,影响大的是父亲王仁照,他当过师范学堂的监督,这职务在晚清相当于校长,讲究文字音韵训诂,教子甚严,教导儿子的首要认识,就是“做学问是一种责任”。
王泗原做过小学和中学老师,做过很长时间编辑,这两项工作都很普通,却说明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脚踏实地,都可以做出非同寻常的成绩。当然麟角凤毛,通常只对老派的人才有效,真正脚踏实地,不受人间影响和诱惑又谈何容易。现如今中小学的师资队伍,多如牛毛的各路编辑,真正能做出王泗原这样学问的人,怕是再也找不到。时乎时,不再来,时代变了,人也全变了。我也说不好王泗原有多大学问,只好借别人的眼光,我祖父的观点不能完全作数,那就说一说张中行先生的评价。张中行是老北大出身,积累很厚,学问过人,又是王泗原几十年相处的老同事,评价可算是知根知底。他觉得王泗原“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压倒古人”,觉得他的文章“不读书破万卷就写不出来”,因此,那些想走上古典征途的人,请先细心读读王泗原的书,“当作厉兵秣马,以免仓卒登程,碰到小小坎坷就摔倒在地”。
最早见到的是《离骚语文疏解》,这是王泗原的第一本书,显然是一本很难读进去的书。虽然至今我还能马马虎虎地将《离骚》背出来,可是对于这本“疏解”,还真是一读就坎坷,一读就明白自己的学问太差。在书的空白处,王泗原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对祖父表示谢意:
圣陶先生:
这本书出版了,我带着感激,拿第一本样书送到您的面前。
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您从我交给组织上的自传里知道我写了这样一本书。您亲自到我办公的地方,亲切地问我,说想看看。我写信到上海取来,请您教正,您看过了,说可出版,并介绍到开明书店。您多次谈到它,有时候有一两句称许的话,我听了只低着头,不能说什么,我不敢用虚文来对答您的那样质朴的话。稿子整理过后,适逢开明书店出版方针变更,您又介绍到俞平伯先生和文怀沙先生。付排以后,每一次见面,您总是很关心地询问排校的情形。您想到这本书的时候比我自己还多。这使我深深感念,永远不忘。
泗原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
祖父对王泗原的欣赏非同寻常,常以平生获此得力助手而自豪。这段文字还可以续写下去,一九七一年,跟钱钟书先生一样,王泗原也从干校回到北京,在与祖父的闲谈中,说起昔日研究典籍的种种独特感悟,祖父觉得很有意思,力促他将这些感悟写出来。当时环境下,写下这些感悟,基本上自娱自乐,至多也就是惠及友人同好,因此王泗原也根本无意写作。因为祖父的建议,他“勉思所以报命”,把它们当做随笔写,或长或短,每写了一二十则,便送来给祖父看,让祖父提意见。起初是十六开白纸钢笔写,每则另页,后来写多了,有些零乱,祖父很喜欢这类文字,提出要分类装订,自告奋勇乐意为他效劳。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一来一往,就是很多年,祖父对这些文字始终“深致奖誉”,渐渐老眼昏花,王泗原又改毛笔纸墨,用大字抄录送来让祖父过目,再到后来,祖父目力更加不及,只好改为口述,每次三五则,一句一句议论。
终于完稿,终于成书,这就是后来让学界感到震惊的《古语文例释》,所谓集四十年之深厚功力,洋洋洒洒的四十万言。王泗原就先秦两汉典籍的疑难问题,一一做了辨析,提出正确的解释,对真正有志于研读古籍的人会很有帮助。王泗原著作并不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还有一本《楚辞校释》,凡是熟悉王泗原的,无人不敬佩他学问精详。然而他的过人之处,还不仅仅是古汉语的研究深入,现代汉语的功力也是十分了得。
王泗原的白话文非常漂亮,打个不恰当比喻,就像毛笔字的一手正楷,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多年来,他一直在从事教材的编撰工作,当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手云集,谈笑皆鸿儒,王泗原之外,还有张中行,还有张志公,还有隋树森,都是一时俊杰,他们这些人为语言文字所做的努力,默默无闻的贡献,远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道白。还是用一句最简单的评价,人教社的教材关系到全国的中小学生,只要是“王泗原看过的稿子,大家就放心了”,他是把守文字大关的最后一个守门人。
王泗原曾当过胡耀邦的家庭教师,每周上门为其授课,自然是有专车接送,但是他坚持只在远处的胡同口上下车,不让接送的小车开进胡同,以免过分张扬。这就是他最典型的迂腐之处,胡耀邦敬佩王泗原的学问,执弟子礼甚恭,他却从不以此为炫耀,终生不改布衣本色。
(摘自《陈旧人物〈增订本〉》,上海书店2010年1月版,定价: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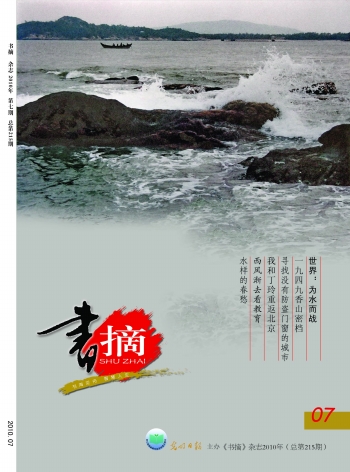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