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与恢复党籍
1979年1月我们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到位于和平里的文化部招待所住下。当天就有很多人来看我们,以后几天,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许多年不见,话是说也说不完的。春节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第一次在北京团聚了,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还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春节联欢会。
我们回来后,一方面是跑医院,看病,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解决政治上平反的事情。丁玲尤其着急,她的问题由作家协会处理。作协的负责人没来,只是秘书处、复查办公室的几位同志来看过丁玲。作协几位上世纪50年代的秘书在做甄别工作,他们对丁玲说:你的事解决没有问题,只是对当年的几位领导人还要做点思想工作。他们都是这么讲的,我们也不是很着急,知道这些事情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些手续,也是很麻烦的,所以就等着,我们很体谅他们。
我们心里明白,虽然“四人帮”已经打倒了,但是事情还是复杂的,天下并不太平,许多事情也并不那么简单。
我们写给中组部的那些申诉信,都转给了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当时,张僖是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而且他是老作协的人,上世纪50年代就在,情况都比较熟悉,所以都是他来跟丁玲谈。5月初的一天,张僖送来了《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但在丁玲的历史问题结论上,他们就是不肯改正。
大概是因为丁玲对她的历史结论有意见,恢复党籍的事情就迟迟拖着。后面的恢复原工资级别,适当安排工作等等,就一直没有消息。这时,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要开会了,6月份,张凤珠和戈扬来了,她们说是受了作协组织上的委托,来通知丁玲,第四次文代会计划在7月间举行,要她准备在会上作一个发言。丁玲就说,我还没有恢复党籍呢,我应该以党员作家的身份参加这个大会呀。后来文代会延期,丁玲就写信给作协党组,要求恢复组织生活,应该以党员作家的身份参加文代会议,而不能作为一个非党作家来参加这个会。可是作协党组没有答复。第二次又写信,丁玲一共给作协党组写了三封信,但是都没有回音。最后,丁玲把信抄了一份给中央宣传部,那时胡耀邦已经到中央宣传部了,10月间,胡耀邦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中宣部的宣教局,催促他们联系中央组织部加快办理。
10月下旬,我记得是10月二十几号,中央宣传部通知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通知了作协党组,通知是写给文代会核心小组的,说鉴于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丁玲同志已当选为代表,请先自即日起恢复其党籍,恢复其组织生活。这样才恢复了丁玲的组织生活。
后来到了1985年,丁玲病重住到医院的时候,张僖到医院去看丁玲,我问他,为什么1979年我们回到北京以后,作协党组老不给丁玲恢复组织生活呢,难道没讨论过吗?丁玲写过几次信啊。这时他才告诉我,丁玲恢复组织生活这个事,作协党组讨论过。他们一直是压制丁玲的,不让丁玲出来,总想给丁玲带条尾巴。所以丁玲恢复党籍不是一帆风顺的。
周扬总是说,你说丁玲不是国民党派到延安去的,但是她在延安是暴露黑暗派啊,丁玲历史上的疑点可以排除,但是污点还是有的嘛,她和冯达同居那么长时间,冯达是特务啊。他总是要在这些地方给丁玲安个尾巴。冯达是不是特务呢?也没给他做结论。
与周扬的关系
当年把丁玲和我打成“反党集团”,这里面周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有很大的责任。现在拨乱反正了,我们已经平反了,周扬不仅没有承认错误的表示,而且还在继续坚持他的错误,阻挠中央组织部给丁玲彻底平反的决定。
1979年春天,《新文学史料》上面刊登了一篇文章,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写的访问记《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原来刊登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面的。那个访问记里说,周扬告诉赵浩生:“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
其实赵浩生的这篇文章我1978年12月到北京来的时候就看到了,那还是在外文编译局的一个内部刊物上看到的。我们原来还以为,周扬出来以后,第一个平反的就会想到丁玲,因为他对丁玲的问题最清楚,最了解,而且他也有责任。但是后来在报纸上杂志上看到三篇文章,心里边就清楚了,周扬不会给丁玲平反的。第一篇,讲姚文元是丁玲的儿子;第二篇,讲鲁迅《悼丁君》的诗,是痛斥丁玲叛变自首的行为;第三篇,就是赵浩生写的访问记《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这时我们就完全明白了,指望周扬是指望不上的。
我们还在山西的时候,丁玲的女儿祖慧去看周扬,她和周扬的女儿周密从小就在一起,是好朋友,所以到周扬家里去她也比较随便,她就向周扬问她妈妈平反的消息。周扬对祖慧说:几十年过去了,你妈妈的疑点可以排除了,但污点还是有的。
后来在中组部1984年给丁玲历史问题的平反上,周扬一直不同意,贺敬之当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他看了中组部的文件,都感觉很有道理,所以他赞同中组部给丁玲彻底平反的文件,周扬就很厉害地说他:你以后还想不想在文艺界做工作了?你这不是同意叛徒哲学吗?给以后贺敬之在中宣部的工作,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1979年秋天,大约就是在召开四次文代会的前后,有一次王震请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贺敬之、柯岩两口子要做好事,想要给丁玲和周扬做一点团结的工作,就提议,请王震同志出面做团结工作,王震同意了,因为他跟双方都很熟悉嘛,在延安的时候就熟悉嘛。找了一天中午,王震在北京饭店宴请,请的人有丁玲和我两口子、艾青高瑛两口子、贺敬之柯岩两口子、周扬苏灵扬两口子、李千烽姚文两口子。我们到的比较早,跟王震说话聊天,最后就差周扬跟苏灵扬没有来,我们在北京饭店等了好长时间,一直等到12点。那天下午王震还要到飞机场去,有个外事活动,所以不能久等,他说那我们就先吃吧,他简单吃了一点就先走了。后来,我看到贾漫写的文章,才知道,那天贺敬之去请周扬,他原来同意来的,到时却迟疑了,动摇了,他就说:“有必要去吗?”贺敬之说:“这是王震同志的好意,为了团结嘛,有什么不好呢?”周扬犹犹豫豫地说:“我不要去了,去了也不好谈什么。你就说我身体不太好。”事后王震同志知道了这个情况,还解释了一下,说:可能是丁玲同志心直口快,周扬同志有顾虑吧。王震、贺敬之都是好心,结果没有搞成。
大概是6月初的一天,我们早晨听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里,广播了新增补的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突然听到了丁玲的名字,此外还有艾青、贺子珍等。我们都很意外,事先并没有人通知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后来《人民日报》也刊登了这个名单。过了大约十天,全国政协开会了,丁玲接到作协拿来的通知,就去参加会议了。会议期问,她又接到通知,要她去参加政协的党员会议,丁玲也去了。周而复是会议的召集人。丁玲回来告诉我,她走进会议室,第一句话就说:“我没跑错地方吧?”因为当时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呢。周而复说:“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开会。”那是丁玲回到北京以后第一次参加党员会,她当然很激动,就写了一篇散文《“七一”有感》,说:“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21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这个文章7月1日就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但是发表后就听到了一些传言,说这篇文章是丁玲在给中国作协施加压力。
关于丁玲的历史结论
1979年的8月,中央组织部干审局有人来通知我们两个一起到中组部去,谈丁玲的历史问题。干审局的两个人,一个是王荣光,一个是倪书林。他们的办公室在三楼,我们到了大门口,传达室往上传,说我们来了。他们要我们上去。门口站岗的解放军都说,叫他们下来,你们那么大岁数了,让他们下来。我们还是上楼去了。他们谈话的主要意思,就是仍然坚持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的结论,丁玲有变节性的政治错误,还是要坚持这个。我和丁玲表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是应该恢复中央组织部1940年的结论。他们这两位就说,你要知道,1943年在延安审干,中央党校还有结论呢。丁玲就说,那我一概不知道。我们也没要他们把那个结论给我们看。就这样,历史结论就一直拖在那里。
一直到1983年夏天,李锐,和我们住在一个楼里的,他那时在中央组织部任常务副部长,我们有一天在他那里谈天,谈到中组部干审局的结论。李锐就说,那你们再写个材料来吧。这样,我们又写材料重新上诉,因此才有了1984年中央组织部的九号文件,《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通知,中组部的人写完了,拿过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丁玲看了这个文件,关于历史问题,完全恢复了中央组织部1940年的结论,文件说“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看完了,丁玲说,现在我可以死了。她的意思就是,死而无憾了。
这个文件起草完了,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要送给几个当事人看,征求一些当事人的意见。但是在征求这些当事人的意见时,他们的倾向性可是大不一样。
我最先知道的是林默涵的意见:同意!没说别的。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三S研究会,就是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三个人的研究会,林默涵也去参加会了,他走到我和丁玲面前来,对丁玲说,我完全同意给你彻底恢复名誉。林默涵先是签字表示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后来又口头道歉了。刘白羽的签字是:完全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有错误,我应该检讨。而且他还打电话来,一定要来看丁玲,是我接的电话,我说,你身体也不好,不要来了,等丁玲身体好了,哪天我陪她一块去看你。他说,那不行,应该我来看你们。结果他就来了。来了嘛,丁玲就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谈了,我们好好团结吧。丁玲去世后,他在悼念文章里还说了:我要负历史的重责。
文件送到周扬那里,他就不大满意,说,起草这么个文件,事先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呢?我不是宣传部的顾问吗?贺敬之就回答他,这个文件不是宣传部起草的,是中央组织部起草的。送到陆定一那里,陆的意思是,没有意见,随他们搞吧。送到张光年那里,张光年最隐晦,说,那时大后方的情况很复杂,我不了解。但是他把国民党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回忆录里面有关丁玲的部分复印下来,附在决议后面,送上去了。我知道,徐恩曾这个材料是作协的一个编辑给他的。这就是那几个当事人的态度。
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
关于我修改丁玲作品的事,我需要作一个说明: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丁玲晚年的东西大多都经过我的修改。她在山西写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我也改过,但不多。我主要修改她遗留下来的《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这两部作品,花的时间多一些。
不是说丁玲晚年的东西粗糙,晚年的作品也都反映了她的思想,但是她的年纪毕竟大了,有时说话难免出错。比如她在口授遗嘱时说,她留下来的积蓄,给孙女一万,给外孙一万,其余的留给婆婆,因为她还要办《中国》,还有社会活动。她说“婆婆”,其实是说“爷爷”,指的是我。所以她晚年写的东西,有的句子不完整,有的措辞过重,我就给她润色。现在我把经过我润色的东西都清理出来了,放在那里。我并没有在丁玲的手稿上修改,而是先抄下来,在抄下的副本上改,这样今后也好有个对证。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再三要出她的文集,在丁玲生前出了6集。这6集都经过我的校改。我对丁玲说,你过去写的文章,主要是到延安之前的文章,有些句子太欧化,不适合青年人阅读,是不是改一改?丁玲同意了。于是我就一篇一篇地校改,校改完一篇,就拿给她看,她认可了,我再交给她的秘书王增如誊清。她有些讲话录音,人家整理的,拿来也是我校对,有一些讲话录音改动比较多,但有一个原则,不改变她的原意,改过后也同样要交给丁玲自己过目。
至于丁玲上世纪40年代的日记,因为要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去世,没办法和她商量,只得我独自替她改。我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她的日记本来记的就很不完全。我修改过她和毛主席的谈话,因为她与主席的谈话,也是凭记忆记下来的要点,不可能一字不差,意思可能不是很完整。比如毛主席说,茅盾的东西不忍卒读,看不下去。没有讲到茅盾作品的好处。我以为,如果把丁玲的日记原封不动地公开,人们会以为,丁玲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攻击茅盾。考虑到毛主席说这番话,只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不是太严谨,同时对茅盾也稍过了一点,所以我把这段话做了适当的修改,把丁玲说的对茅盾肯定的话加进去了。再比如毛主席说郭沫若,有才华,但组织能力差一些,我的修改也没有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丁玲接着毛主席的话说,他们的作品还是写得好,我不如他们。丁玲当时记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发表。丁玲去世后,我觉得这段谈话有些意义,可以发表,比如毛主席一再对她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几年,而要看几十年。
丁玲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对外界隐瞒我修改她的文章,她曾经对人说过:你们知不知道,我家里还有个“改家”。这个“改家”说的就是我。有的作品她甚至想要署上她和我两个人的名字,我坚决反对。《丁玲文集》第6卷里,她又要放我的照片,我也没同意,为此丁玲还有些生气。我做这些事情,不为名,不为利,完全都是为了丁玲。
她的回忆录《魍魉世界》,最后一章还没写她就走了,怎么办?我想要为她补写,可是这能行吗?我有这个把握吗?但我还是决定补写,根据平时她和我所谈,我所了解的,我对她理解的,揣摩、把握,完成了最后一章《起飞》。后面还加了一些附录的文章,是我编进去的,这样有助于读者对于那一段历史、对于丁玲那一段经历的理解,显得完整一些。《魍魉世界》的手稿现在在蒋祖林手里。
说到丁玲的手稿,我不得不说说对手稿等“遗物”的处理问题。丁玲去世后,她的手稿、来往信件、日记、笔记、照片等,这些东西堆了一间屋子。蒋祖林认为这些是他妈妈的“遗物”,他是当然的继承人,他曾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撬开门锁,拿走了一些。对于丁玲的这些“遗物”,应当如何处理,我认为我最有发言权:因为这些“遗物”,不是丁玲的祖产,绝大部分是和我共同生活时的产品,在这些“遗物”上我曾经倾注过大量心血,如前面所说改稿。
另外,为了让这些“遗物”在经历几十年曲折坎坷能够保存下来,我所做的努力也难以复述。这一切,丁玲的子女并未参与。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遗物”,我最有发言权。
十几年来,我把这些“遗物”分类,陆续送到有关单位。比如说比较重要的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手稿,就送到了北京图书馆,那里有很好的保存条件,而一些手稿、信件、书籍、照片等等,甚至日常用具,就给了现代文学馆。丁玲百年诞辰时,她的家乡湖南临澧县建立了颇有规模的“丁玲纪念馆”,所展出的书籍、照片、手迹和各种物品,大部分是我提供的。北京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上海的“左联”纪念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鲁迅纪念馆都有我提供的丁玲“遗物”;还有北大荒,甚至涿鹿县的温泉屯,大大小小的纪念馆里的丁玲书籍、物品,都是从我们家里拿走的。
我这样做,并没有否认祖林、祖慧是丁玲的财产继承人。事实上,丁玲去世后,我已经把家中有经济价值的字画分给了他们;她的作品稿酬一直是由我和祖林、祖慧三人平均分配。甚至他们在2008年为我起草了一份文件,让我放弃丁玲作品版税稿酬继承权,我也签字同意了,尽管我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丁玲去世以后,我忙忙碌碌地过了三年,就年过古稀了。1989年,经朋友介绍,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退休干部张钰结婚。她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古典文学专家张友鸾。张钰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有深厚的家学,对我工作帮助很大;她的家庭也经历过曲折坎坷,我们之间能够互相理解,生活很融洽,我们相依相伴度过了风平浪静的20年。我的晚年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摘自《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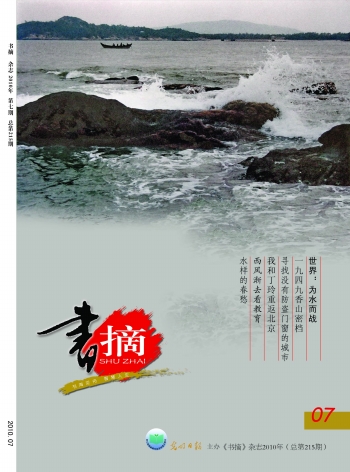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